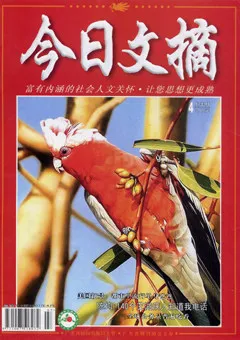汪精卫身死之后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中央党部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全体中委在会议厅门前合影时,汪精卫站在第一排中间。突然,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从记者群中跳出,拔出手枪,向汪精卫开枪。汪精卫身中两弹,一弹击中左颊,一弹击中脊背。住进中央医院之后,取出左颊内的一颗弹头,另一颗子弹仍留体内。
1943年8月,汪精卫枪伤复发,南京日军陆军医院为他施行手术,虽然取出了第二颗子弹,但病情未见好转。次年三月,汪精卫被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就医。11月10日,死于名古屋。
汪精卫死后,其妻陈璧君决定将遗体运往南京,先由医生将尸体进行了防腐处理,又煞有介事地为汪精卫换上“新国民礼服”,颈上套上日本天皇所赠送的菊花章饰。
11月12日,汪精卫生前最喜爱乘坐的专机“海鹣”号,载着陈璧君等人及汪精卫的遗体直飞南京。
到了南京之后,“统办丧仪”成为伪府官员的一件要事。先是出巨资240万元,让汪精卫生前的一个副官置办了楠木棺。此副官仅花了140万元置办了棺材,余下的100万元私吞。此事人人皆知,只是瞒过了陈璧君。
汪宅原是在颐和路34号。旁边西康路的几幢大厦本可设置灵堂,但陈璧君以为汪精卫“开府和运”一场,偏偏要将灵堂设于伪府大礼堂。
当伪府官员一一“瞻仰”遗容以后,重行入殓后却遇到一个问题,即棺柩如何摆放?由于礼堂的讲台前后较窄,左右较宽,若是按照民俗,前后方向竖放,则前面死者遗像和香案不便放置。若将棺材横过来摆放,又于“理”不合。若是把讲台拿掉,则摆放位置太低,未免有碍“观瞻”,若是去掉讲台再重新做一个合适的讲台,则时间来不及。
只见陈璧君怒气冲天,大骂左右“不会办事”。之后,亲自出马,叫人将棺材抬起来,亲自布置,一抬再抬,挪前挪后。一帮伪府官员,尽管心里不以为然,但却缄口结舌,不敢言语。汪精卫的儿子汪孟晋对陈璧君所为一忍再忍,最后终于发火了,大声骂道:“你不必再胡闹了。爸爸在世的时候给你搬到东,搬到西,丝毫不得自由,现在你还把他搬来搬去,弄得死者不安,我看你将就些,算了吧!”一番话,说得陈璧君哑口无言,不敢还嘴。熟悉汪家底细的人都知道,汪家有一奇怪现象:儿子怕汪精卫,汪精卫怕陈璧君,陈璧君怕儿子。这一现象被人称作“连环怕”。
灵堂布置完毕,伪府官员环绕棺材行礼。之后,又有一问题:陈璧君认为遗像太小,因棺前所挂的遗像是一张普通照片,仅有十二寸。于是便让人将其放大。谁知,放大后遗像又太大,比人的身体还大。由于灵台前没有这么大的地方,于是只好呈倾斜状,斜放在案前。
礼堂两旁挂有大小汉奸的挽联。大汉奸陈公博的一幅挽联,其上联为:“大夏奠新基,保亚兴华千古仰”,下联为:“哀音传薄海,鞠躬尽瘁百僚悲。”
依照一干伪府官员的心思,陈璧君及汪精卫的子女当睡在灵旁“陪灵”。谁知,陈璧君一声令下,要叫伪部长、次长以上官员及各方面的大员按照所拟名单陪灵。一个个官员暗暗叫苦。
陪灵官员每晚九点钟必到,若迟到,陈璧君必然发怒,骂道:“不忠于职守,一点良心都没有。”次日早上八点方能离去,若有早走者必被骂。
陪灵时一律不许带被子、毛毯等卧具。最叫苦的是有鸦片瘾的官员,因为鸦片烟枪不能带往灵堂。这些官员便在家中过足烟瘾之后再来灵堂。此外,陪灵时,假若官员们说话声音略大,这时副官便会出来说:“说话低些,不要惊了夫人睡觉。”若是官员半夜打起哈欠,被陈璧君看到,她便要问:“×同志,你何必来呢,在家里睡觉不舒服吗?”
依陈璧君的主张,是将汪精卫葬在广州黄花岗旁边的白云山。后来,陈璧君的干儿子、时任伪宣传部部长的林柏生说:“这样的一个大人物,应该葬在中山陵以永垂不朽,等到交通便利再另作计划。”林柏生的意见得到大小官员的一致赞同,陈璧君也表示同意。
汪精卫下葬的山地原没有名称,于是,林柏生取名叫“梅花山”,以为如此一来,可与黄花岗“比美”。但梅花山上一棵梅树也没有,林柏生又出一主意:待来年清明再行补种。同时,又传命伪府各部门摊款,兴修石墓,“以志景仰”。后来,陈璧君乘机大捞一笔巨款。
下葬之后,发生了一件奇闻:安葬送殡的那天,大赚棺木钱的那个副官,手扶棺材,寸步不离,走了几十里路。那种悲哀欲绝的样子,使许多官员都以为他“忠心故主”。但是,到了第二天,副官突然“七孔流血”暴死。究竟因何而死成了一个“谜”。陈璧君“盛道其孝”,便仿效明代太监王承恩殉葬崇祯皇帝故事,将此副官葬于汪墓之旁。
汪精卫死去一周年后,又发生了一件奇闻:周年时,其女汪文恂前往坟前祭拜,并栽了一株菊花。到了11月22日9时,汪精卫的尸体被人掘出移走,下落不明。汪文恂为此事遍询南京各机关,并给蒋介石发去一封长信“有所请求”,但此事始终未见消息。
(孔令申荐自《知识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