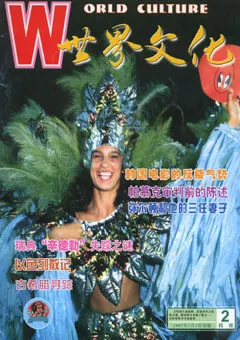爱尔兰断忆
我曾常驻伦敦,因为公事,爱尔兰去过多次。从伦敦到爱尔兰非常方便,每天飞往都柏林的航班多得很。仅仅50分钟的航程,而且作为国内航班处理,不要签证,不填表格,不需办理任何海关手续,顺当极了。尽管是两个国家,但感觉上好像没有出国似的。
苍凉
凑巧的是,我去爱尔兰除了一次,其他几次都在暮秋时节。一种很萧飒的感觉老是笼罩在我的心头。静僻的使馆区有条叫艾厄伯利的马路,我有时漫不经心地独自徘徊在这条路上,路两旁梧桐树那枯萎的阔叶悠悠然随风飘落,很快在路面上积了厚厚的一层,以至掩没你的脚踝。我从未看到有人去打扫。任其散落,任其堆积,任其浮移。这里的人们好像早就习惯了如此。双脚踩踏在那枯槁无奈的黄叶上,立时发生阵阵清脆的声响,曾经是多么生机盎然的生命,竟如此破碎了,这时再加上秋风掠面,无疑是一种苍凉的氛围,令人怅然若失。
爱尔兰与英国是近邻,何止是近邻,历史上爱尔兰在英国人掌控之下曾达数百年之久。如今虽说还有无数的恩恩怨怨,却也难以离分。萧伯纳出生在都柏林,人们或者说他是爱尔兰人,或者说他是英国人,似乎都没有错。由于两国挨得太近,关系太密切,至今人们还常常将它们放在一起议论或者比较。例如有这种说法:“如果说英国是城市,那么,爱尔兰就是农村。”意思很清楚,爱尔兰远比不上英国发达与繁荣。英国和爱尔兰都多雨,天气恶劣是远近有名的,尤其爱尔兰更甚,于是有了这种说法:“英国的雨是爱尔兰下剩的。”我去爱尔兰几次,还不错,没有碰上那倒霉的阴雨天,但天天几乎都是满空阴霾,很难见到让人赏心悦目的明媚阳光。如果你到海边去,更是朔风狂猛,几乎站不住脚,加上冷冽彻骨,很难久留。
原野
我去过爱尔兰的西部和南部,一次是由爱尔兰国防部组织武官团去南部参观,三次为中国代表团的访问作准备,去西部的香农、利默里克一带。我实在为爱尔兰原野那无边的绿色植被而感叹。无遮无挡的视野里,不时出现三三两两或者大群的牛羊安静地吃草,它们是那样闲适,那样漫不经心。微微参差起伏的绿茵般的原野上,水草丰茂,那绝对是牛羊的天堂,它们站在那儿,好像根本无需向四周挪动,仅仅身边的青草就足够了,让你感觉永远也吃不完似的。
有一次,我们从香农返回都柏林,乘坐当地出租车,六七小时的路程。憨厚热情的中年司机一路上给我们当讲解,路过风景奇异的威克洛时,司机告诉我们那就是好莱坞大片《勇敢的心》的外景地。这部影片我看过几次,民族英雄威廉·华莱士的故事感人至深。司机给我们讲述一段后就自得其乐地唱起歌来,他唱的歌多是简单的节奏,却十分明快,可能都是爱尔兰的民歌。他边说边唱,长途旅行中他不觉疲倦,我们也开心。
历史
都柏林谈不上多么宏伟气派,它无法与伦敦、巴黎、维也纳相比,但一点也不缺少古朴雅致的魅力。很多街道、楼厦、教堂一看就很沧桑。更不必说那建于中世纪的曾见证都柏林无数凄春悲秋的城堡,昔日英国驻爱尔兰的总督就是在这里颐指气使、挥舞权仗的。古老的利菲河悄无声息地缓缓流过市区,河上静卧着一座座年代悠远的大桥。流经市区的还有条运河,出租车司机告诉我,那是当年为了专门把都柏林酿造的佳酿——吉尼斯啤酒运出去而开凿的。河道不宽,河水却那么盈满和清澈,难以想象的是,河边竟摇曳着一丛丛如雪花絮的芦苇,不仅如此,三五成群的野鸭和天鹅优雅地在河面上游来游去,诗意盎然。
公事之余,我悠闲地走上都柏林最著名的大街——奥康内尔,这是爱尔兰一位杰出民族英雄的名字。街中心矗立着高达120米的上下一般粗细的金属柱形塔,如果让我形容,那就像孙悟空的金箍棒插立在这条大街上。入夜,这高高的都柏林塔通体晶明透亮,屹立于云空,它象征着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昂然精神。距离这塔不远处便是建于1818年的古典式建筑——邮电总局,1916年复活节反英起义就是在这里揭开序幕的。组织起义的共有16人,非同寻常的是这其中大多为诗人。据我驻爱使馆沙大使介绍,这次起义遭到英国殖民主义血腥镇压,为了免得更多群众受牵连,组织者表示投降,他们被押送英国,最终还是统统被杀害!
冤家
爱尔兰与英国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对冤家对头。可是,长期历史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他们又难分难解。英国1169年入侵爱尔兰,由于爱尔兰人民顽强抗争,1921英国被迫同意爱南部26郡成立“自由邦”。1949年4月英国最终承认爱独立,但拒不归还北部6郡。也就是说,英国曾统治爱尔兰近800年,多么漫长的苦难岁月!我的爱尔兰朋友一说起英国人,几乎都没有好感,往往情绪激动,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最起码也是不屑一顾。有一次,我乘坐出租车,与司机不知怎么说到英国,只听他很鄙夷地发出一声:“呸!”使我大吃一惊。我不止一次听到爱尔兰朋友不厌其烦地谈起1845—1851年大饥荒的惨痛岁月。土豆是爱尔兰人的主食,一日三餐离不了,可是那几年因病害土豆严重欠收,老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可是,英国逼着爱尔兰人照样向他们出口谷物等。由于饥饿、伤寒、霍乱,造成爱尔兰150万人死亡,迫使200万人移居海外。爱尔兰人永远忘不了这苦难的历史。很多年间,甚至爱尔兰独立后,对于大事小事,尤其是国际问题,凡是英国人说:“Yes”,爱尔兰人总是说“No”,简直是不共戴天。
可是,爱尔兰与英国的苏格兰关系却不错。历史上,苏格兰与英格兰分治,英格兰以后吞并苏格兰,实行残无人道的统治,比如苏格兰男人结婚,当地的英格兰首领对新娘享有“初夜权”,所以,爱尔兰与苏格兰有共同遭遇,相互同情。举一个小例子,一次我与爱尔兰朋友谈起苏格兰的食物,苏格兰有种著名的传统食品“哈吉斯”,羊肚子制作的,我说不敢恭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确实很难吃,可是那位爱尔兰朋友听我这样说,一声不吭,明显有些不乐意的样子。所以,以后我再也不敢在爱尔兰人面前说苏格兰人的任何不是了。
当然,爱尔兰官方的态度则谨慎得多了。记得一次我同英国、美国驻都柏林的武官到爱尔兰国防部去拜访,那大楼过道里有几座乌铜色塑像,半身的,我随口问了一句这都是谁的塑像,爱方陪同官朝着英国武官毫无忌讳地说:“我们的英雄!是被他们杀害的!”为了不过分刺激英国武官,又补充了一句:“这当然是历史了。”那位英国武官满脸堆笑:“我们现在是朋友了。”目前英国和爱尔兰的关系总体上还是比较密切的,双方相有需求,在北爱问题上,英国需要爱方支持,而英国则是爱尔兰的主要出口市场。
舞蹈
爱尔兰的民间舞蹈,尤其是踢踏舞,比如《大河之舞》那种以踢踏舞为主轴的集爱尔兰舞蹈之精华的绝妙艺术,更是四海闻名、耳熟能详了。跳踢踏舞其舞者越多越精彩。此种艺术功夫尽在足下。据我驻爱尔兰沙大使说,每秒钟舞者足部各个部位可迅速击打地面17次!实在不可思议!你不可不欣赏一下这美妙绝伦的艺术:数人动作齐整化一、声响锵铿有力、神态俊丽潇洒,伴随着悠扬委婉、充满节奏感、旋律反复无尽的音乐,真是气势夺人,极视听之娱,浑身热血澎湃,沉醉其中而忘乎所以。我看过踢踏舞的大型表演,也看过酒吧里的小型表演。记得那次应邀在利菲河畔的阿灵顿饭店的底层酒吧里看歌舞表演。这是个能坐三四百人的很不小的酒吧,人手一大杯飘着白色泡沫的深咖啡色吉尼斯啤酒,璀璨的灯光把那不大的舞台照得通亮,踢踏舞由单人,或双人,最多四五个人表演,舞技一流,还不时穿插男高音歌手唱的民谣,很快把气氛推向高峰,观众们发了狂,再也坐不住,很多人干脆一下子跳到桌子上,皮鞋踏着桌面大跳特跳起来。夜阑更深,宣布散场,许多人甚至是边跳边踱出酒吧的。
文学
现在我该以同样崇敬的心情,说说爱尔兰的文学了。这也正是爱尔兰人最引以为骄傲的地方。爱尔兰人使用英语(至于爱尔兰语如今只有35%人掌握),英国人更是使用英语,但是,英语在爱尔兰人的语言中,才出现了令举世赞叹的辉煌。爱尔兰人一致这么认为的。当然,英国文学的成就毫无疑问也是非凡的。不过,爱尔兰作为一个很不起眼的蕞尔小国,竟有4个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就是诗人叶芝、大文豪萧伯纳、以《等待戈多》为代表作的剧作家贝克特和诗人希尼,这不能不说是奇迹。何况,其他极有成就的作家还多得很,这包括19世纪唯美主义代表王尔德、代表意识流最高成就的《尤利西斯》作者乔伊斯。这里,还值得提到的是在爱尔兰长期独立斗争以及英国工人阶级斗争中,涌现了许多以作品鼓舞人民斗志的诗人。他们中不少人本身就是斗争的参加者。比如爱尔兰贫农的儿子吉姆·康奈尔就是创作革命诗歌的名手,他为歌曲《红旗》作词:
我们把人民的旗帜降下,盖起为自由而战死者的尸体,他们凝结在旗上的鲜血,从此就把烈火燃起。
我去过爱尔兰多次,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爱尔兰人对他们那些大作家与诗人极为尊重与崇仰。我曾住过鲍尔斯布里奇饭店,我发现这饭店8层楼,每层楼都以爱尔兰的一个作家或诗人命名,包括王尔德、叶芝、乔伊斯、贝克特、肖恩·奥卡西(戏剧家,作品主要有《一个带枪人的影子》)等。并且,每层都放置着作家的小型塑像,附着作家生平文字。我还曾住过梅里恩饭店,院内有个美丽的花园,花园中间甚至竖立着如真人般高大的乔伊斯的塑像,其足下是贴地的铜质大圆盘,上面密密麻麻地镌刻着《尤里西斯》的精彩章节。不仅如此,在都柏林市中心著名的格拉夫顿商业街,也有一座乔伊斯的塑像:戴着礼帽、眼镜,手持拐杖,侧着身子,面目清瘦,却风度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