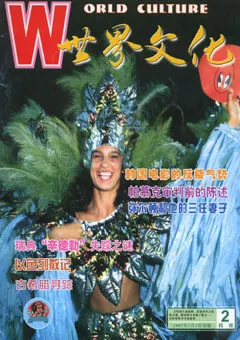宣泄与独白
肖斯塔科维奇生于1906年,卒于1975年,享年69岁,他的《第一交响曲》、歌剧《姆青斯克的麦克白夫人》(又名《卡杰里娜·伊斯玛依洛娃》)、《黄金时代》等作品引起了世界乐坛的瞩目。他早先热衷于音乐的革新,但得到的却是前苏联官方的严厉批判,以致于不得不立即撤回正在排练中的《第四交响曲》;随后他以较快的速度写了《第五交响曲》,才算得到当时官方和音乐评论家的认可。从此,他开始写传统式的作品,但创新的步伐并没有停止,而是采取了“旧瓶装新酒”的韬晦之术。正如一位作家所说:“他在作品中似乎总是探索着,一方面显然是公开的,另一方面则是隐蔽的,他以一种多样化的风格来适应这个世界。”他不断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冲击,为此,他心情压抑,难以释怀,不得已只好以“宣泄和独白”为两大特色在音乐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感情。
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往往不能把题目与作品的内容联系起来理解,例如《第八弦乐四重奏》,总谱的题目是“追忆残酷的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但与战争的内容其实根本无关;又如《第五交响曲》,它以“一个苏联作曲家对外界公正的批评的回答”面世,一般都认为这部交响曲与贝多芬、柴科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都是属于人与命运较量的同类作品。实际上,作品内容深藏玄机,细听之后感到它是一部悲剧性的交响曲。第一乐章上下跳跃的主题新鲜特别,宣泄作曲家的悲愤痛苦,与严酷现实的冲突,几番挣扎最终只能诉诸无奈的期待。在第三乐章里,以三个互补的主题深切地倾诉对受苦受难者的同情,也表达了作曲家本身的沉痛,结尾时竖琴和钢片琴组合的主题,似泪珠滴落,感人至深。第四乐章是明朗的快板,两个主题相互递增至一个又一个的高台,可见挣脱苦难之艰辛,在强有力的鼓号声中痛快淋漓地宣泄出来。这是官方所希望的结果,也是他对今后创作充满信心的宣告。
1953年,斯大林逝世,肖斯塔科维奇很快写出了《第十交响曲》并随之演出,由此引出了无数的赞誉和质疑,而他本人则对作品的内容闪烁其词,讳莫如深。这部作品仿佛是他蕴藏很久的积郁一下子宣泄了出来,内涵非常丰富,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签名主题(DSCH)贯穿全曲,充分体现出作曲家个人对时代的深刻反思;人性化的、富于哲理的、复杂的构思令人难以捉摸。
在《第八交响曲》的第二、三乐章中,肖斯塔科维奇的讽刺、斥责,木偶式的、肆无忌惮的狂暴形象尽情展现,仿佛烈火,越烧越旺;高超的技法,令人惊叹。在《第十一交响曲》中,无助的主题与狂暴的主题交替出现,对比强烈,令人惊心动魄。在这些乐章中,肖斯塔科维奇的作曲才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善于创造性地发挥,乐曲构思深广,配器巧妙,能把群众咏唱的歌曲融入交响曲的洪流之中,可以说是一个经典的范例。
与他的宣泄相辅相成的另一个特色是他的内心独白。在漫长的创作岁月中,肖斯塔科维奇不断受到官方的批判和压制,他只能在音乐创作中抒发自己的委屈与不平,并一再沉浸在深刻的思索之中。尤其是在他许多日记式的弦乐四重奏中,处处可以听到使人难以理解的独白式的、扑朔迷离的喃喃自语,他晚年创作的那些四重奏,足可以与贝多芬最后的几部四重奏媲美。《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是悲剧性的帕萨卡里亚调式,冷峻、凄美,欲言又止,最后只好舍弃乐队,以完全独自的形式,尽情倾诉。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奥伊斯特拉赫曾说:“我越是了解这部协奏曲,越是仔细地去听它,它就越让我喜欢,于是我以更大的热情去研究它,思索它,为它而活……”这里,我想他所指的就是这个感人肺腑的乐章。
肖斯塔科维奇逝世后,乐坛开始对他的创作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他的作品重新全面评价,几乎演出了所有他的歌剧、芭蕾舞剧、交响曲、协奏曲和15首弦乐四重奏、奏鸣曲、各式小品以及电影音乐。他是音乐史上少有的、能及时反映时代信息的音乐大师,他具有适应各种曲式的才华,例如反映二战的第七、第八交响曲,反映1905年二月革命的《第十一交响曲》,歌颂绿化的《森林之曲》等许多杰出的作品。他还为不少电影配乐,如《伟大的公民》、《卓娅》、《攻克柏林》、《难忘的1919年》等等。
客观地说,肖斯塔科维奇是一位爱国的、才华横溢的作曲家,他一生热爱祖国,始终没有移居国外;他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法西斯兵临城下,为了保卫斯大林格勒,他挺身而出,担当消防队员,他的作品在隆隆炮声中演出,鼓舞人民与一切邪恶势力作不屈不挠的斗争。罗斯特罗夫斯基称他为“20世纪的贝多芬”,联合国请他谱写歌颂和平的联合国国歌,他的为人和音乐创作,值得人们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