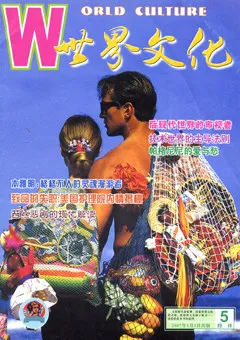“最蓝的眼睛”的困惑
在上世纪40年代以前,美国主流文学中的黑人女性都是以一种刻板的模式出现的。南方文学中最突出的黑人女性代表形象大多以保姆、情妇或混血儿出现。直到上世纪70年代,随着黑人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美国文坛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黑人女作家,如托妮·莫里森、爱丽斯·沃克等,自此,黑人女性才开始突破单一模式,变为内心丰富多彩、有独立个性的丰满形象。这些女作家的作品不仅揭示了广大黑人在遭受种族歧视和压迫下痛苦的生活现状,还触及了更为深刻的主题,即建构本民族文化,追求个性自我。迄今为止,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影响力与成就甚至超过了美国黑人男性文学。
托妮·莫里森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她原名克鲁伊·安东妮,1931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洛雷恩镇的一个黑人家庭,父亲是蓝领工人,母亲在白人家庭帮佣,自幼深受黑人民族传统和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培养了她强烈的民族感情。1970年,她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一问世,立即引起美国文坛的重视,之后她又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秀拉》(1973)、《所罗门之歌》(1977)、《柏油孩子》(1981)、《宠儿》(1987)和《天堂乐园》(1998),并在1993年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如今,她与爱丽斯·沃克齐名,成为美国黑人女作家的代表,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当代黑人小说家之一。
莫里森的大多数作品关注的都是关于现代美国中的种族和性别的问题。她的作品触及种族和压迫,尤其是对女性的压迫,实际上,她的作品很少以男性为主人公(《所罗门之歌》是她惟一一部以男性为主人公的作品)。她从开始创作起,就关注残酷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给黑人女性带来的双重压迫,并积极探讨黑人女性如何确立自我身份,寻求自身生存出路。莫里森认为,黑人女性若要拥有自我,必须不断地进行奋斗,并且要建立起一种与黑人同胞紧密相连的关系,脱离黑人民族文化和传统,割裂与黑人社会的联系,必将深陷痛苦之中。
莫里森谴责那些抛弃本族文化而一味追求美国白人主流文化的黑人们,建构黑人文化是莫里森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当时,许多黑人在长期受压迫、受歧视的状态下,漠视本民族文化传统,厌弃自己的黑人身份,转而追求白人文化,一味盲目迎合白人审美观、价值观。尤其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黑人女性,在白人种族主义盛行和男权意识猖獗的社会里,她们是当时最弱势的群体,她们不仅感到困惑无助,而且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和位置,从而不自觉地从心理上、行动上依附强权。
莫里森最早的作品《最蓝的眼睛》代表了她创作的主要思想,奠定了她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是黑人女性作家作品题材的一个突破。在这本书中,莫里森生动地描绘了一群性格迥异的黑人女性形象,这是在其他黑人作品中很难见到的。通过对黑人女主人公悲惨生活经历的描述,莫里森展示了由白人文化冲击所造成的黑人自我身份的困惑和迷失,以及他们对本身弱势的忧虑与无助,并着重描述了在种族与性别双重压力下美国黑人女性的生活状态。
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表现了黑人女性在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造成的自我身份迷失和对主流文化的盲目追求,并探讨了如何进行身份重建。在长期痛苦压抑之下,很多黑人女性首先否定了自己的黑人形象,进而又否定了自己与黑人家庭和社会的感情联系,书中的女主人公佩科拉的母亲波莉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她在白人家庭做女佣,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压迫、被奴役,反而以此为荣。她将自己的生活分为两部分,把她在白人家“美好有序的生活仅限于她个人的小世界,并不把它带到库房的家里,也不带给她的孩子。”在白人家里,她尽心尽力,任劳任怨,而回到自己家中,她满腹怨气,让自己的儿女们整日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中,因为嫌弃佩科拉的黑人外貌,她只让佩科拉称呼自己为“布里德洛夫太太”。
在当时她们生活的黑人社区里,大部分黑人在长期受压迫与奴役下,已经接受了白人的主流文化,她们鄙视自身的肤色,将白人的审美观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渴望拥有白人一样的外貌,完全忽略和漠视了她们本身的特质和美感。“大人们、大女孩们、商店、杂志、报纸、橱窗——全世界都一致认为所有的女孩儿都喜爱蓝眼珠、黄头发、粉皮肤的布娃娃。”
因此,黑人女孩佩科拉将自己生活中的不幸归咎于自己的黑人外貌,她日夜祈祷,渴望得到一双象征着白人社会的审美观的蓝色眼睛来解除自己的痛苦,得到其他人的关注和爱。“佩科拉意识到如果她的眼睛……不同的话,就是说,她有双美丽的眼睛的话,她本人也会不同。……漂亮的眼睛。漂亮的蓝眼睛。又大又蓝的漂亮眼睛。”殊不知,这只给她带来灾难和不幸,在遭受父亲的强奸并怀孕后,社区里的黑人们在白人的各种价值观的影响下,没有宽容和原谅她,她最终发疯了。通过佩科拉的悲惨遭遇,莫里森试图唤醒广大黑人同胞重构本民族文化,同时告诫他们,丧失了自己的种族文化,终将失去一切。
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里还描绘了一些坚守自己民族文化的坚强而自立的黑人女性,在周围人们盲目而狂热地追求白人审美价值时,她们自尊自爱,自强不息,坚守黑人文化,在抗争中顽强生存,如佩科拉的好朋友克劳迪娅,她毁掉了她的圣诞礼物——带蓝眼睛的白洋娃娃,痛恨雪莉·坦布尔(印在杯子上的漂亮白人女孩),拒绝接受白人审美观、价值观。在佩科拉被人欺负的时候,她总是挺身而出,帮助她、保护她。当周围人们都希望佩科拉的婴儿死去的时候,克劳迪娅却希望他能活下来,“为的是与大家普遍喜爱的雪莉·坦布尔、莫里恩·皮尔等白娃娃们抗衡。”和其他人不同,她看到了婴儿的美,“婴儿长着卷成O形的细发,小黑脸上闪动两个银币似的眼睛,宽鼻子,厚嘴唇,黑绸子般的皮肤。不是耷拉到蓝眼睛前的黄色人造纤维头发,不是小翘鼻子,樱桃小嘴。”她的种族自豪感,她的自尊自爱,她的反抗意识,让她不同于那些抛弃本民族文化,一味盲目迎合白人的愚昧软弱而麻木的同胞们。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黑人的希望,莫里森通过塑造这位自强自尊、充满反抗精神的黑人小姑娘,向广大黑人同胞呼吁,只有首先尊重、热爱本民族的文化,才能得到其他人的尊重,进而迎来整个民族的复兴。同时,莫里森也进一步指出黑人应该如何摆脱压迫和歧视,在反抗白人的种族压迫时,黑人应该将本族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武器,抗拒种族观念的歧视,坚守黑人本族传统文化,最终实现真正的自我。
通过塑造几位有代表性的黑人女性形象,莫里森揭示了当代黑人女性生活现状和心理活动,那些在白人价值观的强大冲击下迷失自我,抛弃本民族黑人文化,否定自己黑人身份,进而否定与黑人社会联系的黑人女性,无法抵御种族主义观念的侵蚀,注定成为牺牲品,陷于寻找自我的痛苦中。只有自尊自爱,热爱家庭,坚守本族文化,坚定自己黑人身份的黑人女性才能界定自我身份,获得完整的自我,找到自己的生存价值和生存空间。至此,莫里森为黑人女性身份重建问题提供了明确的答案。
在积极探讨黑人女性身份建构问题的同时,莫里森也不忘关注黑人男性的生活状况。在《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的父亲乔利好吃懒做,不事生产,经常动手殴打妻子。在学校里,一群同为黑人的小男孩常常欺负佩科拉,“他们自己也是黑皮肤……他们对自身肤色的鄙视使这种辱骂更尖刻。”书中的大部分黑人男性表现出来的都是他们残忍暴力的一面,莫里森将他们描写成失去人性的一群人,其根本目的并不是谴责他们对黑人女性的压迫,而是希望人们能够关注他们的不幸。正是由于整个白人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和迫害,使他们在长期的痛苦中变得自憎,对生活感到无望,而他们又无力改变现状,才转而压迫黑人女性来宣泄心中的苦闷。
《最蓝的眼睛》是莫里森的成名作,同时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她在书中塑造了种种个性鲜明的黑人女性形象,向人们展示了身处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的黑人女性生活状况,同时提出了尊重本族文化,建构自我身份的创作主题。黑人,特别是黑人女性要想获得自由和独立,不能脱离本民族传统和文化,要以民族文化为基础来建构自己的民族身份,从而获得自己的个人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