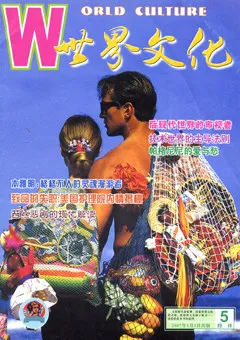马真读碟
只有黑暗穿过了玻璃——《犹在镜中》
在伯格曼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结婚之后,其电影风格走向了室内化。在我看来,这种电影风格的变化,混合早期的文学化对白,由此形成了最典型的伯格曼风格(有些评论家称之为“室内心理剧”)。在这种风格最大的转折期,伯格曼拍摄了震惊世界的“上帝沉默三部曲”——《犹在镜中》、《冬之光》、《沉默》。这三部曲真正体现了导演对于神学的怀疑态度,从某种角度来讲,《第七封印》和《处女泉》并没有彻底的否定上帝的概念,《第七封印》中的马戏演员看到的圣母形象,以及《处女泉》最后的神迹出现,都是对上帝的肯定。然而,《犹在镜中》中对上帝存在的怀疑,《冬之光》中对信念的否定,以及在《沉默》中对上帝缺失情况下的人与人关系的讨论,不仅否定了上帝概念,同时流露了伯格曼后期关于人物交流困境和心理阴影的电影主题。
《犹在镜中》中讲述了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女儿和她的丈夫、父亲、弟弟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故事主要发生在一个小岛上的与世隔绝的小屋里。对于这个女人来说,她一直在等待着上帝的接待(这被看作一种精神疾病),上帝不仅成为了她心灵上的寄托和追求,同时可以在生理上给予性满足(当然这也被看作某种精神分裂的特征)。而电影结尾上帝以蜘蛛向女人显现最终导致了她精神的完全崩溃。此外,父亲对于女儿的病情并不是特别关心,他细心的记录病情的发展只是为了自己写作的需要,女儿的精神失常同他的妻子的自杀好像是一种生命轮回,一种对于他冷漠虚伪的犬儒主义极大的抨击。而她的丈夫只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治疗自己的妻子,他是人类迷信科学的典型代表,因此夫妻两人不可能有任何沟通的信念基础。在整个故事中,最具特征的人物还有弟弟一角,他正处在青春萌动的年纪,对于神秘而美丽的姐姐有一种暧昧的需求,然而由于道德的心理原因,他又对于这带给他冲动的女性抱有一种敌对的态度,他们相互辱骂(在姐姐看到他在拉丁文书中偷藏女人的图片),又相互吸引(姐姐在她的阁楼中向他诉说自己的痛苦)。在电影最后,姐姐被直升飞机带走之后,弟弟在心理上也留下了很深的阴影,他所构建起来的现实生活也因此瓦解。电影结尾,父子一段对话,父亲试图规避上帝存在的问题,将爱作为一种信仰灌输给已经丧失信仰能力的儿子。最后一句对白——“父亲和我说话了”,也可以看作是整部充满了压抑、挣扎、绝望的电影中一个希望和曙光式的表达。
来自上帝沉默的光芒——《冬之光》
《犹在镜中》通过严谨的音乐结构所达到的人物关系的对立和变奏,从而达到对上帝沉默的一种解说。从某种角度来讲,这部电影是三部曲的基础,如果上帝根本不存在,那么信仰问题(《冬之光》主要探讨)就根本不会提出。《冬之光》这部电影的风格相比另外两部,更加趋向于一种文学性,电影主体是通过大量的对白所构建,因此主题的把握深深地隐藏在角色大量冗长而晦涩的独白或对话之中。
电影截取了一个牧师在早晚两次布道这段时间内发生的几件事情。这部电影不像《犹在镜中》那样所有人物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主题是通过人物关系的转变而被推动,《冬之光》中的牧师成为了绝对的主角,他总是试图向别人表达一种上帝沉默的思想,包括求助于他的渔夫、他的情人和一个教堂的管理人员。他不仅怀疑自己信仰的力量,而且将这种思想作为自己自私虚伪的借口。下面我要引用电影中一段对白:
“现在我读到耶稣受难那部分了,那部分使我停了下来,所以我想和您讨论一下,艾里克森牧师,我觉得,对于耶稣的受难,他的痛苦,您说过于强调是不是全错了?这个对于肉体痛苦的强调,其实有些专横,或者并没有那么坏。以我的愚见,我受到的肉体痛苦也有耶稣这么多,而他的痛苦非常短,我想那大约持续了4个小时。我觉得他在另一方面受到的苦要深的多。也许是我想错了,但想一下蒙难地,牧师,耶稣的门徒都睡着了,他们不明白最后的晚餐的意义。当执法者出现时,他们都跑了,还有人否定自己是耶稣的门徒,而耶稣却被人出卖了。耶稣已经认识他的门徒3年了,他们一天到晚住在一起,却不知道耶稣说的、做的什么意思,门徒们抛弃了他,全部都这样。他被抛下了,意识到没有人明白他,当他需要人依靠时却被抛弃了。那一定是无比的痛苦,但最糟糕的还没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吊在那里受苦时,他叫到:“神,神啊,你为什么抛弃我?”他有多大声叫多大声。他以为他神圣的父亲抛弃了他,他觉得自己鼓吹的都是谎言,在他临死前他都怀疑。这不是他最大的痛苦吗?上帝的沉默!”
假使我们相信上帝的存在,然而在任何事件发生过程中(就好像耶稣的受难),他都是沉默的,他不为信仰他的人指明道路,总是在事情发生之后通过神迹来补偿,那么信仰就是一种痛苦的事情,因为在信仰的过程中,并不知道信仰是否有效。在电影中的牧师,已经丧失了信仰的能力,他却试图通过祈祷(祈祷应该建立在信仰之上),重新获得信仰的能力,或者可以说,试图通过祈祷可以从上帝那里寻求祈祷的理由。
写实还是写意——《无间风云》
当你对比一下《无间道》中文绉绉的对白和《无间风云》中“fuck”满天飞的对白,就可以知道这两部电影除了故事以外,没有任何可比性。如果你喜欢《好家伙》,那么你一定不能错过同样优秀的《无间风云》;但如果你喜欢《美国往事》多一点,那或许你更加中意香港版的《无间道三部曲》。
《无间道三部曲》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的“写意”文化传统上的,干净整洁的办公大楼,不言不语的内敛表演,影片中那些华丽的慢镜头,以及适时响起的蔡琴的歌声,都烘托了一种悲壮无奈的英雄主义色彩。加上众多“文斗”场面,使得观众在智力和情感上都能够认同刘德华和梁朝伟饰演的角色。因此,“无间”来自于两个卧底内心不断纠葛的矛盾挣扎,而环境则退居到背景的地位,为两者的行为提供合适的条件。因此,香港版本的《无间道》的主题集中在了“人”的身上,尽管不能说这是这部电影的失败(恰恰它的成功就在于此),但相对于《无间风云》宏大的叙事背景,香港版本显得有些小家子气。
《无间风云》的英文原名是“departed”,这个词来自于电影中一张献给死者的纪念卡片,“Heaven holds the faithful Departed”,意思是“天堂收留那些忠诚于信仰的死者”。在此,斯克塞斯将“无间地狱”的折磨转换为“天堂”的救赎,而这恰恰是对《无间道》主题最大的改编。斯克塞斯不仅在主题上作了文章,而且为两个卧底的身份背景做了更加详尽的安排,因此不同于香港版本对人物关系的注重,导演更加深化角色本身的力度和深层的表现空间,并将其植入社会大背景之中,展现了“美国梦”的破灭。与此同时,导演还为观众呈现了一个现实化的黑帮社会,这个黑帮社会是我们在《好家伙》和《教父》中熟悉的意大利黑帮,残暴但注重血缘关系。因此,斯克塞斯仍然坚持着自己曾经的现实主义社会批判风格,并将其注入到《无间风云》中,使得它脱离了“写意”而更加“写实”。
《无间风云》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克塞斯对于剧本强大的把握能力,他把陈慧琳和郑秀文扮演的角色合二为一,塑造了Darleen的角色从而凝合了剧情的张力,且为最后Sullivan被杀提供了基础。同时,导演将黄秋生的角色又一分为二(实际上港版也是有两个人,但另外一个警官没什么戏份),电影最后Dignam(可以想象他曾经也必然是卧底)杀死Sullivan也成为了影片绝佳的一个结局。在这个正义与邪恶错综复杂,警察与罪犯身份交织的世界中,复仇或许比法律手段来得更加容易。此外,众多时段打乱时空的平行剪辑,使得情节发展流畅而迅速。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众多演员具有爆发力的演出为影片深化了角色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