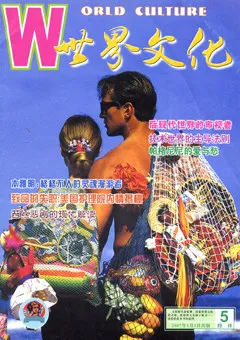后现代世界的审视者
电影《黑客帝国》中,导演沃卓斯基兄弟用以下场景向他们所崇拜的鲍德里亚致以敬意。在电影里,救世主尼奥翻开了一本由鲍德里亚所写的名为《拟像与模拟》的书,而这本绿色封皮的“书”里面装的则是一张与全世界人民性命攸关的光盘。
当地时间2007年3月6日,经过长久的病痛折磨,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静静地在他巴黎的寓所中去世。至此,亲历法国“五月风暴”、投身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68一代”知识精英集体谢幕,只剩下他们的宗师——99岁的列维·斯特劳斯仍然顽强地活着。
我们普通大众之所以能够与这位思想庞杂晦涩、言辞犀利、激励人心但是也富有争议的当代法国思想家在现代“消费社会”邂逅,那就得感谢鲍德里亚的书迷——导演沃卓斯基兄弟了。沃卓斯基兄弟正是通过《黑客帝国》中的以下场景向他们所崇拜的鲍德里亚致以敬意。在电影里,救世主尼奥翻开了一本由鲍德里亚所写的名为《拟像与模拟》的书,而这本绿色封皮的“书”里面装的则是一张与全世界人民性命攸关的光盘。电影中类似于施洗者约翰角色的孟菲斯对尼奥说:“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这句台词事实上也是原封不动地掠美鲍德里亚的原话。在拍摄《黑客帝国》的续集时,导演沃卓斯基兄弟(从去年开始变成了姐弟,因为哥哥拉里做了变性手术)还积极地与鲍德里亚联系,请教他对于剧本的看法,要求剧组所有人都认真阅读《拟像与模拟》。考虑到这本出版于1981年的书到1994年才翻译成英语在美国出版,而电影拍摄于1999年,沃卓斯基兄弟已经算是善于追逐理论潮流的了。然而鲍德里亚却认为这兄弟俩的读解“主要是基于误解”,并且拒绝了他们改编剧本的邀请。尽管如此,骨灰级的“黑客迷”们还是将鲍德里亚奉若圭臬,视他为“黑客帝国之父”。
让·鲍德里亚(1929~2007)出生于法国东北部阿登省兰斯一个农民家庭。对于自己的童年生活,他后来回忆说:“祖父一生务农。父亲是一位公务员,未到年龄就退休了。”鲍德里亚说,在他的家乡,农民是懒惰的,他们从不拼命工作,只是维持着劳作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农民们付出的,正是由土地和神袛们带来的东西,他们不需要多生产些什么。他自嘲地说,这是一种懒惰的策略,一种致命的策略,他自己就感染了这种懒惰的世界观,对市民社会中那种惟利是图的主动精神、竞争风格表现出明显的反感,而把懒惰看作是一种“自然”的力量。
但是鲍德里亚并没有选择这种乡村生活,而是成为家庭中惟一一位研究学术的人,一个在后来反对符号统治但又用符号进行写作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这就是“同父母决裂了”,也是与他的乡村生活的决裂。当然,这仅是一种“虚拟”的决裂,在他的心灵深处,鲍德里亚还总是存留着对乡村生活的眷恋,日后的鲍德里亚似乎总是处于这种虚拟决裂的状态。
这种心态也影响了他后来的理论风格,那即是总是走向边缘化,总是与现有的东西进行决裂。先是由马克思,走向后马克思思潮,然后是同弗洛伊德主义和福柯决裂,接着是同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甚至是后现代主义决裂,在根本上是同“现实”本身进行了决裂。而这种决裂由于上世纪60年代之后那种乌托邦精神的消失,从而走向了一种悲观的境地。
就世人而言,鲍德里亚更多地被视为是一位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
一位美国学者指出——让·鲍德里亚是迄今为止立场最为鲜明的后现代思想家之一。而鲍德里亚的追随者则称赞他为新的“后现代世界”的守护神。他给后现代场景注入了理论活力,他是新的后现代性的超级理论家。更重要的是,鲍德里亚发展出了迄今为止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极端的后现代性理论,这些理论极具渗透性,影响到了文化理论、现代媒体、艺术等各个层面的话语。
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在《理解媒介文化》一书中,把鲍德里亚的理论比喻成暴风雪的来临,是“当前所见到的最精密复杂的对大众传播的后现代性批判”。这一论断给人一个提示,要深入、透彻理解鲍德里亚的“传播媒介理论”,就必须融入他所描述的那个后现代性的社会文化景观—— 一个由时尚符号、电子媒体主宰的世界。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在一个后现代语境中去把握鲍德里亚的思想。
鲍德里亚也是一个悲观的媒介技术论者。对传媒的讨论是鲍德里亚理论架构中的主题之一,电视、网络、广告都是他关注的焦点。在研究方法上,他采用了符号学、心理分析和差异社会学等研究范式。在信息传媒手段高度发达的情形下,他直接追问人的本质和人的意义,摒弃了意识形态等诸多社会因素,把传媒技术和人的最终迷失和堕落作为一对因果关系。这一方面为人们开辟了思考的新疆域,为人们冷静、理性地重新审视新型文化提供了一条路线。大家普遍认为,他是第一位反思“新型文化”的思想家。但另一方面,过分强调媒介的作用又使他极容易落入客体主义的陷阱中,落入“万事无一物”的虚无。
虽然研究界倾向于将鲍德里亚定位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但鲍德里亚自己却不认同这种看法。他说:“对于这种‘后现代的’诠释,我不能做什么,那只是一种事后的拼贴。在拟像、诱惑和致命策略这些概念里,谈到了一些与‘形而上学’有关的东西(但也没有想要变得太严肃),而‘后现代’则把它转化为一种知识界的流行效应,或者是因为现代性的失败而产生的征候群。由此来看,后现代自己就是后—现代:他自己只是一个肤浅模拟的模型,而且只能指涉它自己。”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更愿意把鲍德里亚看作是一位文化思想家,他认为,在所谓“后现代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证过程中,鲍德里亚的思想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伊哈·哈桑则“将他归入政治哲学家一类,名列马尔库塞之后,但位居哈贝马斯之前”。如此这样排名,应该与鲍德里亚早期的“符号马克思主义”分析消费社会有关。凯尔纳在《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则把鲍德里亚作为一位形而上的诗意哲学家来进行定位,并且重点批判了他后期的虚无主义哲学。到底把鲍德里亚放入怎样一个理论坐标里去考察?学者们的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定论。
有人问鲍德里亚:“您是哲学家、社会学家、诗人,以上皆非或以上皆是?”鲍德里亚回答:“我既非哲学家亦非社会学家。我没有遵循学院生涯轨迹,也没有遵循体制步骤。我在大学里教社会学,但我并不认为我是社会学家或是做(专业)哲学的哲学家。理论家?形而上学家?就极端的角度而言才是。人性和风俗德行的思索者?我不知道。我的作品从来就不是大学学院式的,但它也不会因而更有文学性。它在演变,它在变得比较不那么理论化,也不再费心提供证据和引用参考。”
其实,这种理论归属的流变性和透明感,不仅反映了鲍德里亚整个理论发展的轨迹,也为把他最终定位为后现代思想家作了很好的注释。他的理论中充满了对同一体系、总体化的拒斥,崇尚差异性,强调瞬间感的话语。他的叙事体系缺少严密的理论论证、常常流于空洞的说教,而且行文时思想跳跃性强,文字怪诞,使我们在理解他的思想时会遇到不小的障碍。另外,对符号现象的分析是鲍德里亚的理论基点,符号结构体系支配着现实世界,拟像、仿真是符号结构支配的形式和手段,在后期,鲍德里亚甚至把这种符号结构用“全能符码”这一抽象的概念来描述,有人认为,鲍德里亚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以一种“总体性”去取代另一种“总体性”,理论上的悖论存在于他所信奉的那种反总体化的观念中,这种悖论同样也存在于其他许多后现代理论家的理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