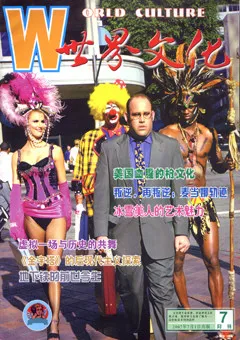父亲·母亲·牛皮癣:厄普代克的童年记忆
1932年3月18日,厄普代克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伯克斯县的先令屯镇。在厄普代克来到人世前,美国爆发了一场经济大灾难,即始于1929年的大萧条。到1933年,美国的工业产值下降到萧条前的三分之一,数千家银行关门,近1300万人失业。城市中充斥着救济平民的流动厨房,农民的粮食由于无法卖掉而腐烂。伴随着经济萧条的便是整个社会的动荡和人心的浮动。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6岁的厄普代克已经懵懂地开始记事。1945年,战争结束时,厄普代克也刚好结束了自己的童年,离开了先令屯镇。虽然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才正式加入战争(1941年12月7日),但随后的几年中,战争几乎影响到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厄普代克这个普通的家庭。6至13岁期间的厄普代克也许无法理解家庭、美国和世界的危机,但毫无疑问,童年时代关于家庭的模糊记忆,对厄普代克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父亲、母亲和自身的疾病尤为值得一提。
首先是父亲的形象让厄普代克终生难忘。美国和世界的变故对厄普代克的影响是间接的,但却直接改变了厄普代克的父亲威斯利·拉塞尔·厄普代克的生活。老厄普代克出生于1900年,逝世于1972年。当他年轻力壮的时候,却因为经历萧条和战争的破坏而找不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他曾经做过电报员,但不久后就下岗了。根据厄普代克后来的说法,在童年时代,工作对他的家庭来说是奇缺的。历经周折后,威斯利才于1934年在先令屯镇高中谋得一份职位,教授中学数学,年薪1749美元。这不是他梦想中的工作,但还算稳定,基本可以维持家庭的运转。父亲对贫困的恐惧、无奈和坚韧态度;对家庭的平凡而持久的爱护;对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的高度责任感(老厄普代克一直坚守讲台30年)深深影响了厄普代克。在第三部长篇小说《马人》(1963)中,厄普代克所塑造的那个散发着基督光辉的父亲卡尔德威,便是以他的父亲老厄普代克为原型的。
其次是母亲对厄普代克走上文学道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厄普代克的母亲琳达·格雷丝·霍耶尔是一位执著的文学发烧友。她生于1904年,1989年离开人世。如果说父亲的命运告诉厄普代克,什么是真实的生活,如何坚强面对它,那么母亲的独特爱好却启示厄普代克,什么是艺术的生活,如何超越现实世界。琳达年轻时在康奈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嫁给威斯利·厄普代克后,成了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不过她始终用一种超脱的方式坦然面对现实的困扰,那就是对文学的热爱。于是,在厄普代克的记忆中,留下了关于母亲的这样一段影像:“我最早的记忆是看她坐在写字台旁。我羡慕她的写作文具,打字机橡皮,一盒一盒的清洁打字纸。我记得装了原稿的黄牛皮纸大信封,原封寄了出去,又原封退了回来。”
在母亲的潜移默化影响之下,年幼的厄普代克对神秘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遭受无数次的退稿之后,1960年,琳达终于在《纽约人》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译文》。而她后来的大多数短篇小说都发表在这本杂志上。在很长时间里,厄普代克一直把《纽约人》当成心目中的文坛圣地,并以能加入其中为荣,可能同母亲的影响有关。就算后来离开了《纽约人》,他依然把这本杂志当成表达思想的阵地和大本营。
琳达主要写小说,不过直到1971年才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迷魅》。此后她再接再厉,笔耕不辍,直到临终前才出版了第二部小说集《掠夺者》,而这部作品集也引起了文坛的一些注意。可惜她来不及享受这份喜悦就散手人寰。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厄普代克无意中发现自己初中二年级时所写的一个剧本。厄普代克饱含深情地说:“我发现她已很小心地把它用打字机打出来。她实在是任何作家所必需的好母亲。”
琳达尝试过写长篇小说,但没有成功。她的短篇小说发表的也不多。虽然没有成名,但厄普代克丝毫没有怀疑母亲对自己后来走上文学道路的深刻影响,他说:“她的努力、她的灵感却传授给了我”。后来厄普代克确实成为了文坛的常青树,20世纪一位罕见的勤奋又高产的作家,以至于评论家的脚步永远跟不上他发表作品的速度。
1945年,13岁的厄普代克离开了先令屯镇。对于童年的结束,厄普代克不无伤感地写到:“那个夏天,战争结束了;那个秋季,我家突然活动起来,从那间大白屋子里搬了出去。我们是在万圣节前夕搬走的。”厄普代克就这样离开了先令屯镇,这块既让他自豪又让他忧伤的土地。后来,厄普代克以先令屯为原型,虚构了一个叫奥林格的小镇,并以它作为自己很多作品的故事背景,从而传达出作家一种独特的怀旧情绪,即对平淡简朴的小城镇生活的眷念。
最后,童年时代的疾病成为厄普代克一生的隐痛。厄普代克走上作家之路是相当坚定的,也是异乎寻常顺利的。1954年,厄普代克以优异成绩从哈佛毕业。按照厄普代克自己的话说,“哈佛的岁月就像田园牧歌一样,是非常成功的”。同年厄普代克接受诺克斯奖学金的部分资助,和妻子在牛津的普斯金绘画和美术学校学习一年。在牛津期间,著名的编辑和作家E.B.怀特拜访了他,并诚邀他担任《纽约人》专职作家的职位。这是厄普代克期待已久的事情,他自然欣然接受。
1955年,厄普代克回到美国,他把自己的小家庭安置在一个河畔公寓里。他把一切杂事抛之脑后,开始专心为《纽约人》的“话说小镇”栏目写稿。虽然只有23岁,但厄普代克已经开始向世人展示自己优雅、老练和睿智的风格。由于经常在《纽约人》上发表作品,并受该杂志风格的深刻影响,厄普代克和塞林格(1919—)、约翰·契弗(1912—1982)等人一起,被称为“纽约人派”作家。
“纽约人派”因塞林格、厄普代克等作家的短篇小说首先在《纽约人》上发表,然后才结集出版而得名。该派作家具有一些共通的风格:在内容上,他们偏重写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家庭纷争和夫妻关系,所以他们的作品被称之为“社会风俗小说”;在艺术手法上,他们坚持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注重讲述故事和塑造人物,相信事实和生活;在艺术策略上,他们不注重社会全貌的刻画,而是善于通过小人物和小事情来“以小见大”,折射社会风尚和精神的变迁;当然,在20世纪的氛围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借鉴融合了现代、后现代主义的艺术精神。
正当声名鹊起之时,厄普代克却突然离开了《纽约人》杂志:1957年5月,厄普代克迁居到马萨诸塞的小镇伊普斯威奇。伊普斯威奇靠近海岸,离波士顿北部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厄普代克对这个地方显然很满意,他在此居住了17年,直到1974年离开。人们纷纷猜测厄普代克隐居乡镇的真实原因。解铃还须系铃人。厄普代克从《纽约人》辞职,最公开的原因就是他试图突破自我,寻求新的创作素材和思想。他的选择表明,他遵从了福楼拜对作家们的建议:要成为一个大作家就必须像中产阶级那样生活。在伊普斯威奇,厄普代克的工作习惯高度有序。他在小镇中心租了一个办公室,规定自己每天的目标是写三页。早晨写短篇小说、中午写诗歌、评论和处理出版事务。这次迁居割断了厄普代克和纽约文坛的直接联系。作为一个文坛新人,显然是一次冒险活动。因为稍不留神,他或许将就此从文坛销声匿迹。但不久后,厄普代克的冒险得到了回报。自1959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贫民院集市》之后,厄普代克不仅继续在文学的“短跑”项目,如诗歌、散文、短篇小说上凯歌高奏,他还一跃成为美国文坛第一流的“中长跑”选手,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数次将国家图书奖等重量级的文学大奖收归囊中。更重要的是,他用几十年的心血、22部长篇小说,精心构筑起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中产阶级史诗”。相比于《荷马史诗》开创的“英雄”史诗传统,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为主导的“反英雄”史诗传统(资产阶级史诗),厄普代克的长篇小说无疑是典型的“非英雄”史诗,最日常化的史诗,但也是最难书写,最容易引起共鸣的史诗。
厄普代克迁居伊普特维奇这个偏远郊区,远离纽约繁华喧闹的花花世界,其实还有一个更隐秘的动机。1985年,厄普代克在《纽约人》上发表了一篇自传性文章,承认自己一直患有严重的牛皮癣。这种遗传的疾病导致皮肤生长过快过多,遮住了原先的皮肤。近些年,只有通过晒太阳才逐渐减轻了痛苦。在英国的一年期间,由于缺乏阳光,医生把他的病症归入到4-F级。厄普代克不仅将疾病带来的痛苦写进了长篇小说《马人》,他还在1989年出版的自传《自我意识》中专辟一章,回忆自己这么多年来在肉体和心灵上同牛皮癣的战斗历程。在回忆中,厄普代克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这种6岁就患上的疾病不仅是他逃避纽约的重要动因,也是他逃避公众生活,选择作家道路的主要理由。
比厄普代克年轻一岁的苏珊·桑塔格,对“疾病”所带来的比肉体更可怕的精神压力可谓有切肤之痛。她将这种精神上的压力称之为“疾病的隐喻”。在44岁时,桑塔格患上了乳腺癌,比身体的痛苦更痛苦的是另一种更可怕的痛苦,那就是来自社会的偏见和歧视。因此她在著作中写道:“疾病(曾经是肺结核,现在是癌症)本身唤起的是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备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虽然牛皮癣在严重程度上不能和癌症相提并论,但它给厄普代克带来的恐惧感、自卑感和绝望感,以及对社会的重新认识程度绝不亚于乳腺癌带给苏珊·桑塔格的。
厄普代克袒露到,他一直因为自己的皮肤而羞愧,所以从小他就打定主意,长大后要避免从事受到公众广泛注意的职业。父亲的教师职业显然不适合自己,因为在温暖的季节,自己的皮肤很容易暴露。而母亲室内创作的影像刚好深深印在他的记忆之中,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只需在封闭环境中工作,别人看不见工作内容的,只需用作品和外界打交道的作家行业。厄普代克还认为自己早期的婚姻是皮肤所造就的,因为当他发现有一个可以原谅他皮肤的女人时,他便害怕失去她而找不到第二个。他后来之所以迁居伊普斯威奇,答案也随之明了,因为那里靠近海岸,可以经常晒日光浴,治疗自己的皮肤。
然而,厄普代克不是塞林格那样的隐士。在他的一生中,除了青年时代的英国漫游,此后还有三次重要的出国经历。第一次是1964至1965年,作为美俄文化交流团的一员,厄普代克前往前苏联和东欧的罗马利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访问。回国后,厄普代克将这次国外访问经历,连同他的作家生涯共同转化为中篇小说《贝赫:一部书》(1970)。第二次是1973年,受福布赖特法案基金赞助,厄普代克作为林肯讲师团成员寻访非洲,并在加纳、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发表演讲。回国后不久,非洲的所见、所闻和所感被写进了《贝赫回来》,尤其是《政变》之中。1992年3月份,厄普代克得以第三次出国,前往巴西进行一个星期的考察学习。回国两年后,他便出版了长篇小说《巴西》(1994),纪念这段宝贵的旅程。
这些经历表明,厄普代克通过写作完成了精神上的自我拯救和确认后,他同样渴望回归到广阔的现实世界之中。而在他笔下,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都是非常正常、丰富和公众化的,这表明在厄普代克的心灵深处,他一直期待着像一个普通人那样获得社会的接纳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