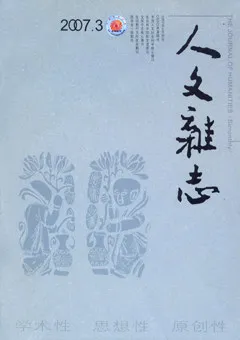论艺术变异的建构功能及形成机制
内容提要 现代艺术将变异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不论是现代艺术还是传统艺术,变异是其根本法则,艺术建构本质上是一种变异建构。变异具有独特的建构功能和美学意义。艺术的变异建构是在感觉、情感、智性等诸多层面进行的综合心理活动。
关键词 变异建构 感觉 情感 智性
〔中图分类号〕J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7)03-0122-04
变异是现代艺术区别于传统艺术的重要特征。现代艺术的理论家们对艺术变异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英国文学批评家斯班特就曾指出:变形“是现代艺术的主要成就,……现代的变形是艺术家解释、选择和变换形象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最新阶段,是传统发展到了尽头的时期。它是艺术游戏发展中的新转折,……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注:斯班特《现代主义是一个整体观》,见袁可嘉编《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页。)现代艺术对变异的高度重视,是与现代艺术对主观性、内向性特征的追求密切相关的。现代艺术更注重于心灵的真实,因而更追求对外部世界的变异与改造。
其实,不论是现代艺术还是传统艺术,变异是其根本的法则。普通的信息传播是以真实为基础的,艺术传达则与之不同,它传达的是一个变异的世界。艺术作为高度主体性的人类精神产品,在注重主体心灵真实的同时,客体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因此,艺术传达是一种变异性传达,艺术建构本质上是一种变异建构。
艺术建构具有变异性,首先在于人的感知具有变异性。从严格意义上说,外部世界永远无法复制。而且人类在感知外部世界时,那种所谓“纯粹的观察”是不存在的,人的感知受着“早先的经验和像需要、情绪、态度和价值观念这样一些重要因素”的影响。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冈布里奇提及,各个原始部族的人在对夜空中的狮子星座进行观察时会产生不同的知觉现象,对同一星座,有的部族把它看作一只白羊,有的部族把它看成一头狮子,也有的把它看作公牛、蝎子等,而南美的印第安人则将它看成一只龙虾。这说明,人的知觉与先在的心理结构有着必然关联,这种心理结构制约着人的感知,使得在感知的开始就把世界变异了。此外,人的任何感知都是特定的个体的感知。个体因素的差异,也带来了感知的差异,从而构成了与原物的距离。
艺术建构具有变异性,还在于艺术审美规律的自身要求。人对外部世界进行艺术掌握,是通过变异才得以实现的。从艺术创造的角度说,艺术不是生活的模仿,而是对生活的超越,变异是题中应有之义。“艺术不能提供原物”,雨果曾如是说。艺术若与原物等同起来,就等于取消了艺术。歌德曾辨证地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艺术家对于自然有双重关系;他即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他是自然的奴隶,因为他必须用人世的材料来工作,才能使人了解;他也是自然的主宰,因为他使这些人世的材料服从他较高的意旨,为这较高的意旨服务。”(注:《西方文论选》(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474页。)所谓“自然的奴隶”,是因为要利用自然所提供的材料,所谓“主宰自然”,意味着变异自然、改造自然。为此歌德又进一步提出:“每一种艺术的最高任务即在于通过幻觉,产生一种最高真实的假象。”(注:《西方文论选》(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446页。)人们不断发展的审美需求,呼唤着更多的艺术新形式的创造。诗歌作为主体意识高度自由张扬的艺术,这种变异就更为强烈与明显,所以雪莱说:“诗使它能触及的一切变形。”艺术提供的只能是一个变异的世界。
既然艺术建构是变异性建构,那么变异对于艺术作品的建构意义体现在哪里呢?
2007年第3期论艺术变异的建构功能及形成机制变异的建构性,表现在能进一步突出事物的某种特征,进而为创作主体的抒情表意做必要的铺垫。台湾诗人罗青的《柿子的综合研究》中这样写:“一个柿子/霍然的/落在我水平水平的床上/悲壮的/对我,摆出一幅/长河落日圆的姿态/使激动万分的我/差点成了一点孤鹜/一只盘旋而起的孤鹜/久久久久……/无枝可栖”。柿子放置于水平的床上,构成了“圆”与“平面”的组合关系,这一特征极像一幅“长河落日圆”图景,于是引起了作者的类似联想,这是视觉特征上的强化;有了这一变异性的强化,才有下文的第二次变异:“激动万分的我”几乎成了一只“孤鹜”,且久久无枝可栖,由人变异为鸟,进而实现了作者的抒情目的。
台湾诗人欧团圆写道:“我也是一把黑伞/在大雨滂沱的街头踯躅终日/固执地/撑开/一把黑伞像一幢流动的/空屋子。”“我”联想为“一把黑伞”,这一变异把主体的孤独感以及与滂沱大雨的对抗品格作了某种程度的强调;接着,“黑伞像一幢流动的/空屋子”,进一步作了变异,黑伞的漂泊不定、空虚等的特征进一步加以放大,从而突出了“我”此时此刻的特定心情。
变异的建构性,表现在它能进一步强化主体的某种情感。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写道:“等你,在雨中,在造虹的雨中/蝉声沉落,蛙声升起/一池的红莲如红焰,在雨中//你来不来都一样,竟感觉/每朵莲都像你/尤其隔着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特定的美好之物:红莲;特定的美好时刻:黄昏,“造虹”的雨中,使诗人产生了每朵红莲都像所等待的人的变异性感觉。这种变异,强化了主体的思念之情。
变异的建构性,表现在能凸现事物或事件的意义。余光中的《我之固体化》这样写:“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仍是一块拒绝溶化的冰——/常保持零下的冷/和固体的坚持。//我本来也是很液体的,/也很爱流动,很容易沸腾,很爱玩虹的滑梯。/但中国的太阳距离我太远,/我结晶了,透明且硬,/且无法自动还原。”此诗写于作者赴美求学之时,国家与民族的厄运使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遭受巨大创伤,身处异邦,一种落寞感、沉重感使他将自我封冻起来,异化为固体的冰,而且拒绝溶化。诗中用了不少物理学名词,加大了变异的客观化、理性化意味,发人深思。
变异建构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概而言之,变异建构能打通感觉之间的联系,扩大感觉范围,提供一种超越的美、变异的美。孙绍振指出:变异和超越是“一切艺术形象的普遍规律”。变异建构,打破了原来的感觉习惯和方式,用更新颖的感觉去表现之,因而它是超越原感觉的;同时因为它是在对原感觉的改变中实现这种超越、突破的,因而产生了变异之美。这种变异建构,给予读者的感官系统一次全新冲刷,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方式,读者也从中获得了新奇独特的美感享受。当洛夫在写出如下的诗句:“三粒苦松子/沿着路标一直滚到我的脚前/伸手抓起/竟是一把鸟声”时,他抓住的必然还有读者的惊奇与喜悦。
正因为如此,为了唤起人们更为丰富与新颖的审美感觉,艺术创造主体常常在变异上下功夫,正如布洛克说:“一件艺术品的表现力量常常是通过其解剖学意义上的不准确性得到的。”(注:布洛克:《美学新解》,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在他看来,不准确性,也即变异,是实现艺术品表现力量的重要途径。
艺术变异建构的形成有其产生的复杂的心理机制,是涉及感觉、情感、智性等诸多层面的综合心理活动。它首先体现在感觉层面。波德莱尔认为,“不变形,就无法感知。”我们知道,变异,在人与世界接触的第一步就已经开始,而艺术创造中的感觉变异更多地借助于艺术家感觉的强化,以及错觉、幻觉、印象、交感等心理状态之中。马尔库塞说:“感觉的强化能够达到直至把事物变异的程度,使得不能说的话说出来,使得其他方面看不见的东西成为看得见的。”感觉的强化产生于以下几种情形;对象的某种特征特别吸引了观察者;对象及对象所处的时空背景契合诗人的审美情趣;对象的特定存在与诗人特定的心情特别吻合。在上述情况下,诗人均会全身心投入感知,而使对象的某些特征朝着某个方面扩大、发展,最终变了形,从而产生出新的形象。
冯青的《月下水莲》更多属于审美感知强化下的变形:“原来/弹着笙的/竟是月亮/把一片屋顶/淹成荷塘//原来/满地的水莲/都是泡沫/让月的镰刀/一朵朵割破”。因为月色如水,所以有“一片屋顶”“淹成荷塘”的变异;因为月是弯的镰刀形,所以“满地的水莲”似被“一朵朵割破”。诗人在变异当中重新组合创造了一个美的境界。
错觉是对外界事件不准确的知觉。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荀子就注意到不少错觉现象。如“冥冥而行者,见寝面以为伏虎,见植林以为后人也,冥冥蔽其明也”。“厌目而视者,视一以为两;掩耳而听者,听漠漠而以为汹汹”。(注:见《荀子•解蔽篇》。)艺术中的错觉,是艺术家有意为之,或将经验中的错觉强化后注入到作品中,造成有意的变形以增加表现力。例如舒婷《路遇》中:“凤凰树突然倾斜/自行车的铃声悬浮在空中/地球飞速地倒转/回到十年前的那一夜”。这是与旧友猝然相逢而产生的错觉,其中既有视觉错觉、听觉错觉,又有空间具象错觉、时间错觉。多种错觉的交汇,强烈地表达了诗人与友人不期而遇时的心理感受。
幻觉是在没有直接刺激的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虚幻知觉,是瞬间感觉的变异。诗人借助幻觉,创造一种亦真亦幻、似真似幻的境界,以表达特定的情绪。比如:“目光自窗沿飞向窗外/顿时之间一根窗棂应声断裂/我走了过去。有一些白墙灰掉在舞鞋上/一下之间挥发出粉红的船片”(郭大篷:《着色断层》)。目光望向窗外,窗棂应声断裂,实际上并未断裂;白墙灰掉在红舞鞋里,红舞鞋一下子变成粉红的船。这都是视觉产生的幻觉,使本来静态的事物发生强烈变异,使本来小的事物突然变大,这就大大增加了感觉的刺激力。
文艺理论家、诗人赫斯列特曾说过:“如果能传达出事物在激情的影响下在心灵中产生的印象,它是更为忠实和自然的语言了。”(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一册),第60-61页。)他所说的:“忠实和自然”显然是针对心灵感受而言的。印象是属于“视觉后”的内容,是感觉留在心灵中的最深刻的印痕,具有强烈的主体感受色彩。比如辛笛的《航》:“风帆吻着暗色的水/有如黑蝶与白蝶/明月照在当头/青色的蛇/弄着银色的明珠”,这里的“黑蝶与白蝶”、“青色的蛇”、“银色的明珠”都是由瞬间印象幻化出的变异意象,从诗人的心理现实来说它是真实的,而对于外界现实来说又是经过改造的,有着较大的变形。
艺术的变异更多地借助于通感手法。德国美学家费歇尔曾说:“各个感官本不是孤立的,它们是一个感官的分枝,多少能够相互代替,一个感官响了,另一感官作为回忆、作为和声、作为看不见的象征,也就起了共鸣,这样即使是次要的感官,也并没有被排除在外。”(注:《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6页。)这种感官的共鸣现象,被称为通感,其本质就是变异。通感现象在人类经验世界里是普遍存在的,并反映到日常语言中,比如形容声音太大,说“刺耳”,是听觉与触觉相通;形容颜色太鲜艳,说“刺眼”,是视觉向触觉挪移;形容声音好听,说“甜美”,是听觉与味觉旁通。对这些现象,钱钟书作过概括:“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动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含有锋芒。”感觉的变异,从表达上看,有助于抒写难写之情,表达难言之感。在日常审美活动中,使用得最多的是视听觉,触嗅味三觉使用的较少,这是实情。使用的多与少,还有一个原因是与感官的有效范围有关联,视听觉可在较大范围发挥功能,嗅觉味觉与触觉只能近距离或零距离接触时方能发挥功能。正因为这种距离感和对身体和器官的依赖性,嗅觉、味觉、触觉有较大的内在性、隐秘性,而视听觉则较为开放与自由。因此在表达感觉时,嗅觉、味觉、触觉存在着较大的限制。比如说,触觉当中的痛觉,在直接表达它时只能说“很痛”、“非常痛”、“痛死我了”等等。但如借用别的感官则可以把这种“难写之情”、“难言之感”表达得可感可触、有声有色。例如《水浒》中写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时,第一拳“正打在鼻子上”,作者不直接写镇关西的痛觉,而转向写味觉感受:“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第二拳打在“眼眶际眉梢”,作者转而写视觉反应:“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红的、黑的、绛的,都绽将出来”;第三拳,“太阳上正着”,转向写听觉感受:“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这就把内在的痛感外化出来,变得可嗅、可见、可闻。这都是感觉的变异与变通,倘若不借助这种变异,不仅在艺术表达上不可能有这种效果,而且这种痛感本身也难以真实传达出来。
艺术的变异建构需要借助情感的力量。列•托尔斯泰说:“诗是心灵之火,这火能点燃、温暖、照亮人心。”赫斯烈特也说:“诗是幻想和感情的白热化。”诗人怀着火一般的白热化的感情感知世界,在激情的冲击下,外部世界的变异就更为明显强烈。在日常经验世界里,情感使外界事物变异的例子举不胜举。诗歌中,表现爱、思念、离别、忧愁的,都可造成变形。这是余光中的《空城夜》,写离别后深夜对妻子的思念:“而到深夜,繁楼复窗/一丛丛,一簇簇,流漾的灯火/相继被海风吹灭了/……你偶尔留下的指纹/在我腕上,便夜光表一样地/幽幽亮起,证明所谓奇迹/……也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妻子留下的指纹能在自己手腕上像夜光表一样发亮,这是一种幻觉,是情感催动之下对客体的变异感知。在情感作用下,不仅客体会发生变异,主体自我也会变异。这是席慕容《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在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为了获得爱情,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极言感情的深沉真切。于是“我”变了,变成了一棵树,开满盼望之花。
情感的另一强化形式是移情。移情是“把自己内心同情所产生的那种心情移置到对象上去”(注:《西方美学史》(下),第617页。)移情强调的是从主体的情感需要出发对自然进行变形,它造成的既是“对象的变形”,又是“自我的变形”。移情是设身处地的写法,是把客体拟人化,客体获得人的情感,客体就不再是原先的客体。这是唐亚平《我就是瀑布》中所写的:
我就是瀑布/在沉睡的梦的边缘截断阴河/变成疯独的裸女/谁也不敢亲近我谁也不能占有我/……我是个悲愤得颠狂的女人/……我是高原女人是十万大山膘悍的妻子
在移情的作用下,“我”变成“瀑布”,“瀑布”也变成了“疯狂的裸女”,变成“颠狂的女人”,变成大山“膘悍的妻子”。人既获得了瀑布的特征,大自然的瀑布又获得了人的情感、人的精神,在形体变异中推进了诗情的升华。
前苏联心理学家列昂夫在维果茨基《艺术心理学》序言中说:“情感、情绪和激情是艺术作品内容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在作品中是经过改造的。就像艺术手法造成作品材料的变形一样,艺术手法也造成情感的变形。”(注:《艺术心理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此语相当深刻。情感使客体变异的同时,本身也必然随之变异。
艺术的变异建构还在于智性的参与。相对于感觉与情感,智性对于外部世界的变异就更为主动、自觉、自由。作为精神产品的艺术创作,虽然感觉与情感是占第一位的,但要使它成为一个独立体从心灵中诞生出来,无不经过理性头脑和智性眼光的加工处理。作家萧殷就曾说:“艺术形象应该是作者把他所感受的生活印象和事实,经过他自己的世界观和美学观点的改造,经过融化和概括,塑造出既具有一般意义的、又独具个性的形象。”这里所说的世界观和美学观点,均属于智性范畴。台湾诗人戴天的《造像》一诗,即是从某一种观念出发进行的变异:“阴影中的脸孔/没有眼睛/阴影中的脸孔/没有耳朵/阴影中的脸孔/没有鼻子/阴影中的脸孔/没有脸孔/阴影中的脸孔/看不见东西/阴影中的脸孔/听不见声音……”诗所描绘的是这样一种人:明哲保身,不分是非,关键时刻总把自己隐藏起来,态度暧昧。为此诗人在“脸孔”中作文章,给以巨大变形,变成“无眼”“无耳”“无鼻”,近乎荒诞,却有很强的理性逻辑穿透。
英国美学家罗杰•佛莱则从读者接受这个角度谈了艺术对生活的变异关系,他说:“对于艺术,我们感觉的第一个品格是秩序,没有它,我们的感觉就会受到麻烦和困惑;另一个品格是变化,没有这个变化,它就不能完满地刺激感觉。”(注:罗杰•佛莱:《视觉与构图》,第33页。)艺术传达是变异传达,变异建构是艺术的根本途径。艺术创造主体通过变异性的艺术传达完成了艺术文本的建构,变异也就是创造。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心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