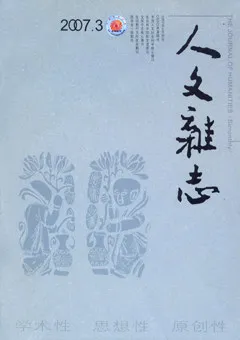J·德里达之后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欧洲大陆出现了一个哲学的后H.-G.伽达默尔、J•德里达的时代,令人忧虑的是, 在世界范围内至今还没有像样一点的新的哲学思想的出现。在这样的时代,作为他们的学生 ,我们肩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应该做些什么?能够做些什么?这些问题,我们无法回避。对 他们本人的哲学思想,我们应该在中国现实生活和思想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独立的 研究成果。而对于他们的欧洲学生,我们是处在同样的学术起跑点上;特别是当他们对中国 的哲学发表意见时,我们提出不同的看法甚至批评,是一件很正常也是很平常的事情。我们 对自己应有起码的自信。 本文还用中文“机”诠释了arche(始基)、Geschick(命运)、 Wesen(存在并活动着)、Zeit(时间)、Dialog(对话)等西方哲学的基本词。
关键词 哲学的后J•德里达时代 命运 责任 自信 机 哲学行 动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 X(2007)03-0001-08
1、上个世纪六十年代,J•德里达和H.-G.伽达默尔共同开创了一个M.海德格尔之后的欧洲 大陆哲学的时代。而当时M.海德格尔本人还健在,他去世是在七十年代。现在,随着H.-G. 伽达默尔、J•德里达他们两个人的相继去世,欧洲大陆出现了一个哲学的后H.-G.伽达默尔 、J•德里达的时代。所不同并令人忧虑的是,在世界范围内至今还没有像样一点的新的哲 学思想的出现。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作为他们的学生、学术后来者,我们肩负有什么样的 责任?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这些问题已经摆到了我们面前,我们根本无 法回避。
2、有人说,在哲学上,看起来我们是可以和西方特别是欧洲大陆的哲学家进行一种平等的 对话了。事实上,在H.-G.伽达默尔、J•德里达那一代哲人去世之后,我们与他们欧洲的学 生、学术后来者处在差不多同一个起跑点上。和他们一样,我们许多中国人在法国或德国都 直接受教于J•德里达、H.-G.伽达默尔。我们对他们法国或德国学生、学术后来者的哲学根 底一清二楚;特别是当这些学生、学术后来者在对中国的哲学发表意见时,他们又缺乏我们 中国学者身上所固有的长期的中国生活的经验和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当然,也包括中国的 语言文字方面的悟性、知识和运用能力。在J•德里达、H.-G.伽达默尔的哲学语境中,这种 语言文字方面的悟性、知识和运用能力,常常直接决定着一个哲学家的水准。因此,对他们 的一些见解提出不同的看法甚至批评,是一件很自然、很正常也是很平常的事情。提不出不 同的看法甚至批评,那倒反而不正常了。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起码的自信。同时,这也是 以实际的哲学行动来维护自己民族的哲学与话语的权益所需。这是每一个中国的哲学工作者 应该做的,也是责无旁贷的。
身处H.-G.伽达默尔、J•德里达之后的时代,这种自信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有了这种自 信,我们就知道:在哲学上,我们中国的学者该怎么做了,我们中国的学者能做些什么了。 在这个意义上,有自信,也正是有哲学的表现;有哲学,就会自信。
3、古希腊有过一个词arche,本是“开端”、“发生”的意思,被很多中国译者翻译成“始 基”,它的意思是:“始于此,亦终于此”。中国的“机”字有着类似的意思,“万物 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注:转引自《庄子集解》〔清〕王先谦、刘武撰,中华书局,2004年 版,第155页。)由此可见,“机”这个中国词,也有着不可小觑的哲学价值。而 从人的生存、人生经验来讲,凡事都讲个“机遇”和“缘分”,中国人还把这两个词再组合 成一个词:“机缘”。在M.海德格尔那里,与此类似的词有:Geschick 、Schickung,等, 它们通常被译成中文为:命运。我则愿意把它们译成“机遇”。“机遇”对于人生是非常重 要的。这种人的生存、人生经验,会使得“机”在哲学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体会到, 在人的一生中,一些偶然的遭遇、意外发生的事情,往往会重大地改变人生。在哲学活动中 也是如此,会使一个人豁然开朗,成为进入哲学的最佳契机。
我见到J•德里达可以说是一个“机遇”,甚至可以说,哲学在我身上的一次“发生”。大 概是1988年2月份,当时,他被邀请到德国的海德堡大学与H.-G.伽达默尔进行哲学对话。
那时,我正在伽达默尔身边研究解释哲学。我刚到海德堡大学不久,我还没有住进大学的客 座教授楼,暂时住在一个名叫Box的小山上。那天好像还下着雪。那次对话,听者云集,挤 满了大学的大讲堂。他们之间的对话主要是用法语进行的。我不懂法语,好在我旁边坐的是 大学法语系的老师和学生,时不时地给我翻上那么两句。这次对话,主要谈论M.海德格尔, J•德里达对总体性(Totalitaet)的批评引起了我的注意。当然,他对“总体性”的批评 , 除涉及独裁政权之外,主要是针对M.海德格尔包括H.-G.伽达默尔等人的哲学倾向的。与此 相关的是,后来我在他的著作中,感受到了他那种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维护本国哲学与话 语权益的坚定倾向。
其实,这次J•德里达与H.-G.伽达默尔所进行的哲学对话,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还不是他 们说了些什么,而在于这样一种哲学对话是如何实际地进行的,特别是世界两个哲学大师之 间的跨国、跨文化对话,是如何实际地进行的。这场对话,给我以触动,使我获得了一个对 于哲学的基本经验。具体到底是些什么东西,我当时还说不大清楚;但是,我能肯定:它会 重大地影响我以后的哲学生活。这种触动和经验,是不可能以读他们书的方式得到的。这使 我在那初遇H.-G.伽达默尔之后,更明确了:从事哲学,不能光读文献。
事后,H.-G.伽达默尔和我谈起这次对话,问我的看法。我说,我不懂法语,听旁边懂法语 的学生翻给我的意思,我觉得J•德里达并不赞成总体论。H.-G.伽达默尔对我说,是这样的 。不过,J•德里达和他的观点尽管有许多的不同;但是,他们都是从M.海德格尔走出来的 ,可以看作是M.海德格尔之后的两个分枝。他对于J•德里达的批评并无明显不快;相反, 言外之意,似乎是:M.海德格尔之后,我和J•德里达两人而已。
在我正式开始研究现象学-解释学的时候,我就把J•德里达作为理解H.-G.伽达默尔哲学思 想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参照点。这可能是在第一次听到他们的对话时就注定了的。实际上,还 不仅于此,后来我在研究E.胡塞尔、M.海德格尔时,也会常常甚至是不可避免地要看看J• 德里达的有关著作;因为,J•德里达发表了对E.胡塞尔、M.海德格尔哲学的不容忽视的见 解,包括对他们一些重要的哲学术语和词汇作出了独特的解读和解释、解构。
从这以后,我就比较注意J•德里达了,偶尔也找他的德文译本来看看,在和H.-G.伽达默尔 讨论哲学问题时,有时也会谈到J•德里达。有一次,讨论到文字作为“印迹(trace)”是 否有意义的时候,我说是有意义的,我以中国的书法为例:中国的书法,其意义并不在于写 者的意图、所写的字的内容,它作为书写甚至是与写者的意图、所写的字的内容毫无关系的 ;但是,这种书写本身、这种“印迹”本身却是有意义的,这种书写、“印迹”具有审美的 意义。我当时只不过是冒说一通,而且我这种认为“作为书法的书写具有审美意义”的看法 ,在中国很平常,有点文化的中国人差不多都能说得出来,更何况我在大学念过美术史。我 没有想到H.-G.伽达默尔听后会那么高兴,他对我说,在古希腊的时候,也有过书法这类东 西,但很快就在欧洲消失了,只有中国流传至今。因此,现代的欧洲人不大会从艺术的角度 去看书写了。当然,在他看来,我也为他批驳J•德里达提供了一件重要的武器,以致于他 在给我的《序》(关于《美的现实性》中译本的)中直截了当地写道:“因此,使 我们非 常突出地感觉到,书写和文字在中国美学文化中作为书法艺术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虽然,我们认为,对于古希腊的文字和绘画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在欧洲这种文化圈子里, 今天又有谁在文字学方面想到了绘画艺术呢?”(注:H.-G.伽达默尔《美的现 实性》,《外国美学》第七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他的最后这句话,我觉得 是直接指向J•德里达的。这使我感觉到,根据中国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化艺术等,可以作 出一些现在的欧洲人不可想象的事情来。
4、对E.胡塞尔的现象学的研究,在J•德里达的哲学生涯中,也应该受到关注和重视。在J •德里达看来,E.胡塞尔的现象学仍带有旧形而上学的倾向,这与那种不死的“在场”性有 关,它突出地表现在意义的在场性、语音的特权地位和直观中的被给予性。J•德里达把它 称之为在场的形而上学。在哲学上,J•德里达的目的是要颠覆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所以, 德里达就把书写与口语对峙起来,并把书写看作“印迹(trance)”,试图改写“意义”理 论。他论证说,这种“印迹”是比E.胡塞尔的语音、意义之类更本原的;这种“印迹”、书 写显示了一种死和不在场性,即主体的不在场和死亡;正是这样一种与死亡、不在场相关的 东西,才能起到再现和唤起意义的作用。这就是说,J•德里达找到了语音、意义之前的、 更本原的东西即书写、“印迹”,用一种死的、不在场的东西取代和超越了活的、在场的东 西,从而认为颠覆了语音中心主义和在场形而上学。到底能不能颠覆在场形而上学,暂先放 一边;J•德里达确是比较彻底地批评了欧洲近代哲学的“主体性”。相比之下,在E.胡塞 尔的现象学中,“主体性”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作为书法的书写具有审美意义”这个说法,却证明了书写、“印迹”本身就有意义;因 此,书法、“印迹”和语音一样,同样具有意义的在场性。换句话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书写、“印迹”并不能也没有起到颠覆在场性乃至在场形而上学的作用,尽管在一定的意义 上它起到了批判语音中心主义的作用。
5、在现象学的发展中,首次突出“语言”问题的,是M.海德格尔。不少研究者认为,M.海 德格尔的突出“语言”问题,是在他的后期;而在M.海德格尔的前期思想中,“时间”占中 心的位置。应该F9RCH/RArzgEFJY2TuBfzg==说,M.海德格尔后期,更突出了“语言”问题。但是,尽管如此,我认为, 不应该用“时间”、“语言”来为M.海德格尔哲学的前、后期划出楚河、汉界,不应该以前 、后期的方式,把M.海德格尔前期的“时间”问题和“语言”分割、隔离开来。这样做,首 先会低估“语言”问题在M.海德格尔前期哲学思想的重要作用;其次,也不可能准确理解 和把握他的“时间”问题。一个基本的事实是,M.海德格尔最初的哲学思考,可以说是起步 于那本《论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种含义》,他把“含义”问题放到E.胡塞尔的现象学 的语境之中,又着重从词义、语言的层面去找出那最初的含义。即便单从“时间”的角度来 看,在他那里,也是与“词”、“语言”的问题无法分开的。
在《存在与时间》等前期著作中,M.海德格尔就从“词”、“语言”的角度来解读“存在” 了。他从词的含义而不是概念的定义,来确定“存在”的原初意义。而这种确定,包括通过 “存在”这个词从不定式到动名词这种语言的转变。动词不定式Sein加上冠词das,就成了 动名词 das Sein。就“存在”而言,动词不定式在动名词之前,是比后者较原初的。
M.海德格尔的用“时间”来解释“存在”,似乎还借助了动词的“时态”。例如:在德语中 ,“存在”(Sein)这个词是动名词;这个动名词Sein,原本是动词的不定式。ist、seien d、gewesen,它们分别是Sein的现在时、现在分词、过去分词,等等。用这种动词的不同“ 时态”,有利于理解和解释“存在”的“多种含义”。Sein这种动词不定式,我视为较原初 的。我称之为“较原初的”,就是说,还有比Sein更原初的。那些更原初的词,除了古印欧 语系中的之外,就德语本身而言,在M.海德格尔看来,那个更原初的词,是Seyn、Sein、is t等等,都只不过是一些辅助性的词而已。找到了Seyn,才最终完成了他对古希腊原初的“o n”在德语中、在日尔曼民族生存中的确认。有了这种确认,才可能产生德国的“存在论” 。他把“词(Wort)”看作是“Seyn”的“说(Sage)”;而“语言(Sprace)”则产生于 “词(Wort)”的“说(Sage)”。显然,“语言”、“说”与“词”之间又可以分出三个 层次。就这几个层次而言,“语言”并不是最初的。而“存在”的“多种含义”中的“最初 含义”,也就必须到那最初的发源地中才能找到。但是,一般人讲M.海德格尔的“存在”思 想与理论,只讲到Sein为止,并没有追索到更原初的,例如:Seyn。
从上面可以看出,不论是对“存在”的词义分析、词型转变的分析、时态的分析,还是找出 Sein之前的Seyn,都是在“词”、“语言”问题中作出的,是被置于“词”、“语言”的维 度中的。所以,从 M.海德格尔哲学的发生、起源的角度和意义上来看,他的“时间”观, 实际上也是产生于一种“词”源的追索和“语言”分析;至少是与上述密切相关的。对“时 间”的解读,在M.海德格尔那里,是与他的“词”、“语言”分不开的,甚至是要服从他的 “词”和“语言”观的。
再如,M.海德格尔前期思想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里的他的对词的许多用法,如Da-sein 、Um-welt、In-der-Welt-sein等等,这种对词的独特用法正是根据他对“语言”的独特见 解,是这些独特见解的实施和贯彻。这些做法,体现出了语言自身所固有的那种活生生的、 变动不居的和多义的特性。
6、词源回溯和用动词的不同“时态”来解释“存在”的“多种含义”,等等;M.海德格尔 的这些举措,把亚里士多德的“存在的多种含义”变成了一种德语的“词义”分析,从而具 有重大的哲学意义。就是说,以德语的词的组合变化和动词的时态形式,来处理古希腊的哲 学问题,把亚里士多德的“存在的多种含义”本土化了即德语化了,变成了德语的哲学问题 。这是走向哲学本土化的关键一步,进而可以从德语的独特结构和运用中形成德国自己的哲 学问题,用德语来讲德国自己的哲学。真正的对外国哲学的翻译、解释,目的就是要形成、 发展自己国家的哲学。在这方面,M.海德格尔堪称楷模。
但是,M.海德格尔流露出的那种优越感,似乎除了古希腊语之外,只有德语才配作哲学的语 言,以及他对拉丁文的批评,都引起了J•德里达强烈不满;尽管在反对语言霸权方面,J• 德 里达比较多地强调了反对英美霸权。而当J•德里达打算建立一种新的法国哲学时,也必然 要 维护自己本国的语言。除此之外,他的强调书写、“印迹”,所具有的这种反对语言霸权主 义的意义也不可忽视或低估;他的反对语言霸权,和他的反对语音中心主义,都是他所处的 生活的、哲学的边缘状态和心态的一种反映。J•德里达容不得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霸权 主 义,他毕生在为颠覆这些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而奋斗,并由政治的颠覆转而集中于语言的颠 覆。
这里,还涉及到对一个德文词的如何翻译问题。M.海德格尔有一个说法:Die wesende Spra che。这个说法很重要,而能否准确解释这句话,关键就在于对wesende这个词怎么理解和翻 译。wesende 是源自wesen;wesen在这里是动词,而不是名词; wesende是由wesen这个动 词所变成的 wesend,现在分词作形容词用,就成了wesende。如果wesen作为名词,第一个 字母就得大写,就成为Wesen,作为Wesen 是可以翻成中文的“本质”或“本性”的;不过 ,作为名词的Wesen是绝对不可以变成wesende的。wesen这个词,是被海德格尔作为动词并 标明了时间性,才成了wesend;因此,在这里不能翻译为“本质”或“本性”。它的意思应 该是:逗留、延续;也就是说:存在并活动着。而这些,正是存在的意义所在。这样一来, Die wesende Sprache就不能译成“语言的本性”,而应该被翻译成为:“存在并活动着的 语言”或“语言存在并活动着”。这样来译,语言就自己显示了它的生命,成为活生生的, 由此才可以称得上是生命之源、存在之家。我曾在《批判哲学与解释哲学》那本书里讲到过 wesen作为动词来理解的问题(注:郑湧:《批判哲学与解释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
7、从“作为书法的书写具有审美意义”这句话来看德里达与H.-G.伽达默尔的联系,可以 看 出,J•德里达用书写、“印迹”来取代口语,对于H.-G.伽达默尔而言,只是对艺术的经验 一种拓展而已,即可以不限于口语,完全可以拓展到文字上去。这就是说,从口语转变到文 字,并不能、也没有推翻H.-G.伽达默尔所建立的以艺术经验为基石的解释哲学(Hermeneut ische Philosophie)。
8、我所理解的解释学,是一种关于翻译的学问;而在解释学的意义上,哲学就是翻译学。 我之所以这样讲,一方面是根据M.海德格尔和H.-G.伽达默尔的看法和做法;另一面,后来 ,又有了我自己的切身体验和理解。
首先,M.海德格尔就是从翻译入手建立现象学-解释学的。把古希腊的“存在(on)”译 成了德语的Sein;并且,这个Sein是动词,也可以是动名词,但不是一个一般的名词。因此 ,On-tologie在德语中就成了:活动着的存在-说。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翻译,M.海德格尔建 立和形成了他的哲学存在论。这种存在论,着眼于Sein这个动词的不定式,把它看作是较原 本的东西;并进而又从Sein回溯到Seyn,找出最初的东西。这是就M.海德格尔的哲学理论建 立与形成而言。
而对于哲学本身,在M.海德格尔看来,哲学(Philosophie)中的Philo指的是一个人,他是 一个摩西那样的人,他把上帝的话和宗教典籍翻译成凡人能够听懂、读懂的语言,借以传递 上帝的意旨。既然,哲学以Philo这样一个译者的名字命名;因此,哲学就是一种翻译者的 智慧、学问。
再就解释学(Hermeneutik)这个词来说,词中的Herme,也来自一个人的人名即Hermes,He rmes是神的儿子,他负责把神的话译成凡人能听懂的语言,把神的意旨传达到人间。这就是 说,解释学也是以一个传话者、翻译者的名字命名的,由此而形成的哲学显然也是一种关于 翻译者的智慧、学问。
显然,在他们看来,翻译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枝节问题,而是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当年 ,我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跟着H.-G.伽达默尔搞解释学时,就是从这样一个问题入手的。1989 年4月,我在德国当时的首都波恩召开的题为《论海德格尔哲学的现实性》国际海德格尔哲 学大会上的学术报告,题目就是Chinesische-Heidegger-Gadamer-Uebersetzung(即《海德 格尔-伽达默尔的中文翻译》)。在这个学术报告中,我把翻译是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来讲的(注:这个报告后来被收到大会论文的第三集,于1992年出版。它的中文译本 ,也以《从翻译见海德格尔的理论基石——词的意义》为题被收入了我的论文集《批判哲学 与解释哲学》。)。另一方面,就是我做的翻译活动。在此之前,我已着手 把H.-G.伽达默尔的《美的现实性》译成中文。
可以说,我是从翻译问题和对H.-G.伽达默尔的《美的现实性》的翻译进入解释哲学的。而 据我所知,J•德里达的进入现象学-解释哲学,特别是“解构”哲学思想的提出,也是与翻 译有关。
在《致一位日本友人的信》中,J•德里达说:“解构的问题也是彻头彻尾的翻译问题”。 他 还说:“我当时希望把海德格尔的Destruktion 或Abbau翻译并采纳过来,为我所用。”J•德里达:《中国讲演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9-230页。他把M.海德格尔的那两个词翻译成法文的deconstruction。Deconstruction被置于“结 构主义”的语境中,就形成了J•德里达的被人们称为“解构主义”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 可以说,他的“解构哲学”本身,就是在翻译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
9、J•德里达与M.海德格尔、H.-G.伽达默尔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的相关性,当然远不至于 此 。比方说,解释哲学所需的宗教经验以及宗教所特有的那种视野。M.海德格尔就不必去多讲 了,他从小就在教堂生活(除此以外,当然他还带有一种德国山区农民的视野);而且,还 具有对天主教、新教特别是路德教的深厚学养。其学术生涯的起步也与这些密切相关。而在 J•德里达身上也十分明显,特别是犹太教的影响,尽管J•德里达本人不大愿意承认。犹太 教 特别尊重传统、重视对于宗教典籍的注释,在它那里,传统与注释是相互依存的,这是其一 。其二是,犹太教典籍还是人们代代注释的产物,而并不是神的原话,所以能被人们所理解 。这样一种注释,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地去神圣化、世俗化的过程。但在J•德里达看来,我 们人类还远没有进入世俗的时代。当然,这些典籍也是人们世代解读、翻译的结果。
10、尽管M.海德格尔、H.-G.伽达默尔都不重视甚至贬低文字;但是,解释学在传统上与文 字有关,例如,F.施莱尔马赫就曾说过,解释学是一种正确地理解别人的话特别是文字的艺术(注:郑湧:《批判哲学与解释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156页。)。不过,在理解文字的时候,切不可遗忘和低估了“书法”。
语言、文字问题,在现象学-解释学的产生发展中,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语言的发展 ,曾受到过数学的影响;后来,词又被抽象成概念,逐渐形成概念的系统,按照逻辑来推理 。这样,词就脱离了它原有的上下文、语境乃至具体的人的生存环境。而一个词,重要的是 它正在被说;它的意思,往往是被决定于说的不同的时间、场合等等具体条件和环境的,只 有在它原有的具体环境、语境中,才能自己显示自己的意思(词义),人们从而获得解读和 理解。现象学的意义理论,就是注重它的“说”,它在具体的语境中的自己“显现”。
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记忆犹新的是,一个词、一句口号的出现,都有其特定 的政治含义;这种含义靠形式逻辑是推不出来的。而且,这种含义所涉及的已经不是词义的 理解问题,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并且事关人的政治生命乃至肉体生存,人们必须 谨小慎微、出不得丝毫的差错。这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词所可能涉及的东西,不仅 仅越出了概念、逻辑的范围,而且越出了理论的范围,甚至会危及一个人乃至一群人的生命 。中国的学人,对于这些越出理论的事关生存的特殊状态并不陌生。所以,经历过“文化大 革命”的人,基于自己切身的生活经验,对于这样一种词义的现象学理论应该并不难理解。
在语言成为现象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后,语言本身的许多问题就被凸现了出来。其中一个, 就是“独白”还是“对话”的问题。
根据数学的榜样和概念、逻辑的要求,语言是单义的,也是“独白”的。“独白”的语言, 就成为旧形而上学的标准用语。H.-G.伽达默尔认为,要想在哲学上根本改变旧形而上学, 就不能不去改造它的语言;否则,就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形而上学。E.胡塞尔也好、M.海德格 尔也罢,他们把语言还是看成“独白”的,因而被认为未能彻底祛除形而上学的影响。
在语言是“独白”还是“对话”这个问题上,一块重要的试金石就是:自言自语。如何看 待“自言自语”?自言自语,是自己和自己说话,在E.胡塞尔、M.海德格尔看来,是“独白 ”。H.-G.伽达默尔则认为,自言自语是对话,他根据的是柏拉图的说法:“思想就是灵魂 和自己的对话,默默地和自己的对话”(注:柏拉图《泰阿泰德》篇,转引自《 道,行之而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这是H.-G.伽达默尔与 E.胡塞尔、M.海德格尔的不同;不过,他们之间的不同,仍然是发生在语言之中的。
J•德里达则把分歧扩展到了语言之外。在“语言”还是“文字”这个问题上,J•德里达把 哲 学的视角从“语言”转向了“文字”。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他把法语中的différence这个 词的后一个字母e改写成了a,就变成了différance。这两个词读音相同,但书写不同。而 书写的不同,显示了词义的不同。这说明,光靠读音是无法区别词与词之间的不同的;而书 写却能。仅就这一点,就可以表明,在词义的追究、分析方面,“文字”确有“语言”所无 法企及之处。当然,由此也可以指出语音的不足乃至语音中心主义的不足。
11、如何来看待J•德里达在现象学哲学里的发展和独特的建树?他的这些发展和建树又是 怎样成为可能的?如果可以作一个极简略的概括的话,那么,我认为主要有两条,一是:J •德里达把E.胡塞尔的“意向活动”变成了“语言行为”。二是:把M.海德格尔、H.-G.伽 达默尔的“语言”变成了“文字”。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可不可以说:J•德里 达是注重修辞学的,他是站在修辞学的立场上来批判逻辑学的传统的。
对于他的哲学立场,我们很难说“是什么”;同样也很难说“不是什么”。他自己就曾这样 说过:“解构不是什么?什么都是。解构是什么?什么都不是。”(注:J•德 里达:《中国讲演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235页。)
关于修辞学,我的看法是:站在修辞学的立场上来批判逻辑学的传统的,恰恰是H.-G.伽达 默尔的比较明显的哲学特征。他在《美的现实性》等著作中,特别推出了修辞学;他还认为 ,欧洲美学的创始人鲍姆伽登在建立美学时,曾把修辞学作为了美学的榜样。在他看来,修 辞学与注重口语和艺术经验的哲学相关。
而对J•德里达来说,首先,他主张颠覆一切,当然也包括修辞学在内。在《致一位日本友 人 的信》中,他明确表示:语言学、语义学等一切模式,都应该接受解构性质疑,解构不能被 还原为这些模式,解构不局限于任何一种模式。当然,他也说过,解构不是颠覆;解构本身 坚持的是一种肯定的经验和活动,它要分析原来的遗产中有哪些东西自己在解构(不:参阅德里达:《中国讲演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147页。)。
其次,修辞学最初是前苏格拉底哲学中的智者学派的主要模式,当时与雄辩术同义,是关于 一种口头辩论的技巧和艺术,与书写无关。H.-G.伽达默尔推崇修辞学,与他的主张口语与 对话密切相关。仅从这一点来看,作为对古希腊哲学有异议的、并抵制口语的J•德里达, 是 不大可能以修辞学为自己的哲学立场的。当然,后来修辞学又从口语发展到书面语言、乃至 于侧重于书面语言。因此,不能说J•德里达侧重文字就与修辞学无关,也不能说J•德里达 不 可以从修辞学的角度来批评H.-G.伽达默尔。他完全可以并且他所擅长的正是: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他可以修辞学来批评H.-G.伽达默尔的口语与艺术的理论。但是,所谓“其 人之道”,正是说明这个“道”是H.-G.伽达默尔的,而不是J•德里达的。因此,作为当时 欧洲哲坛巨匠、开拓“解构主义”哲学新时代的大师,决不可能以他人之道为自己之道,一 定会确立一己之道。修辞学,充其量也只是J•德里达哲学的一种辅助性手段而已。
那么,J•德里达究竟有没有一种哲学的立场?如果,一定要为J•德里达找到一种立场的话 ; 那么,与其选择修辞学,倒不如选择“语言行为理论”。这一点,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 2001年9月4日在北京大学的那个关于《宽恕》的演讲。他讲演一开始,就使用而不仅仅是 提到了Pardon这个动名词,把它作为动词的行为词,而且成为一个行为句。对于这些,他根 据“语言行为理论”作出了分析。与E.胡塞尔、M.海德格尔、H.-G.伽达默尔等人相比较, “语言行为理论”的哲学成果,是J•德里达哲学中比较独特的东西,是可以作为他的哲学 的基本立场的东西。
J•德里达、M.海德格尔、H.-G.伽达默尔他们三个人哲学上主要问题在哪儿。我认为,他们 的问题主要在于重语言文字、重文献的倾向。可以说,他们各自哲学思想的确立,靠的是重 语言文字、重文献的倾向;而他们之问题所在,他们哲学思想的最终完结,也正是因为这种 重语言文字、重文献的倾向。
他们把哲学的“意义”问题归结为“词义”问题,在这里我要强调指出的是西方那种根深蒂 固的传统,那就是:重“言”。而且,是上帝带的头,据记载:上帝说,有光,于是便出现 了光。借助于上帝,西方的这个重“言”传统又被神圣化了。
就重“言”来看,他们在欧洲阐述“言”,受到了欧洲语言文字的局限和约束;他们三个人 又都不懂中国的语言文字,也就无法以此来补救欧洲语言文字的偏颇。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 这一点;因此,他们极力呼吁他人能在这一方面有所改善。
在中国的文化中,有一种与重“言”不同的传统,那就是:重“行”。而且,是一种与“言 ”相比较后的重“行”。例如,中国的一般老百姓,都懂得“听其言,观其行”,“行”重 要于“言”,“行”可以检验“言”,“行”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当然,重“行”,也 被中国式地神圣化过,例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
另一点,就是重“文献”。就J•德里达而言,他的哲学思想也非常依托文献,注重对文本 的 解释。就他2001年9月4436c124ee203d1401b086cff7982e9466472dd42be16d364c49de0fcc75b695e日在北京大学的那个关于“宽恕”的演讲来说,这个讲演的绝大篇幅 是在作文献的解读、解释,主要是对扬凯列维奇的《宽恕》、《不受时效约束》等著作进行 解读、解释。
事实上,哲学特别是人生哲学最主要的基础,是在于对人生的最深切的感悟和经验,而这些 感悟、经验,通常来自实际的生活、生存,而不是信仰、理论、文献之类。在人们的实际生 活中,生存问题、现实问题往往会突然凸现出来,信仰、理论、文献之类往往落后于它们, 并被它们甩得远远的。J•德里达他们三人并不是不懂得这一点,但他们所处的语境正是欧 洲哲学的语言转向。从这一点来说,历史既造就了他们,又束缚了他们。
处于特定的历史境遇, J•德里达、M.海德格尔、H.-G.伽达默尔等人重翻译、重解释,一 方 面,固然是出于加强、增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沟通的需要。以前被认为是 理解了的、沟通好了的,现在看来并没有真正地理解和沟通;所以,在这方面特别需要加强 。另一方面,我认为,这或许也是人类被边缘化的产物。曾几何时,人们认为,凭借科学技 术,人类不仅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而且还可以主宰大自然。因而,人就成了人类和自然的 立法者。然而,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和世界大战等严酷而又无情的事实,粉碎了人类的这个 迷梦。人们只好退而求其次,人不再幻想自己能成为自然和人类的立法者,而只想成为自然 和人类的解释者乃至解释的解释者。
在哲学上,欧洲又流行一种古希腊以来的主流哲学,拉丁语系的语言和哲学受到排斥。法国 的哲学,也处于一种边缘状态。
J•德里达的反对中心主义,与其生活经历和法国哲学的境遇不无关系。他在结构主义的语 境中 ,从结构的角度,以说明中心主义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人们往往在某种结构中,试图树立一 个中心,来支配、驾御这个结构。但是,这个中心,本来就是那个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如 果,这个中心想支配和驾御那个自己所在的结构,那就得超越那个结构;而超越了结构的中 心,就在结构之外,就不再是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在J•德里达的诘难下,中心处于一 种既在结构之中、又在结构之外的两难境地。
在中心主义盛行的时候,J•德里达明确提出反对中心主义的口号,犹如喊出“王侯将相宁 有 种乎?”那样振聋发聩。在这一点上,我认为,J•德里达显示了维护本国哲学和话语权益 的坚定立场,他有着极强的反抗精神和坚苦卓绝的斗争精神,以及他学术上的独创性。
就欧洲哲学而言,J•德里达强调的是多元性、相互的独立性和各自的合法权益。在欧洲哲 学的相互之间,事实上并不应该有什么所谓的边缘与中心。中国与欧洲分属世界的两种根本不 同的语言和文化,其哲学也是根本不同的,各有其自身的正当权益与合法性。对于我们自己 的正当的、应有的权益,我们应该努力加以维护 。
我认为,世界两次大战,那么多的人生命受到威胁乃至摧残,人的生命和生存问题就凸显了 出来。这样一来,人们面对的,首要是生命、生存,而不是信仰、理论等问题。对于哲学来 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E.胡塞尔、M.海德格尔、H.-G.伽达默尔、J•德里达都敏锐地 感受到了现实生活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并从解读、解释、回答这个问题的需要出发,找到了 一种新的哲学视角,形成了一种新的哲学语言。
而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机遇”。比如,其中之一就是,在上个世纪六十 年代H.-G.伽达默尔、J•德里达创立了各自的哲学体系之后,一直到他们去世,既没有人能 够超过他们,也没有人能够克服欧洲所陷入的长期的理论疲软。当时,我在德国时,德国哲 坛许多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可就是束手无策。也许,有着不同生活经验、文化底蕴的中国 人,以不同于欧洲人的视角,会有些新的发现?
从德里达之后的今天回望他,我们应当重视的是:其一,并不在于去说清楚他们的哲学是什 么;而在于:在他们之后,哲学将如何发展?其二,在他们之后,哲学将如何发展?这个问 题的解决,似乎也不是靠去探讨哲学是什么、将来哲学是个什么样之类;重要的是哲学活动 本身。但愿有一天,人们惊喜地发现:正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这些并不起眼的哲学活动,构 成了J•德里达等人之后的哲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 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