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南音部分)随想
《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由三本在明·万历年间流传至欧洲的,刊载当时流行于福建闽南的戏曲、南音的珍贵史籍装订而成。是至今发现流传最远,最早记录闽南戏曲、南音的读物。其中戏曲部分发现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而南音部分则发现于德国萨克森州立图书馆。其发现者英国著名汉学家龙·彼德先生凭着他对中国闽南文化的热爱,把它们编订成册,这无疑对闽南地区的戏曲、音乐、文学、文字、方言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一、关于《精选新曲》
从名称上可看出:《精选新曲》应该是当时广泛流传的南音新曲目,从内容上看,有的可能是吸取戏曲唱段,有的可能是出自文人们的抒情创作。
《精选新曲》中,除了所印的唱词和曲牌名外,看不到一个工乂谱符号,所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有的唱段如《启公婆》,从唱词上看是出自《雪梅教子》故事,曲牌处却仅写了一个“北”字。虽唱词与当今广泛流传的《启公婆》基本一样,但今天流传的《启公婆》曲牌为“北青阳”;同样有一“北”字,前者是否后者的简称呢?我们不得而知。加上没有其他工乂谱符号,我们很难断定它就是今天流传的“北青阳”之《启公婆》。
该部分中,其它如《一杯淡酒来尊前告》《精神顿》等曲目与当今流传的同名曲目比较后也有类似现象。
《一杯淡酒来尊前告》在曲牌处写的是“北”,与今天流传的《尊前过》在第一句唱词上少了“一杯淡酒来”五个字外,内容基本一样,而今天的《尊前过》(“过”疑为“告”的误写)其曲牌却写的是“锦板·风潺北”。
《精神顿》在曲牌处写的也是一“北”字,但现在流传的《精神顿》曲牌却写着“中潮”。
不仅以上提及曲目,一些现在于曲牌处写明“锦板”的曲目如《金井梧桐》,在《时尚摘要》中也标为“北”。这又不由人再做另一番设想:闽南人素有将外来人称之为“北”的习惯。有可能《精选新曲》中的一些曲目就是今天我们广泛传唱的曲目,但因为它们的曲牌吸收了某些外来的音乐元素(或者就是取自外来曲牌),因而被冠以“北”的称呼。这种情况虽无十分把握,但通过前后联系,古今比对却也是很有可能的。
该部分的另一首曲目《娘子简劝》唱词中,除第一句唱词在今天流传甚广的名曲《荼蘼架》中没有外,其它的唱词与今天的《荼蘼架》基本一样。在曲牌处,《娘子简劝》写的是一个“滚”字,而今天的《荼蘼架》写的却是“双闺”。唱词虽变化不大,但曲牌上的一个“滚”字与“双闺”却相差甚远。这就不由得让我生疑,《荼蘼架》是否取《娘子简劝》的唱词略加改动再填入“双闺”曲牌而成呢?
二、关于《新刊弦管时尚摘要》
在该书的《新刊弦管时尚摘要》(以下简称《时尚摘要》)部分中又按“背双”、“双”、“相思引”、“北调”分成四个分部。其记录南音的符号相对完整些。它们除记录唱词外,还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一些不完整的工乂谱撩拍符号,这为我们今天对南音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多的方便。其中一些曲目与当今流传的同名曲目比较后,发现这些曲目除了唱词基本一样外,其标出的工乂谱拍位符号、曲牌名称也基本一致。
例如,《时尚摘要》中的《谗臣》一曲,其曲牌标明“相思引”,将它与今天所流传的《谗臣》比较后,发现二曲同是出自“王昭君”故事,其唱词基本一致,拍位也大致一样,而今天流传的《谗臣》其曲牌也是“相思引”。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其曲调也应该大致相同?如果曲调各异,那么,拍位怎么可能大致一样,曲牌又怎么可能相同呢?
这部分中的《盘山过岭》一曲虽没有写出曲牌名,却写着“双”(关于“双”接后论述),将它与现在流传的《盘山过岭》比较,同样可发现:其唱词基本一样,拍位基本一致;虽没有曲牌比对,但管门却也相同。因此,我们同样可以推理得出:它们的曲调也应基本相同,今天的《盘山过岭》就是当时《盘山过岭》的延续。
《时尚摘要》中类似《谗臣》《盘山过岭》的现象较多,于此不可能一一列举。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今天我们仍在传唱的某些曲目早在明代就已相当普遍地流传,简直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两个时代相隔几百年的同一曲目虽存在某些差异,这也是正常的,它完全符合民间音乐流传、发展的规律。
从这些比对过的曲目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的南音已有较为庞大、严谨的音乐结构和相应的写作手法。可以说是比较成熟的、高水平的。也说明南音在此之前已走过一段相当漫长的发展之路。
《时尚摘要》中第上十页“双”分部刊有《心肝跋碎》《感谢公主》(二者合为一曲),第下二页至下三页“北调”分部刊有《朱郎卜返圆》《我只恐畏》(二者合为一曲);它们统属于“朱弁”故事,其间却相隔页数甚多,分属两个不同分部而并非连在一起。今天,这四首曲目连接起来正是指套《心肝跋碎》。也是较为人们所熟悉的南音“五大套”指套之一。
显然,当时这几首曲目并未集结形成套曲(指套),甚至有可能将几首有一定唱词、表达一定内容的曲目按一定规律连接成套(指套)的概念和做法还没有形成。如果是这样,指套的形成就有可能是在“明”以后。
在这些分部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有的曲目在《精选新曲》中也同样被收集。
例如《时尚摘要》中的《拙时无意》《朱郎卜返圆》二曲在《精选新曲》中均有所见,这也说明当时人们在保留传统曲目的同时,对新曲目的接纳和包容。
《精选新曲》由于没有撩拍符号,我们无从了解那些曲子的更多情况。而《时尚摘要》中,由于记录有工乂谱拍位符号,通过手中现有资料比对(由于手头资料有限,加上有些曲目可能已经失传,因此,不可能每首曲目给以比对),可发现:曲目中,七撩(如《心肝跋碎》倍工·玳环着)、慢三撩(如《馋臣》相思引)、紧三撩(如《朱郎卜返圆》锦板北)、叠拍(如《我只恐畏》锦板叠,现为《只恐畏》)等南音唱腔中的节拍现象当时已较完整,只是没有运用这些对撩拍的名称。从比对过的曲牌上看,当今广泛流传的,民间经常演唱的一些紧三撩、叠拍的曲牌甚为少见。试想,如果这些曲牌在当时就很盛行,作为《时尚摘要》不至于入选量如此之少,甚至没有。
从这两点看,是否可说明:一些当今广泛流传的撩拍名称及曲牌是在明末或清代才被大量吸收和运用的。
三、关于“双”与“背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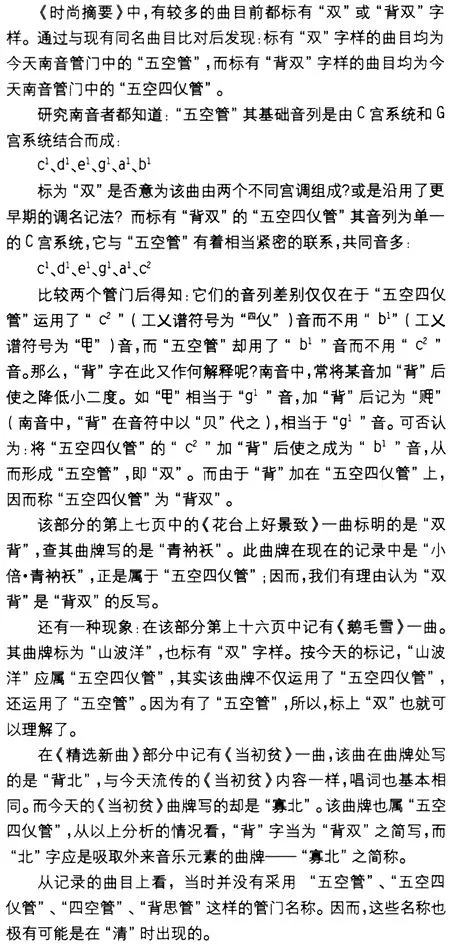
四、关于吸收与创新
从标题的“新曲”二字上、从今天的撩拍名称上、从吸收曲牌现象上、从管门名称的运用上,我们都可以看出:当时的南音前辈们比起今天的部分南音人们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更具有大胆的吸收和创新精神。他们既尊重传统,又不迷信传统,既保留传统,又不被传统所束缚;从而吸收和创作出更多的南音新曲,并得以广泛流传至今。
与此同时,先辈们的做法在不经意中也留下了更多的古代其它音乐之脚印。假如没有他们当时的大胆吸收与创新,今天,我们的南音宝库将少了许多优秀的、令我们引以为豪的南音作品。一些更古老的音乐线索今天也可能芳迹无踪。他们的做法很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适应了广大民众的心理。难怪纯民间的南音在当时会如此盛行,如此博得大众的喜欢。由此还有力地证明:吸收与创新本就是南音的优秀传统,也是保存南音、延续南音的有效手段。
吴璟瑜 泉州南音乐团二级作曲
(责任编辑 金兆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