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草原的底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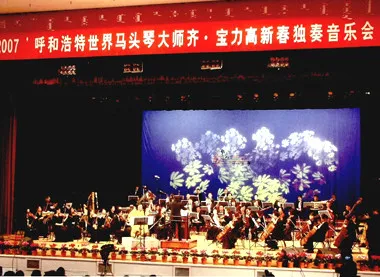
草原上万马奔腾,天空中雄鹰翱翔,小溪里泉水淙淙,摇篮旁深情吟唱……伴着激动人心、震撼灵魂的琴声,高昂着那颗尊贵的“大头”,披散着一头马鬃似的长发,无比坚毅的神色以及随着音乐而紧张、松弛、喜悦、痛苦的面部表情,这就是音乐会上马头琴大师齐•宝力高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齐•宝力高创作的马头琴乐曲已有100多首,出版的马头琴演奏录音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有多少小时,他说:“反正从早到晚听不完。”他到过亚洲、欧洲、美洲、非洲的许多国家,他把马头琴这件乐器从蒙古包推向了世界,对马头琴音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006年10月19日晚,我在中国音乐学院演奏厅听了齐•宝力高的一场演奏会。音乐会上,他不仅用完美的演奏展示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高超的演奏技艺,还讲了很多自己难忘的故事,发表了许多极有见解的思想。这一切都深深打动了我。为了进一步走进大师的心灵,2006年10月20日,笔者从早晨到晚上一整天和齐•宝力高在一起,话题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从艺术到哲学,从民俗到宗教,不仅十分广泛,而且相当深入。本文就是这次长达十个小时亲密接触的感悟结果。
一、 独特人生造就的艺术奇才:“先天”注定的传奇人生与艺术之路
宝力高说:“艺术家首先应该是个哲学家,没有思想就只能像个钉鞋匠,成不了艺术家。”宝力高对艺术、对人生的洞察力深刻、独特,常常在不经意间说出极富哲理的话语。这些得益于他独特的个人经历,是他的“社会大学”,造就了他对社会、对艺术的独特感悟和深邃思考。
1944年农历二月初二,在这个中国文化中不同寻常的日子里,齐•宝力高在内蒙古科尔沁大草原降生。他的母亲是一位酷爱唱歌的人,经常唱着蒙古的各种民歌,这使宝力高自幼就受到家庭音乐环境的熏陶。母亲是蒙古贵族后裔,是一位很有个性、很有修养的人,善良、坚强,经常教导宝力高:“人要和自己过不去才能有出息”。这句朴素的话,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要不断“挑战自我”。这对宝力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鞭策宝力高不断前进的动力。至今,宝力高常说:“母亲是最伟大的人!”
宝力高的父亲曾在阿拉坦西热图大庙当过活佛,还在印度等地研习佛经19年。“我在娘胎里就是听着佛经长大的”,宝力高说。 这种家庭背景培养了宝力高的佛家心性,使他具有了一颗充满善良和仁爱的“佛心”:爱人类、爱动物、爱草木、爱和平。
然而,这个出身,却为宝力高坎坷不平、充满传奇的人生,铺就了一条无法逃避的“预置”轨道。
宝力高三岁时,经过一番严格程序,被确认为莫力庙第五世活佛,但五岁时被赶下台。“我是三岁登基,五岁下台”,宝力高说。当时还要把他拉出去枪毙。有人说:“五岁的孩子还在吃奶呢,留他一条命吧。”就这样,这个幼小的生命因为幼小而逃过一劫。
更大的磨难还在后头。“文革”中,因为活佛出身,再加上倔强的性格,遭受批斗就像是家常便饭,还受诬陷蹲过几年监狱,遭受过脚踢、毒打、火烤等种种酷刑。后来,虽然他考上过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但因为活佛出身却被剥夺了上学的资格。
然而,积极的人总能在消极不利的环境里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化腐朽为神奇。宝力高说:“只要你留意,身边到处都能学到东西。社会就是大学。”他在监狱里读了很多书,哲学著作看了不少,尤其佩服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矛盾论》都看过,认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洋为中用,古为今用”都是从实践里总结出来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坎坷的经历并没有摧垮宝力高坚强的心,反而磨练了他钢铁般的意志。多舛的人生造就了他对社会、对人生、对艺术的深刻理解和非凡的洞察力。酸甜苦辣人生百味的反复品尝,喜怒哀乐世间情感的丰富体验,也铸就了宝力高无比丰富的内心情感世界。 这为他日后的音乐创作和表演,为他多彩的艺术生涯,提供了丰富、充足的养料。除了演奏马头琴,创作马头琴音乐、歌曲,他还写诗,画画,练书法,这些都为他的音乐艺术增添了不少文化厚度。
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没有体验就没有真情,这是古今中外艺术领域里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
宝力高在苦难中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妈妈告诉他马头琴是佛爷留下来的乐器,是成吉思汗留下来的乐器,是蒙古人灵魂深处的声音,是神圣的乐器。从此,他和马头琴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双重乐感”:有了科尔沁大草原音色的“底色”,什么技术都可以借鉴
马头琴在齐•宝力高手中是一件可塑性极强的乐器。他不仅可以在质量一般的琴上拉出动人的声音,还可使自己的马头琴演奏出多种截然不同的音色。他用马头琴演奏风格浓郁的内蒙古音乐,草原音乐的独特韵律、马头琴独有的音色、长调的悠扬、“潮尔”的震颤、“诺古拉”独特的润腔,让你仿佛置身于辽阔无垠的科尔沁大草原上,徜徉在内蒙古音乐的海洋中。一瞬间,他又把马头琴变成另外一副面孔出现在我的面前,用它奏出帕格尼尼、莫扎特、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等人的动人旋律。纯净的音质,美妙的双音、和弦、跳弓、顿音,快速音阶,此时,马头琴俨然成了一把小提琴!
听过宝力高马头琴演奏的人都不难听出在他的马头琴音乐中的提琴意蕴。演奏技术如此,创作的作品也是如此。
齐•宝力高跟随马思聪的高足王华翼学过四年小提琴,13岁起就一直跟着杜兆植老师学习作曲技术,西洋乐理、和声、曲式都系统学过。他把这些技术都用在了马头琴上,他说:“马头琴融合了世界各种弦乐器的优秀技法。”
看到他在马头琴演奏、创作上借鉴了这么多的小提琴因素,我内心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虑:这音乐还是马头琴的音乐吗?
在场的额尔德尼解开了我心中的疑团。他是宝力高早年教过的学生,跟宝力高学琴30多年了,他现在演奏马头琴,也制作马头琴。他说:“乐感是最主要的。乐器和技术都是为乐感服务的,宝老师能在小提琴上演奏出马头琴的感觉。”我说:“可以不可以这样说:技术和乐器是电脑的硬件,乐感是软件,是预置的操作系统?”额尔德尼说“是的”。这样来说,在齐•宝力高的乐器、技术背后,支撑他马头琴艺术的是两套“操作系统”,一套是早年预置的“内蒙古系统”,另一套是后来安装的“欧洲系统”。在这两套系统中,前者是基础性的构建。

对于我和额尔德尼的说法,齐•宝力高也表示赞同。童年时期,科尔沁草原乌力吉牧仁河的滚滚河水、河边高大的树木和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给宝力高留下了无法抹去的深刻记忆。而烂熟于胸的几千首内蒙古民间曲调,是“刻”在他心里的音乐烙痕,为他的乐感涂上了一层浓重的草原音乐底色。他说:“我的乐感来自科尔沁大草原”,“一个人的本性八岁以前就定型了,八岁以前是一张白纸,画上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他还反复说:“狼就是狼,狗就是狗,本性是不能改变的。”这语言虽然略显粗糙,但道理却很深刻。有了科尔沁大草原乐感的“底色”,什么技术都可以借鉴,借鉴什么技术也都不会失去蒙古音乐的韵味。
他一边向西洋技术学习,一边挖掘民间的艺术宝藏。直到现在,他还每年都要到最偏僻的地方去寻访民间艺人,学习他们的演奏方法,吸收他们的音乐思想。最近他就在阿拉善西部腾格里沙漠深处寻访到五个健在的尚能演奏马头琴的“马步”的民间艺人,最年轻的64岁,年龄最大的89岁。他们能演奏地道的“原生态”的“马步”,但也只会七十多种“马步”中的十几种了,其余都失传了。宝力高去了两次,每次半个月,学到了这种“马步”演奏技术,并在舞台上作了介绍,还据此写了一首新作品。对于他来讲,民间艺术是永不枯竭的艺术源泉,需要永无止境的探索。
他还认为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首先要学好民歌,打好乐感的基础。在他的理念中,从心灵到音乐有一个固定遵循的路径,那就是心灵决定乐感,乐感驾驭技术,技术支配乐器,乐器发出声音。对音乐最终起到决定性、根本性作用的是心灵和乐感。
三、“变与不变的对立统一”:齐•宝力高的马头琴改革实践与理念
大家都知道是齐•宝力高把马头琴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但很少有人注意他改革中的坚定信念。
马头琴的共鸣箱早年是用马皮蒙的,因为极易受潮跑音,在宝力高手上就改成了用定音鼓皮蒙制。但这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善,一遇阴天下雨、气温升降,音高极不稳定。1973年一次演出遇到大雨,马头琴在舞台上声音逐渐减弱,最后终于失声。 这促使宝力高下决心改革马头琴,他想到了蟒皮。换成蟒皮的马头琴音色淳厚、优美抒情,音域也得到扩展,迈出了重要的改革步骤。但是,马头琴的共鸣箱面积大,大块蟒皮受潮、遇热、遇冷,张力变化明显,用蟒皮蒙制的马头琴也还是没有解决音高的稳定性的问题。1983年在北京与交响乐团排练《草原音诗》时,因为频繁的定弦,被乐团同行嘲笑:我们排练的是马头琴协奏曲,不是“定弦协奏曲”!在这个强烈刺激下,宝力高终于迈出了马头琴改革的关键一步:把琴面换成梧桐面板。当年花八块钱请制琴师傅用梧桐木做面板的那把马头琴音色明朗,音量宏大,歌唱性强,并且音高稳定,与乐队合奏时轻轻松松即可从音流中脱颖而出。这把琴成了宝力高的挚爱,几十年来一直伴随着他走南闯北,与他形影不离。后来,他在日本又做了一种用松木做面板的马头琴,又作了一些局部的改进。
这样,马头琴从马皮、定音鼓皮、蟒皮、桐木板、松木板,已经经历了五次换代。再加上其他的配套改革,如琴码、琴弓、音孔位置和形状等等,使得马头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招来了不少批评。同样,笔者心中也充满了疑虑:这还是马头琴吗?f孔一开,与小提琴还有什么区别?
怀着这样的困惑,我向齐•宝力高表达了我的疑问:马头琴没有改变的本质是什么?改革的理念又是什么?
宝力高说:“没有传统的瞎改当然不行,要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改革。马头琴的‘马尾织弦法’是不能改变的。马头琴的琴弦与小提琴不同,用‘马尾织弦法’做成,小提琴是一根合为一体的弦,马头琴的弦是相互独立的很多根弦。这样的琴弦有它独特的音色。噪音也是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没有噪音就不感人。马头琴的噪音就是这种琴弦产生的。‘马尾织弦法’要是改了,马头琴就完蛋了。”
原来,“马尾织弦法”以及由此带来的独特音色是宝力高在马头琴改革中固守的传统底线!说到底他固守的是传统的马头琴音色韵味,这正是马头琴音乐的本质“内核”。
他还说:“我们并不是为了改变而改变。过去的马头琴声音像蚊子一样,音高还不稳定,不改革除了进博物馆,别的没有出路。逼上梁山,不改不行。”
传统是条河,那是一条既保留着自身内核又日新月异的河。梅兰芳先生也有“移步不换形”之说。齐•宝力高说他的马头琴改革是“变与不变的对立统一”。
变,是为了求生存;不变,是为了传统的基因。这就是齐•宝力高马头琴改革的核心理念。
四、“父亲﹢母亲=老师”:齐•宝力高的责任公式
齐•宝力高在给“老师”下定义时,语出惊人,他说:“什么是老师呢?父亲加母亲就等于老师。”父亲﹢母亲=老师,这就是齐•宝力高的责任公式,是他对传承马头琴艺术高度责任心的体现。
宝力高介绍说,“文革”期间,马头琴被当作民族分裂的乐器,不准拉。他就把当时的“革命歌曲”改编了在马头琴上拉,那时候,整个内蒙古就他一个人在拉马头琴。“文革”结束后,他把传承马头琴艺术的重担义无反顾地挑了起来。他在内蒙古教过很多学生,很多人如今都成为马头琴演奏家,成为马头琴艺术的栋梁人才。但是,宝力高从来没有收取过这些学生的学费,还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在家里管吃管住,还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难题:没有老婆的帮着张罗,买不起房子的帮助买房子,夫妻打架的帮助平息争端等等。这样,学生们都爱戴他,信任他。2001年,他亲手建立的马头琴“野马队”队员由27人猛增到1000人,一个夏天的集训,齐BmNp3vWoUrDuZezzX7RJJihldGQYuO852xbVyFPxuGU=•宝力高就拿出了家里的12万元积蓄,还从别处找来20万元,全部用于集训开销。在日本还捐助30万日元帮助学生交学费,完成留学学业。
宝力高说他在中国教学生不收钱,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他本人学琴没有交过学费,所以也不收学生的钱。但是他在日本教学生要收学费,因为那是资本主义国家,情况不同。
不交学费的学习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宝力高说:“我不收你学费,你吊儿郎当的我就要揍你!你们谁愿意跟我学我都教,但是不认真学我必须揍你!”
说起宝力高对学生的严厉,他的学生都是深有体会的。他自己的儿子学琴他不满意时也是一样,很粗的棍子都打断过。
宝力高的逻辑是:老师是你爹妈加起来的综合体,要爱你,不好的时候就要打你。他打学生,也是一种深爱表达的方式。爱之深,才恨之切。
五、坚韧不拔的开拓者:用成吉思汗的精神统一马头琴弓法
齐•宝力高是一个坚韧不拔、执着顽强的人。在谈到他戒烟的时候,我问他有没有出现过反复。他斩钉截铁地说:“我这人说话算数,说戒就戒,没有反复!”这种精神在他统一马头琴弓法的事情上得到充分体现。
从1973年写关于马头琴的演奏技法的书开始,齐•宝力高就在探索、归纳马头琴的演奏弓法,尝试统一马头琴的弓法。1986年成立“野马队”,八个人,各不相同。这一年,各个旗抽调文化系统的马头琴演奏者成立高级训练班,统一集训,回去再传播马头琴艺术,49个人,每个乌兰牧骑都有一个人。宝力高正式开始了他艰难的统一弓法之旅。马头琴是一种起自民间的乐器,一开始演奏者都不知弓法为何物,一人一种方法,“乱七八糟”,统一起来谈何容易!坚韧不拔的宝力高把这些人带到锡林郭勒盟一个无人居住的偏远地方,封闭式强化训练45天,统一了这些人的演奏弓法。到1989年,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宝力高终于实现了统一马头琴演奏弓法的梦想。
笔者问:“统一弓法对马头琴艺术是一件好事吗?”他的回答是:“什么事情不统一都不行。当年成吉思汗用武力统一了整个蒙古,要是不统一的话,各个部落整天互相残杀,蒙古族早就不存在了。我统一马头琴弓法用的就是成吉思汗的精神。”
六、充满爱心的“和平使者”:心灵的呼唤与倾诉
齐•宝力高到今年已经在日本住了22年,他的马头琴艺术在日本深受欢迎。他还到过欧洲、美洲、非洲的许多国家演出,2005年8月16日还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过。他把马头琴这件乐器从蒙古包推向了世界,也把爱好和平的理念传播到世界各国。
宝力高认为他的音乐是“人道主义的”、“和平的”、“充满爱的”。他说:“我通过马头琴能够促进和平、传播文化、增进了解、增加友谊。”他成了一位“和平使者”,足迹所至,都成了他用心灵倾诉友爱、呼唤和平的地方。
孟凡玉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音乐系副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2004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