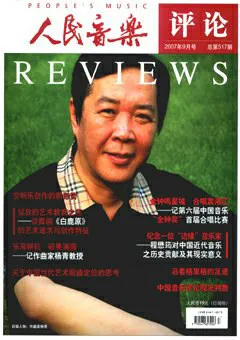与“他者”的目光相遇
在“第十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中,原生态唱法从民族唱法组中分离成为单独的一组。从那一刻起,原生态一度成为音乐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这不禁使我回想起第十一届青歌赛中的一幕:当时,来自云南的原生态歌手李怀秀、李怀福姐弟,以一曲原汁原味的彝族海菜腔《金鸟银鸟飞起来》,把民间音乐的表演和表现形式推向了中国音乐最引人注目的舞台。在用歌声打动观众的同时,也打破了声乐界传统的评分标准。
给出低分的是部分学院派老师,他们解释到:“这种唱法还是一种民间的演唱”,姐弟俩还需要“提高专业水平”;而打出最高分的民族音乐理论家田青却认为:“我在他们的歌声里第一次听到了来自自然的声音,听到了传承自祖先的声音……”。这两种评价标准的依据是什么?笔者认为,学院派老师是以美声唱法为基础的,要求声音必须具备专业性和科学性。众所周知美声来源于西方,所以这其中暗含的是一种“他者”的立场;①相反,田青老师则用一种“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②从文化主体性意识的角度提出了“我者”的标准。这两种评分标准的闪亮登场,使“我者”与“他者”的目光在这一刻相遇,引发了笔者对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意识的思考。
一、 主体“我者”的困境
经常关注媒体的我们会发现,采用美声发声方法演唱中国歌曲成就了一种“学院派民族唱法”(或称新民歌)的辉煌,它造就了如彭丽媛、宋祖英和阎维文等一批深受群众欢迎的歌唱家。这本无可厚非。但长期以来,国内各种声乐大赛似乎都以这种演唱方法作为对民族唱法和民间唱法评分的唯一标准,并且“这样一种绝对权威形成了一种从学校教育到社会媒体的话语霸权”。③而代表中国各民族或地区文化的原生态唱法却很难在媒体和各类比赛中亮相和获奖,这便形成了各民族地区民歌主体“我者”的困境。
首先,我们面临着观念上主体“我者”的困境。人们对民歌的理解有两个误区:第一,凡是基于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或用学院派民族唱法演唱的歌曲就是民歌;第二,学院派民族唱法是“科学的唱法”,其它则不是,或原生态唱法只有经过学院派的训练,提高到“专业水平”才有价值,才有“美感”,才是发展民族唱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由此,学院派民族唱法成为了歌唱的“文化主体”,④而代表中国各民族或地区文化的原始形态的歌唱却成为了“边缘的”、“不适时宜的”,甚至“落后的”象征。
其次,社会的困境也让“我者”举步维艰。随着音乐商业化的发展,各类传播媒体日益增多。广大媒体在促进音乐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损害。媒体从没有考虑过代表中国各民族或地区歌唱的原生态民歌及其文化价值,那些歌曲排行榜考虑的是发行量及“流行”趋势,说穿了就是以商业价值为重。什么是代表各民族和各地区真正的民族唱法,中国丰富多样的民间歌唱并不是打造的对象。音乐人类学家洛马克斯曾讲:“每一种歌唱表演体系,以它本身来评价,是文化的生动象征,也是这种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⑤但是,我们的媒体没有将中国音乐文化的这种“生动象征”展示出来,就把各类学院派民族唱法的音响制品、出版物或栏目赫然打上“民歌”的标志。这种对自己“祖先声音”的无知,竟演变成了一种全民性的误解:学院派民族唱法就是我们音乐文化的“象征”。由此,大家对学院派民族唱法就是民歌的概念越来越格式化和固定化,似乎成为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当前音乐环境对人的感染和冲击是如此巨大,“如果任其泛滥,就会淹没并摧毁人类各种文化和各类音乐品种。”⑥
再者,中国音乐教育也同样面临着主体“我者”的困境。我们的声乐教育与教学都是以“美声”为基础建立的:声音的共鸣、声音的张力、声音的音域要符合“美声”的原则,并与宏大的交响乐队音响“抗衡”,才是反映工业现代化的标准,才是最高水平;在固定视唱练耳教规的行为矫正中,我国民歌与生俱来的即兴演唱的自我表达已被抛弃;听帕瓦罗蒂、卡雷拉斯和看西方古典歌剧就意味着欣赏“高雅音乐”;如果不符合美声或所谓学院派民族唱法的发声标准就进不了专业院校;专业音乐院校的课程设置中很少有系统介绍和学唱我国传统戏曲、说唱以及少数民族歌唱的课程……而我们的音乐教师能否作为民歌的传承者?他们对本民族音乐文化的歌唱到底了解多少?“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己对此都知之甚少,怎么能使坐在课堂里足不出户的学生们知道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民歌呢?我们承认美声的发声方法是科学的、规范的,且有大量的文献和音响资料。但它并非中立的,而与“我者”同样,也是受本民族文化美学标准所制约和影响的,具有其独特的文化性以及历史性,而非仅有科学性,并超越一切文化或历史标准之上。用“他者”美声的标准越过自身的限定范围去解读“我者”的原生态民歌,长此以往将会使“我者”、“他者”最终都会变为“同者”。试想,世界上所有的歌唱越来越趋同,各民族的声音特征越来越模糊,有一天全世界多姿多彩的歌唱形式都变成了“同者”,那该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二、音乐文化主体性意识的构建
如何摆脱主体“我者”的困境,关键是要建立起全民族的音乐文化主体性意识。
首先,理清观念、正确解读。要搞清楚民歌(即原生态唱法)、学院派民族唱法的概念以及文化价值。民歌不等于学院派民族唱法。民歌是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广泛的口头传唱而形成的民间艺术,与我们本民族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语音语调、民族心理等因素息息相关。而学院派民族唱法却是在民歌元素的基础上加以美声科学的发声方法改变而来。美声唱法是为了适应工业化时期交响乐队以及“宏大叙事”的要求产生的,而今天它已经不再是声乐发展的唯一标准了。理清民歌的概念,识别其不同功能和文化价值,才能来谈音乐歌唱标准的问题,才能对主体性意识进行构建。我们并不反对学院派民族唱法,但我们更不应该去压制我们民族自身所拥有的歌唱及其方法。甚至,为了维护我们的传统,为传统争得有限的生存空间,我们应该对那些压制行为进行“抵抗”,就像田青老师在评分时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出于主体“文化自觉”的举动,⑦我们需要这种举动。正如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所言:“每一种文化都是与其它文化交流以自养,但它应当在交流中加以某种抵抗。如果没有这种抵抗,那么很快它就不再有任何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去交流。”⑧
其次,舆论引导、社会帮助。现代媒体如报纸、杂志、电视、网络和广播是很好的手段和工具,应给予民歌和民间歌手以正确和广泛的宣传。多开展一些有关民间音乐文化的演出与比赛,比如2004年CCTV举办的“西部民歌大赛”和2006年的“青歌赛”就让我们了解到了更丰富多彩的原生态民歌。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的“青歌赛”设立了原生态组,这本身就是对民间音乐文化的一种正确认识和有力推动。尽管“蒙族的长调和哈萨克的民歌能否放在一起比”还有争议,但毕竟代表各民族和各地区真正的民间唱法已经开始展示在央视的舞台,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此外,政府和各级机构不应只给在国际上或国外获奖的音乐工作者予以奖励,也应该对有卓越贡献的民族音乐家和民族音乐工作者们给予物质与精神奖励。同时,以优厚的条件和待遇邀请并鼓励其它国家的音乐工作者或爱好者们来我国学习包括民歌在内的本民族音乐文化。只有在社会舆论的重视下,在和谐共生的音乐文化的基础上,才会重新唤醒我们民族音乐文化的主体性意识。
再者,源头教育、固本强基。在音乐教育的声乐教学中,应注意中西方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相差甚远,我们的民歌是受特定语音语调、风俗习惯和地理特征的影响而形成的,必须在中国特定的民族文化和背景中来解读。中西声乐好比两座山,相互学习是为了共生共存,互相增高,而不是为了填平两座山。否则,将不会两山受益,而是受损。正如洛马克斯所举的一个例子:“黑人——他们的文化赋予他们极好的声音和非凡的音乐感——会因接受新的音乐训练,用西欧风格和由和声堆砌而成的传统和声体系去演唱而遭受损害。”⑨我们的声乐教育同样应该引以为戒。中国的民间唱法是丰富多彩的,很多民族都有其自身的歌唱标准和体系,需要我们音乐教育工作者们付出艰辛的劳动去为其挖掘和整理。音乐院校不应该以美声和学院派民族唱法作为衡量和录取声乐人才的唯一标准。音乐教师也应该负担起自身多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责任。音乐声乐教学的课程设置可以系统介绍和学唱中国各民族地区民歌、戏剧、曲艺和说唱,并在此基础上开设与其相关的文化课程,以此来加深对民歌的理解,更好地把握民歌。定期邀请民间艺人进课堂,为学生表演和讲解民歌,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学生与原生态民歌面对面交流,加深学生对民间音乐的感情,在零距离接触中牢固地树立起我国音乐文化的主体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