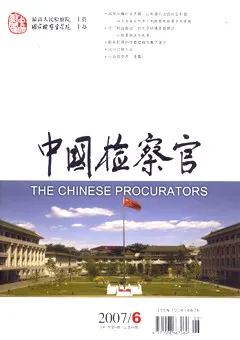职务犯罪的侦查措施完善之途径
内容摘要:如何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扭转我国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侦查不力的局面,是人民检察院亟待解决的问题。重新认识职务犯罪的特点,整合检察机关的侦查力量,制定专门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建立职务犯罪的特殊侦查措施,是检察机关摆脱目前困境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职务犯罪 侦查措施
有效预防和打击公职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犯罪,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开章就明确规定:“本公约的宗旨是:促进和加强各项措施,以便更加高效而有力地预防和打击腐败。”我国政府已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了该公约。如何有效打击职务犯罪,不仅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且也是我国履行国际条约的法律义务。人民检察院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了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犯罪的侦查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存在严重的不力,职务犯罪日益猖獗,这业已阻碍了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危及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引起了人民的严重不满。如何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扭转我国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侦查不力的局面,是人民检察院亟待解决的问题。重新认识职务犯罪的特点,整合检察机关的侦查力量,制定专门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建立职务犯罪的特殊侦查措施,是检察机关摆脱目前困境的关键所在。
一、改造现有的立案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立案是刑事诉讼开始的程序,只有在立案之后才能开始进入侦查程序。由于立案程序的存在使立案前的调查行为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一些侦查措施不能及时使用,致使嫌疑人利用自己的职权毁灭证据、收买证人等,力图阻止立案后侦查行为的顺利进行。从司法实践看,检察机关初查率很高,但成案率相对较低,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及时地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在初查阶段为嫌疑人提供了伪造、毁灭证据的机会。为了有效地查处职务犯罪,应废除立案程序,取消检察机关内部存在的大案、要案的立案请示汇报制度,一旦获得案件的线索,对案件进行登记后,检察机关的侦查局就应立即进入侦查程序,可以对嫌疑人采取一切合法的侦查措施,这样既可以督促侦查机关及时办案,也可以有效地避免因初查无效而导致侦查时机的贻误,以保障侦查的成效。
同时规定职务犯罪侦查局在侦查职务犯罪时,可以行使同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可以自行进行拘留、无证逮捕、留置盘查等侦查措施,以有效打击该类犯罪。对此新加坡《反贪污贿赂法》第18条规定:“检察官依刑事诉讼法典的授权,可以给予局长或行使权力的特别调查人员以授权令,在成文法规定的任何案件中,行使有关警察调查的全部或任何权力。”
二、建立强制调查制度
强制性调查是指检察机关侦查局的局长或者负责案件侦查的侦查人员如有合理怀疑某人实施了职务犯罪,可以强制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强制性调查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强制有关单位提供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
如果侦查局的局长或其他侦查人员确信某人实施了贪污贿赂犯罪,可以调查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与该行为人有关的银行帐目、消费帐目或任何其他的帐目、或任何银行中的保险寄存箱,并且可以调查嫌疑人的亲属或关系密切的其他任何可能帮助其隐匿、转移非法利益的人员的上述帐目;并且可以命令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侦查人员所需要的任何材料、帐目、文件和物品;并且金融机构有义务按侦查人员的要求监控某人的帐目往来,并向侦查人员随时报告其变动的情况。这是职务犯罪侦查的有效措施。
银行或者其它金融机构,或者其他被要求提供材料的单位或个人,故意忽视或者拒绝执行命令,或作故意提供虚假材料的,将构成妨碍司法罪,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或并处罚金。新加坡《预防贪污贿赂法》第17条第2款规定:“任何人不向被授权人出示这些资料或提供这些帐目、文件或物品者,根据本法都将构成犯罪,并应处以不超过2000新元的罚金或不超过1年的监禁、或者并处。”
(二)对嫌疑人的强制调查
由于公职人员履行的是公共权力,与公务职权有关的原则和制度,如公务活动公开透明的原则、个人财产的申报制度、行政机关对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等原则和制度,是履行公共权力对等的义务要求,所以在职务犯罪的侦查中,嫌疑人就应比一般的公民犯罪负有更多的诉讼义务。为此,检察机关侦查局局长或其他侦查人员可以命令任何其确信有犯罪嫌疑的公职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到侦查局接受调查或提供书面陈述,说明属于他或近亲属的所有的动产或不动产,说明上述财产的取得的日期以及取得的方式,说明本人或近亲属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其他人较大数目的银行帐目合法来源。对于渎职侵权犯罪的嫌疑人,可以命令其说明任何与案件有关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依据,并可命令其交出任何归其占有、控制的文件和物品。必要时,侦查局的局长可以决定暂停其履行公职,或在问题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不得晋升或调职。如果被调查人故意忽视,或拒不执行命令,或作虚假的陈述或说明,将直接构成妨害司法调查罪,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之刑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条第3款规定:“本公约的宗旨:提倡廉正、问责制和对公共事务和公共财产的妥善管理。”该公约第9条具体规定了公职人员问责制的内容。这是我们建议采取上述强制性调查制符合国际刑事司法程序的依据。新加坡《预防贪污贿赂法》第22条也有类似的规定。
三、构建强制作证制度
由于职务犯罪查处更多的需要人证,而证人不愿意作证又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尤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这一问题更为突出。为了有效打击职务犯罪,必须建立证人强制作证制度。在美国,大陪审团调查公职人员腐败案件中,可以命令任何证人在陪审团宣誓作证,证人作证时律师不得在场,如果拒绝作证,将构成蔑视法庭罪;如果作虚假证言,将构成伪证罪,由大陪审团予以追诉。我们认为,在我国职务犯罪建立强制作证制度,具有可行性。强制作证制度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而我国却没有建立强制作证制度,这一制度的缺失直接影响我国各项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影响控制犯罪和司法公正的实现,但由于强制作证制度以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为前提。在我国目前不可能对所有的证人建立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现状下,在特殊类型的案件上首先建立强制作证制度和证人保护制度具有示范和表率作用,将来在国力允许的情况下,再将此制度推行到所有案件上。职务犯罪由于其比其它一般犯罪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以及以人证为主、没有直接的被害人等特点,急需建立强制作证制度,同时,这类案件相对较少,依我国现有的国力完全可以对该类犯罪案件的证人建立较为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因此,在职务犯罪的追诉中,首先建立强制作证制度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2条第1款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的法律制度并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适当的措施,为就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作证的证人和鉴定人并酌情为其亲属及其他与其密切者提供有效的保护,使其免受可能的报复或者恐吓。”该条第2款规定了保护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的具体措施,并在适当情况下允许不披露或者限制披露其身份和下落的资料。同时,规定允许以确保证人和鉴定人安全的方式作证的取证规则,例如允许借助诸如视听技术之类的通信技术或者适当手段提供证言。笔者认为,在我国应制定专门的法律,规定职务犯罪的强制作证制度和证人保护制度。侦查局可以要求任何人提供该类犯罪的证言,如果其知情却拒绝提供证言,或作虚假的证言,则构成妨害司法罪或伪证罪。
四、建立作证豁免制度
作证豁免权是侦查机关为了获得严重犯罪的重要证据,而免除证人因作证而可能遭受刑事追究的权力。作证豁免可以分为“罪行豁免”和“证据豁免”,前者是指因证人提供的证言可直接导致本人受到有罪的追究,因而应免除因证言而受到犯罪的追究;后者是指因证人证言的派生证据,可能使本人遭到犯罪的追究,应禁止以该证据的派生证据作为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制度。作证豁免制度是根据不必自证其罪原则确立的一项诉讼制度,对于查处严重犯罪,瓦解犯罪团伙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证豁免制度在英美法系较早得到承认和运用。在英国1965年开始确立作证豁免制度,在1980年《犯罪检控法》中得到进一步规定,并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得到运用。后来在美国、新加坡、我国的香港等地方得到了确认和发展。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虽然规定了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但没有规定不如实回答的制裁,也没有关于回答后的免罪规定,这既违反了沉默权的基本规则,又有自证其罪之嫌。笔者认为,应该制定专门的职务犯罪法,建立作证豁免制度。具体规定是,对于职务犯罪的同案嫌疑人,侦查局可以要求涉嫌罪行较轻的一人或多人提供证言,或者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如果拒绝作证或回答,或作提供虚假的证言或回答,将以妨碍司法罪治罪,同时不免除对其所实施的犯罪的追究;如果其如实提供了证言或回答,应将其提供的证言或回答全部予以记录,作为免除该事项对其任何诉讼的凭证。
五、规定对职务犯罪的技术侦查手段
技术侦查手段是指利用秘密监听、监视和秘密侦查员等秘密侦查的方式对犯罪进行侦查的特殊侦查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犯罪和进行反侦查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犯罪的智能化和隐蔽化程度越来越高。因此,必须运用现代的科技手段以及特殊的侦查手段方能有效地追诉犯罪。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规定了对危害国家安全罪、毒品犯罪、涉及枪支弹药类犯罪、有组织类犯罪的技术侦查手段,但从各国的法典来看,几乎没有规定针对职务犯罪的特殊侦查手段。由于职务犯罪的隐蔽性、极大的危害性等特点,通过一般的侦查措施很难有效地查处职务犯罪,面对职务犯罪的严重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0条对特殊侦查手段作出了规定,该条第1款规定:“为了有效地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域内酌情适用控制下交付和其认为适当时诸如电子监控或者其它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其它特殊侦查手段,并允许法庭采信这些手段产生的证据。”基于该国际公约的精神,应通过法律对各种技术性侦查手段和控制下交付程序作出专门的规定,并且规定这些特殊侦查手段所获得的证据可以不必转化,直接为法庭所采信。这是我们对职务犯罪运用技术侦查的法律依据。
由于技术侦查手段的秘密性,使技术侦查成为一柄双刃剑,既能有效地控制犯罪,又容易侵犯人权。正是基于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过法律规定了技术侦查手段的合法性,又从程序上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正如日本《关于犯罪侦查中监听通讯的法律》第1条所指出的:“本法的目的是:鉴于有组织犯罪严重危害安定、正常的生活,且对数人共谋实施的有组织的杀人、非法买卖药品及枪支等重大犯罪,如果不予监听犯人之间的联络电话或其它电讯,查明案件真相显著困难的情形在增多,为适当应对此种情况,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要的监听通讯的强制处分,确定其要件、程序及其它必要的事项,以期在避免不当侵犯通讯秘密的同时,准确查明案件真相。”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特殊的技术侦查手段,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199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这里的侦查指的就是国际上通用得技术侦查手段。侦查适用条件、具体的程序,以及所获得的证据的效力等问题,我国法律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这种侦查措施却经常被使用。为了使技术侦查手段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合法化、程序化、正当化,笔者认为,应该在未来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专门对技术侦查手段予以规定。
六、设置对职务犯罪的推定制度
法律上的推定是指在一定条件上,无须特殊的证明,法律上便视该事项为真实,除非以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推定制度,对于减轻举证方的举证责任具有重要的意义,其相应的加重了被推定方的举证责任,也是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倒置”。在刑事诉讼中,推定被严格的限制,但为了查处特殊类型的案件,在如果不实行推定,控方就难以举出有效证据,而举出相反的证据对追诉方来说又相对简单的情况下,法律上设立了推定制度。在刑事诉讼中,推定主要用以职务犯罪的案件上,因为犯罪行为人以公权力作为掩护,使得对该类犯罪的追诉变得相当困难,而被追诉方又比较容易提供自己无罪的证据。因此,世界许多国家都对该类犯罪设立了有限的推定制度。例如,对于刑讯逼供罪,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推定制度,由被控方负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举证责任。对于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8条设立了推定制度。该条规定:“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所需要具备的明知、故意或者目的等要素,可以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予以推定。”英国最早规定了贪污贿赂犯罪的推定制度,后来新加坡、我国香港地区对于贪污贿赂罪设定了推定制度。而我国没有设定贪污贿赂罪的推定,而是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进行治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贪污贿赂罪在性质上不同,在法定刑上,前者要轻的多,可以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给腐败分子就避重就轻、逃避责任提供了法律上的途径。故对于职务犯罪应通过专门法律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刑讯逼供、非法拘禁、报复陷害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犯罪,以及贪污贿赂犯罪的推定制度。这样可以减轻职务犯罪的侦查的困难,加强打击职务犯罪的效率,保护受害人的权益,保持公职人员的廉洁性。
七、对职务犯罪规定较长的追诉时效
由于职务犯罪具有隐蔽性的特点,应该确立比一般犯罪更长的追诉时效,以便有效地打击该类犯罪。为此,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9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根据本国法律酌情规定一个较长的时效,以便在此期限内对根据本公约确立的任何犯罪启动诉讼程序,并对被控犯罪人员已经逃避司法处置的情形确定更长的时效或者规定不受时效的限制。”因此,笔者认为,应通过专门的法律,对职务犯罪规定比一般犯罪更长的追诉时效。
*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系讲师,法学博士[100040]
- 中国检察官·司法务实的其它文章
- 地方动态
- 检察资讯
- 正义从哪里来
- 探索检察工作的和谐创新路
- 一把手、小圈子与攫取资源
- 正义从哪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