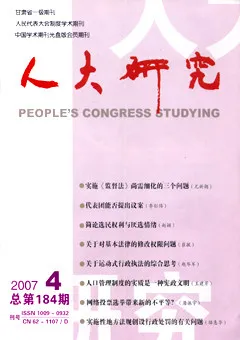简论选民权利与厌选情绪
我国选举法规定, 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民是享有政治权利的年满十八周岁的、具有参与国家管理行为能力的公民。
我们国家现在的选民大概可以分三类:第一类选民是主动参与型选民,他们有着明确的目标和对参与政治的热情,通过积极投票来选出他们心中的代表。第二类选民为被动参与型的选民,他们一般都认定选谁已经是一个既成的事实,选举只是一种形式。第三类就是消极参与型选民,他们不关心选举问题,更不关心选谁为代表,即是参加了选举,投票也比较随便。
一、选民在选举中的权利
一是选举权。在选举中选民有自由投票权,选民对代表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选他人,也可以弃权,既可以自己投票也可以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
二是知情权。比如,选举工作的日程安排、推荐的初步代表候选人名单、正式代表候选人是如何产生的、选票统计的结果等,选民都有权知道和了解。
三是监督和申诉权。选民有权监督选举过程的合法性,检举和控告选举中的违法行为。对公布的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申诉人如果对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人民法院起诉。
四是被选举权。选民还有被选举为代表的权利。
二、选举权的性质
一是个人权利说。当民主政治最早在英国萌芽的时期,选举权曾被英国人看做是财产权的一种。经过自然法学派启蒙思想家的论证,选举权被当作一项神圣的个体人权。洛克、孟德斯鸠等思想家依据自然法的立场,从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民主权等思想出发,论证了选举权是一项天赋的个人权利。他们主张人人有权参与主权的行使,参加投票就是表示意见的方式,从而全体国民就应该拥有选举权,选举权就变成与生俱来的不可让渡的权力,是人类的自然权力之一,国家当然不可以任意加以剥夺和限制。
二是社会义务说。这种主张认为选举是国家基于国家目的赋予国民的一种公共义务,而不是公民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这种学说强调的是个人责任,认为社会成员之间有一种相互依赖性,由于这种依赖性的存在,选举权是选民的当然义务,不得自行放弃,于是国家可以强制投票。
三是权限说。德国学者耶利克纳从国家法的观点认为,选举就是选任国家机关的行为,这种参与任命国家机关的选举,也是属于国家功能的行使,所以选举本身就是机关的活动。投票本身并非是个人行为,而是最高的国家机关行为,选举人在投票的瞬间就是国家功能的行使者,当他完成这个行为后,他就又回复到私人的地位。
四是权利义务说。他们认为选举权在本质上应该兼有权利和义务的性质。参加选举是国家赋予公民的权利,但公民参加选举的权利与其他公民权不同,它不是为了私益而设,不是为了私益的目的而存在的,只是为了社会利益。因此选举又是一项社会公务,是选民执行社会公益的职务,行使选举权构成义务。
在我们国家很多选民对选举权感到疑惑,不知道选举权是权利还是义务抑或两者都是。但是由于舆论和单位领导的行政命令、说服动员,再加上传统的道德观念,很多人认为选民选举是一种义务。笔者认为,实际上选民的选举权是一种权利,从法律上讲是宪法和法律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固有权利;从本质属性讲是一种基本权利;从基本内涵上讲是一种政治权利。
三、选民的厌选情绪
我国的人大制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民主化程度上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不可否认,在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中存在选民投票厌烦情绪,而且厌选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一些人不愿意搞选举,觉得选举费时、费力、费钱,是为选举而选举。在实践中,部分选民不参加选举活动或随意行使选举权,这无疑使选民的权利大打折扣,也与宪法的精神相悖,因此,找出厌选原因并寻求解决的途径是十分必要的。
(一)利益动机缺位,选举缺乏内在动力
选民参加投票选举代表是有一定成本的,为的是代表为自己代言发表意见,以维护自己的利益。选民让渡自己的权力给代表的成本、参加投票的时间成本、关注投票信息的成本等等都意味着选民需要选举带来收益,才能促使他们积极去投票,如果不能带来利益选民将会失去兴趣。虽然我们不排除一些人是基于政治觉悟和民主素养参加选举的,但大多数选民更关注自己付出的成本是否有收益。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就是选举和利益脱钩,人大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仅仅成为一个口号,并没有一套衔接紧密的程序使之成为一种有效的利益保障机制,选民的冷漠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代表与选民之间的疏离状态使选民对选举不关心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主要采用的是兼职代表制。代表以他的职业为本职工作,代表活动为辅助工作。代表们在本职工作上要有所建树,从事各种社会活动、业务往来或学术研究,往往无暇顾及代表工作。而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人大所议事项更加复杂化、专业化和议事工作日常化,兼职代表却没有精力和时间来很好地完成代表职责,传统上认为的兼职代表的优点恰恰成了缺点。还有不少代表是政府官员,他们既要参与决策,又要负责实施;既要代表选民,又要站在政府立场上。上述情形均使代表与选民联系不紧密。这种疏离状态难免造成选民对选举代表不热情。
(三)选举中的违法行为,使选民不满
应该看到现在选举中还有很强的“人治”化操作的因素,存在着违法行为。第一,选举机关违法。由于选举组织工作不细和公民的职业、居住的复杂性,出现错登、漏登选民的现象越来越严重。选举机关不依照法律规定的原则和人口比例分配代表名额,特别是为了照顾领导当选而随意划分选区等。有的地方的组织者为了省事甚至不组织投票找人代填选票,或者为了达到让某些人当选的目的篡改选票。第二,由于人大代表的政治光环使之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价值,在近期选举中贿选和拉票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
(四)选举技术不完善,选民对选举缺乏信心
选举制度设计是否合理、科学,将直接决定它是否能吸引选民。选民参加选举的一个基本前提是选民对选举制度的认可。我国现行的选举制度虽然经过20多年的发展,总体上趋于完善,但是在某些环节上还存在着“硬伤”,如,缺少竞争机制,“暗箱作业”、“戴帽选举”等。因为选民不相信选举的作用,所以选民也不会去追究选举的结果,形成了非良性循环。
(五)选民缺乏知情权
选举中任何一项权利被侵害,都会影响选举的自由与公正,知情权是一项重要权利。选举期间选民的知情权应该包括:选举进行的全部情况和信息,候选人的政治见解和政治主张,他的个人品质、政治素养和能力。选民只有获得这些信息,才能选举出真正符合意愿的代表。但实际情况是,普通的选民只知道候选人的名字,其他信息知道的少之又少,选民的这种状态我们可称作是“合乎理性的无知”。选民自己搜集代表的相关信息成本是很高的,如果选民感到自己的投票行为比较盲目,也会对投票活动持随意态度。
(六)生活、文化水平的制约
生活、文化水平的制约并不与选举的热情成正比,现在生活、文化水平高的人也缺少选举的热情,也存在着厌选的情绪。严格地说,生活、文化水平并不是选民厌选的原因,但是对于某几类选民来说,生活、文化水平肯定是制约他们选举的因素。第一类,贫困人口,他们对待选举的态度很朴实,但是由于生活环境决定了他们的需求层次只能停留在解决温饱的层面上,选举对于他们来说无关紧要。第二类是流动人口。他们除了少数安定外,大多数居无定所,户口又不在本地,所以他们没有在生活地投票的热情。
(七)追求高参选率,使选民产生逆反心理
高参选率历来作为选举成功的一条重要的经验。在追求高参选率的情况下,也就忽略了选民的意愿和情感,引起了选民的厌烦情绪。我们国家宪法和选举法都把选举规定为公民的权利而非义务,也就是说公民有不参加选举的自由。但是实际情况却是,许多选民被动地去参加选举。如此一来,选举不仅不能给选民带来参与的满足感,反而会使选民产生排斥感,把选举看成是额外的负担。“我要选举”和“要我选举”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前者表达了对选举的认同,后者则是一种消极态度。
参考文献:
[1]张明澎:《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蔡定剑主编:《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法律出版社2002版。
[3]杨逢春:《中国的选举制度与操作程序》,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
[4]刘嗣元:《专职代表制可行性再探析》,载《人大复印资料》2003年第5期。
[5]王世荣、王晓敏:《我国选民参与意识与选举制度的关联》,载《人大研究》2004年第11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