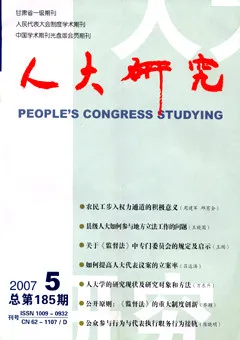农民工步入权力通道的积极意义
2007年3月8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了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盛华仁副委员长在作关于一线工人、农民代表名额的说明时指出:近几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中,工人和农民代表比例呈下降趋势,尤其是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人数偏少。还有,我国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这一标志性事件引起诸多媒体关注。
这则消息表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已经注意到了体力劳动者的利益诉求,人大代表的组成和结构的问题正在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普通工人和农民占全国劳动者绝大多数的中国社会,他们一直在人大会议这一利益诉求的制度性平台上发出足够的声音。历史资料显示: 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有3456人,工农比例为54%。近几年,农民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队伍数以亿计。人数众多的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足以影响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根据城市建设的需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农民工的数量在一定时期内还会持续增长,他们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主体,设置“农民工”界别的条件已经成熟。然而,作为一个新的阶层,农民工当选地方人大代表的还只是极少数,到现在为止,全国人大代表中还没有农民工。而同样是“新社会阶层”的民营企业家却正大量当选人大代表。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本届(2007年)人大的民营企业家代表比例是9.6%,比上届增长了140%,比上上届增长了860%。民营企业家群体的代表比例如此显眼,与农民工群体在公共政策决策中集体失语形成鲜明对照。众所周知,人大代表的组成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有产者和管理者等精英阶层占代表多数的话,最终形成的将是一种有缺陷的社会治理架构。因此,设置“农民工”界别,并且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工应占有一定的比例,应当视为改善人大代表结构的一个积极信号。
从制度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为农民工代言的人,绝大多数不是农民工。来自于社会其他行业领域的人大代表,虽然对于农民工权益问题不乏关注和S3Nlug0KC4iqgYUH+GtNRD/6490G7sP531l8sz/W14E=伸张,但要么因为角色冲突和身份限制,不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么因为精力有限,无法获得最翔实、最贴近实际的“一手资料”,从而让这种“替代式发言”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农民工的问题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他们自己的声音才最有说服力,农民工亟须在公共权力平台上播放自己的原声带。赋予农民工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的直接话语权,农民工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坐在代表席位上“代表”自己,行使神圣的当家作主权力,许多农民工切身的利益、权益因此就能得到相应的维护。
值得欣慰的是,近期,中国各地屡屡传来农民工当选地方人大代表的消息。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农民工戴全明当选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人大代表;重庆市忠县打工农民向世洪出现在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他是沙市区首位农民工代表。如今,农民工从当选地方人大代表到即将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说明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正不断向高层次推进。有人担心农民工当选人大代表后“代言”的质量,对此完全无须多虑。实质问题是代表什么人利益的问题,不是水平和发言质量问题,况且,“素质”和“能力”是会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的。因此,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中给农民工留出“位置”,不仅仅是一种包容,更是一种自我完善。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