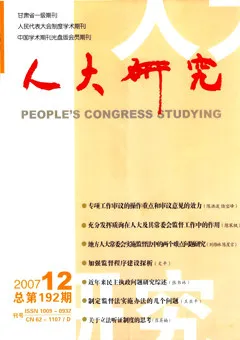浅议人身保护令制度
山西省芮城县学张乡董原村农民董甲宣,被怀疑杀害同村选举对手,于2000年8月11日被刑事拘留,在数次提审过程中,遭受非人的折磨酷刑,致使脚腕、胳膊上伤痕累累,肌肉严重萎缩。直到2002年2月10日,他才被糊里糊涂地放出来,累计被羁押540多天[1]!黑龙江省呼兰县双台镇村民宋德文,55岁时因“强奸杀人”被抓进看守所,一关就是7年零7个月,7里年,有关部门仅对他提审过3次。当他糊里糊涂地释放时,只能拖着一副双拐被儿子背回家[2]……缺乏合法手续而超过法定期限的羁押本身就是严重侵犯人权,我国的审前超期羁押还常常伴随着刑讯逼供、牵连家属、长年羁押不放、查处力度低的特点,成为漠视公民自由和尊严、亵渎法治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身自由是公民参加社会活动和享受其他合法权益的基础。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权利最容易受到损害的群体,对他们人权保障力度的强弱,是衡量一个国家人权发展水平、民主进步与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修正案中,对《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了一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在我国人权保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刑事诉讼法》也应当响应《宪法》新规定。应从立法上完善对被羁押者的司法救济制度,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效仿欧美建立自己的刑事诉讼人身保护令制度。
人身保护令是司法令状的一种。司法令状是由法官根据行政机关及其人员的申请签发的一种命令,根据这一命令,该行政机关及其人员在办理该刑事案件中被授予某一权利(如进行有证逮捕、有证搜查)或者进行某一行为(如根据人身保护令释放被拘禁者)。司法令状制度体现了司法权对于行政的监督,对于保障公民自由权利则是一个优良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原理在于:法院在保障人权方面具有特殊作用,这就是对其他国家机构行使权力的有力制约。
英国《人身保护令法案》规定:“没有法庭所发出的附有理由的逮捕令不得捕人。对于被捕人必须在二十天以内提交法庭审理,逾期应立即释放。”并规定了“人身保护令”制度,即被捕人或代表有权请求法庭发出命令将被捕人在一定期限内解送法庭,以审查其监禁理由,以认为无正当理由可立即释放,否则,法庭应依法定程序进行审判[3]。
《美国联邦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人身保护令之特权不得中止,唯在发生叛乱或受到侵犯出于公共安全必需时不在此限。”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定》必须“在无不必要拖延”的情况下将被逮捕者立即送往“最近的法官处”,由法官对嫌疑人实施“初次聆讯”。这种初次聆讯以开庭形式,负责逮捕的警察或检察官出庭提出控告,解释逮捕理由,法官要告知嫌疑人享有的权利,并就其是否允许仲释作出裁决[4]。
重视公权利的大陆法系国家在涉及人身保护令个人权利上与有着私权利传统的英美法系国家有所区别。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并未制定专门的《人身保护法》,但“任何人不受非法拘禁的原则”却深入人心。如德国规定:“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拘留或逮捕后,应毫不迟疑地被带到法官面前,最迟不能超过被拘留或逮捕的次日,由法官审查逮捕或拘留是否正确,要否维持已经签发的拘留证效力。”[5]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九条第三款规定:“任何被逮捕或者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第四款规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我国已于1998年10月签署加入该公约[6]。
可见,人身保护令制度已成为各国刑事诉讼中维护人权的一项普遍原则。
国外实行逮捕与羁押分离的措施,逮捕往往需要得到有权机关的司法令状方可实施。而逮捕的期限相对较短(往往为几十个小时),期满必须放人。如果要转为羁押,必须经法院的审判。所以,对于逮捕权的控制,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是:引入一个中立的、有权威的裁判者(通常是法院或法官)行使对侦查权的司法审查,以保障人权,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而我国则较为特殊,对侦查机关扣押、冻结财产,拘留犯罪嫌疑人等强制措施仅由做出行为的机关自行决定,唯有一项权力——逮捕需要经检察机关的批准,而这种“批准”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即检察机关毕竟是公诉机关,操持逮捕批准权不如法院行使该权利公允、居中,且整个过程没有赋予交给法院行使,这样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互相制约的原则。笔者却认为,依我国的司法现状,全盘吸收国外经验会造成水土不服。原因在于:
其一,我国没有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环境,法院并没有树立起抗衡立法权与行政权的绝对权威,还达不到“不受传统束缚而作出自由的判断”的完美状态。
其二,我国没有像英美国家那样的,与审判官相分离的治安法官、预审法官,简单地将司法令状的签发权转移至法院,更容易造成法官对案件的先入为主,更不利于法官的公正审判。
其三,我国检察院批捕的把关严格:(1)国外把检察机关定位为侦查机关,而我国检察机关的角色是公诉机关,检察官的全部诉讼活动的伦理基础是公共利益,而不仅仅是褊狭的控告人,要求对于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一律加以注意,维持了一定的公允性。(2)《国家赔偿法》规定了错案追究制度,检察机关应当对错捕案件的受害人进行赔偿。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公权力的滥用。
其四,如果将所有案件的批捕权压到法院身上,法院的工作量将不堪重负。那么,“法院以审判活动为中心”的制度构想将受到打乱和分散。
但是,检察院自侦案件的批捕权仍由检察机关行使,执行、监督隶属于同一机关似乎存有缺陷。所以,笔者建议仍然保留检察机关的批捕权,但是属于检察院自侦的那一部分案件的批捕权应当交由法院行使;同时赋予被羁押人申请人身保护令的权利,规定:被逮捕的人如果对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决定有异议或者认为侦查机关超期羁押的,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通过有控辩双方参加的听审程序,审查申请人的请求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应当将被羁押人立即释放[7]。这样,既可以减轻法院审查的工作量,又可以完善审前羁押的监督制度,还不会对现有的司法构架造成太大的冲击。
杜绝审前超期羁押不是仅靠一项人身保护令制度就可以实现的,还需要建立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创造良好的大环境:
(1)充分利用人身保护令保障自己的权利,需要由有着法律素养和法庭经验的专业律师提供帮助,以弥补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不足。因此,应当建立强制辩护制度,加强犯罪嫌疑人的防御能力。
(2)看守所划归比较“中立”的司法行政机关,实行侦查机关与羁押机构的分离,防止公安机关“自己抓、自己管、自己审”以及超期羁押等侵犯人权的现象发生。
(3)确立自白任意性规则,完善刑事证据规则。将在超期羁押期间获得的口供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从源头上遏止办案人员通过超期羁押获取口供的恶习。
(4)对普通案件、经济案件能不羁押尽量不羁押,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作为替代措施,缓解羁押场所的压力。
(5)降低侦查终结的条件,缩短侦查羁押期限,将案件调查重心移向审判阶段。
(6)对司法人员的超期羁押行为进行制裁是克服审前超期羁押的补强措施。对后果不严重的人员可以给予必要的行政、党纪处分;如果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诉诸刑法。
注释:
[1]《超期羁押严刑逼供两纸国家赔偿难赔数年冤》,载《海峡都市报》2003年12月7日。
[2]李韦君、李永明:《他被超期羁押7年7个月》,载《检察风云》2004年第5期。
[3]陈光中:《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
[4]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294页。
[5]程味秋:《外国刑事诉讼法概论》,中国政法大学1994年版,第147页。
[6]陈光中、张建伟:《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法》,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6期。
[7]张健伟、赵琳琳:《论检察机关批捕权的完善》,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7期。
(作者单位:人民公安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