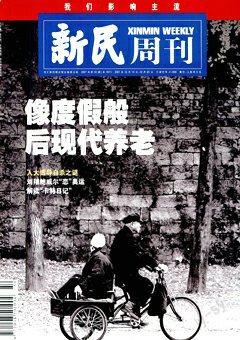他在探索生命的终极
贺莉丹 张益清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朱立元是余虹的朋友,还是他博士论文答辩会的主持人。朱教授说,余虹生活经历很坎坷,但这一切绝对不是造成他自杀的原因。
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12月5日13时用跳楼自杀的极端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后,12月7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朱立元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采访,追忆与缅怀曾经的爱徒、挚友余虹。

朱立元教授在主编中国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时,曾邀请余虹参与编写其中两章(1997年出版),两人因此相识,余虹当时博士未毕业。
此后在广州暨南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应余虹的博士生导师饶芃子教授邀请,朱立元教授主持了那次答辩会,评委组给予余虹的论文高度评价,“我们对他的印象最深,他的博士论文水平很高”,朱立元教授回忆,该篇论文就是后来编撰成书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
为继续深造,余虹申请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作为余虹的联系导师,朱立元教授与他亦师亦友。
他重情义重朋友
在复旦博士后流动站的时候,我是余虹的联系导师,主要是他自己工作,平时有空我们一起讨论,后来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我觉得他是一个性情中人,既有才气又很重情义的一个人。
余虹曾在华中师范大学做过老师,工作一段时间后,暨南大学饶芃子教授招收博士,他就报考了饶老师的博士。从暨南大学博士毕业后,他申请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工作站,直到2000年6月份出站。在博士后流动站期间他还被聘请到海南大学兼任文学院院长,本来他是想回暨南大学的,后来在征求饶芃子老师的建议后,他觉得可以在海大做些事情,于是就去海大任职了一段时间。虽然事务比较繁忙,但他也没有耽误他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就是后来出版的《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写得也很出色。在文艺理论方面,川军(四川学者)很厉害,他是其中之一。
其后,他来到了上海师范大学,呆了一年左右,2002年离开上海去中国人民大学工作至今。
在生活中,余虹是一个没有戒心、可以无话不谈的人。他虽然很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但他为别人想得蛮多,所以大家很信赖他。即使有些观点不同,讨论、商量都没什么,感情才是最重要的。
在上海时我们经常见面,他到了北京之后,我们见面机会少一点,但感情仍然比较深。每次我去北京,他都会开车来接我,邀请我喝茶、送我去机场,每次出国回来他都会给我打电话,很亲切地慰问……这些都是他重情义的表现。
今年11月12日,我去北京出差的最后一个晚上,人大的朋友知道我在北京,一定要请我吃饭,他们也通知了余虹,但后来得知余虹最近胃不舒服、人也消瘦了。7点多,余虹给我打电话说,“真想见您,很想念您,但是下午上了三节课,回家之后人很累,很虚”。我说不要紧,来日方长,叫他多多保重身体,他回答,“不要紧,逐渐在康复中了”。
没想到竟成了我们的最后一次通话。
他电话最近一直关机
我也没想到(他走得)会这么快,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按照他平时的性格,不一定会采取这种方式。我跟他的第二任妻子也是好朋友,据她所说,余虹平时在家里也不是很多话,但跟我们朋友在一起他是很健谈的,并没有表现出很内向、不开朗的感觉,所以我才感到有点不理解。
从事业上看,他总的来说也不错,领导对他很重视、工作做得很出色、学院对他也很器重,我觉得他找到了比较合适的位置,而且有了更大的平台发挥他的才能。他现在是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还是人大《文艺理论》期刊主编,虽然有工作压力,但他是一个很会拼的人,喜欢踏踏实实工作,还很愿意这样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杨慧林院长也看重他的才华,委以重任。当时他刚从博士后流动站出来,有一定影响,但还没有现在这样的名气。
我认为(两次)离婚等家庭问题都不构成(他自杀的)原因。我知道距离他第二次离婚已大约有两年了,两次离合的经历应该还不至于让他走这条路。他离婚之后我们还见面很多次,都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而且我知道他在这个(婚姻)问题上挺通达的,能合则合,不合则分。他与第一任妻子有个儿子,现在在国外留学,出国之前在人大读书,余虹对儿子很尽责,(儿子)考上大学后就一直(跟他)住在一起直到出国。(感情问题)绝对不是造成(他)自杀的原因。
我知道他的朋友很多,朋友之间来往也很密切。
他说过他胃不好,人又在消瘦,我曾想,是不是因为有病,怀疑有没有得什么绝症,但据他身边的朋友讲他的病也不是绝症。
后来又听说他近来有抑郁症,这个病是可能走极端的。不知道是不是最近有什么事情刺激到他,还是早就有了而大家没有发现?我就不太清楚了。之前也有通话,听他讲话还是很开朗的口气。不过听他朋友讲他最近的行为有点怪怪的,他电话最近一直关机,至于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机)、什么原因,就无从得知了。
我是在当天晚上7点多收到原来复旦大学博士后朱国华的信息,才得知这个消息,我立刻给人大文学院副院长张永清发短信询问,他立刻回电话证实了这一消息,大家都觉得很突然,根本不相信,觉得太不
可想象、不可思议了。北京有影响的学者曹卫东、王岳川等,有很多都是他的朋友,还有他的同事,(他们)经常在一起却都没有看到。其实抑郁症应该有些征兆。
(记者问,余虹教授的博客最后一篇是在9月份写的《一个人的百年》,表达了一些他对生与死的看法,这有某些征兆意味吗?)
可能那时(他)已有一些想法了吧,他两年前写了一篇《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就是探讨了生命与存在的哲学终极问题,这种形而上的思考往往对学者有很多(极端)的影响,尼采最后不是精神失常了吗?
余虹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学术上、情感上都很敏感,在精神上涉及相对敏感的问题可能会钻牛角尖;他也是一个很有艺术气质的人,他在上海曾买了一套房子,都是他自己设计装修。
我知道他过去的经历很坎坷,“文革”时他的家庭遭受了不公待遇,对他的冲击非常大。那段时间他的头发一下子脱落许多,后来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帮他的书写序时,就说他有一个“苏格拉底式的脑袋”,因为他前额很宽,又很发达。他很会思考。真是没想到会走这条路。(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