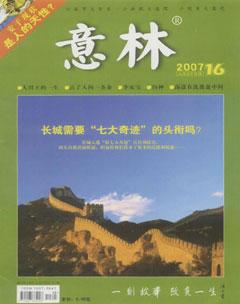你的巴尔扎克在我这儿
朱 砂
接到那个人的电话的时候,我正在给儿子织毛衣,手中的不锈钢针忽然间就落在了地上。
他问:“知道我是谁吗?”我笑而无语,那一刻,温馨的波动在心头滚过,敏感的心被一种情愫包裹着,感情就像透过玻璃窗洒在地板上的月光,清冷而又带着一丝激动。
他小心而平静地诉说着多年以前自己是如何一个人站在风中的月台上忍受着那久候不至的苦等,语气哀而不怨。可是他却不知道,那时那刻一个女孩子正躲在柱子后面窥视着那个东张西望的少年泪流满面。那些曾经焚尽五脏六腑的尘缘无论何时总让人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绪。
那一年,我答应毕业后随他去他所在的城市,可最终我反悔了,我无法拒绝已丧失了劳动能力的父亲那期待的目光,我知道没有什么比自己留下来更能安慰他苍老的心。火车开走的时候,我用指尖儿一点一点地抠着站台上那根水泥柱子的石缝儿,心里默默地呼唤着一个人的名字。
人的一生中总会遇上无奈的时候,有时只有选择放弃。
此刻,温柔的电波传递着属于那个年代的故事,诉说着那个远渡重洋的男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如何将思念折成一只只纸鹤投入窗外静静流淌的泰晤士河,一切仿佛很遥远又好像就在眼前。
“还记得你最喜欢看的那本《巴尔扎克全集》吗?它在我这儿,毕业那一年我从你的书桌里偷去了它,我想我的身边总得拥有一点儿属于你的东西吧!”
他像个犯了错的孩子,嘿嘿地傻笑着,笑出了我的眼泪。
“如果你想要,我就把它还给你,我知道你一直很喜欢它的。”
我无语。
我想要的,又岂止是一本《巴尔扎克》?
屋子里很静,电视上,一个叫苏丽珍的女人穿着高跟鞋独自走在去《星岛日报》的路上,她在路边买了一张报纸,她看到了那个让她柔肠寸断的男人写的武侠小说正在连载。她坐在街边的长椅上读,这段是写一个剑侠每天对着一棵很苍老的树练一套“黯然销魂”剑,累了便对着老树的树洞倾诉着对那个女人的思念。她知道他想她,就像她一样。这一刻,他就在离她不遠的办公室里。她哭了很久,最终,她把那张报纸放在了长椅上,然后,一些陌生人便看到一个穿旗袍的美丽女人的背影消失在码头的尽头……
许多时候,生活本身就是这样,没有太多的重逢、惊喜和巧合,擦肩而过倒是常有的。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那个时代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
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寂寞独处的时候会偶尔想起我,然后莞尔一笑,我已知足。
轻轻地把那张写着一长串数字的纸片儿揉成一团扔进纸篓。我知道,无论是我的《巴尔扎克》,还是曾经的《花样年华》,逝去的永不再来。
(刘洋摘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