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加尔各答到上海
汪 伟

印度的问题也属于中国,印度的答案却只属于印度。
陌生的邻居
小额贷款项目"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不久就到中国来访问,与央行的官员讨论了中国农村金融开放的问题。会见的性质是务虚的,中国农村金融的困局也没有因此有所突破。但会见本身却很罕见,因为尤努斯是一个来自东方和第三世界的金融实践者;近30年来,中国经济问题几乎从来没有问计于西方以外的经济学者。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孟加拉的近邻印度有着传统的历史和地缘联系,都正经历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速经济增长,而且正在和即将面临相同的历史难题:农村的城市化、贫富分化、国际分工中的定位和能源匮乏,以及新形势下的地缘政治。这些问题的解决没有先例可循,需要两国的政经和文化精英寻找新的路径。那么,中印之间有没有可能吸取对方的地方性知识的成果,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这种可能性在未来也许是存在的,但眼下,两个超级人口大国却处于极度的隔膜之中。
中国有过向印度学习的历史。但这段历史似乎已经被全面超越---或者是忘记掉了。自佛教东传到近代,印度与中国文化源流的复杂渊源,极少有人再提起。而20世纪以来,中国与印度的隔膜,大概以最近30年为最。中国人对印度的了解,仅限于一些残存无多的片断,而且,这些片断往往存在无意或者刻意的歪曲。以甘地为例,甘地的中国形象是第三世界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爱国者,谋求国家独立的民族英雄,然而,他对世界影响最大的"非暴力"精神,因为与"阶级斗争"和"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哲学格格不入,被视作小资产阶级根深蒂固的软弱性的代表。在如此基调之下的印度叙事,当然有其复杂之处。但是实施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印度,仍然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尼赫鲁与周恩来的一段外交佳话,在中国一度差不多家喻户晓;而两国在1960年代的军事摩擦,更加使中印的历史表述,增加了些许冷战色彩和亚洲地缘政治的微妙。
随着中国在1978年重新向西方打开门户,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也即知识和道德两方面,印度重新变成了一个中国人眼中相当陌生的国家。
进入21世纪之后,关于印度与中国,孟买与上海的对比,这几年听到的着实不少。这种对比往往着眼于揣测两国在未来的世界分工中的位置:有些人担心未来的"世界工厂"将从中国迁至印度,另一些人则热衷于讨论民主制度与GDP增速的关系。这些话题本身是重要的,但是很少看到精辟之论。
这也难怪。30年来,先是在中国的知识人群,后是在中国的普罗大众之中,早已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发展观念。这种观念的核心是面对西方,向欧美国家学习经验。这是30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核心,也是动力所在。
中国问题
由于少数知识分子的努力,来自印度的声音,近几年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杂志和学术会议上。汪晖和黄平主编的《读书》杂志,以一种有争议的姿态,坚持刊登一些对印度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评述的文章。汪晖本人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常常对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隔膜感到遗憾。汪晖的朋友,上海大学的王晓明教授大概也同样感到了这种遗憾之情。6月15日,在王晓明主持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他强调说,会议将请加尔各答社会研究所所长,同时身兼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的印度学者帕沙•查特吉作会议主题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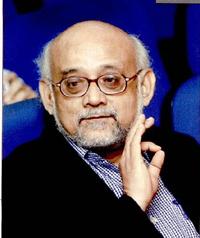
会议是由上海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和亚洲文化研究学会发起的,标举的是"文化研究"。这一196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学术思路,最初的研究对象是大都市中的消费行为,传入中国和印度这样传统的小麦与稻米产地后,一直经历着语境错位的尴尬。当然,不能说在中国进行文化研究一定荒腔走板,或者说,学者都在为赋新词而强行隔靴搔痒---但荒腔走板或者强赋新词的情形,也并不罕见。但这次帕沙•查特吉至少是搔到了痒处。
16日,头发斑白的查特吉在题为"21世纪的农业文化"的演讲中劈头就道出一个令人惊异的"个人结论":所谓的"第三世界"这一说法,已经过时了,因为亚洲和非洲走上了不同的经济发展轨道。他认为,中国和印度经历的惊人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当然,在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和原始积累过程中,两国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相当多农民失去了土地,却不能被资本密集型和技术依赖型的工业所吸收,如果政府没有安置政策,就可能失去生计。
"传统的用武力镇压农民反抗的方式在今天失去了合法性",查特吉说,政府不得不寻求资源给失去生计的人提供其他的生活手段,以此来抵消原始积累的后果。
当他在演讲中说到这一点时,我们突然看到了今天的亚洲现实,如何将两个邻近却隔膜的国家的社会思想连接在一起。查特吉的演讲主要基于他的印度经验,然而其描绘却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现实的困境。
中国的经济学者如温铁军对中国农村现实的描绘,实在与查特吉的演讲相去不远。中国的经济学者如茅于轼进行的小额贷款实验,实在也与查特吉的"非公司资本"本质相同。他的预测,"21世纪亚洲国家的农业社会一定能生存下去,但条件是必须在农村中容纳很大部分的非农业部门"更是耳熟能详,听起来和"离土不离乡"的说法相差不多。在上海,查特吉说,"作为非公司资本的农业活动将继续发展,在其内部寻求满足农民生存所需的办法,将决定农业社会和农业文化的未来。"我唯独不能确定的是,这种基于印度经验而对亚洲农业的前景做出的描述,与林毅夫等经济学家有关"新农村建设"的论述,到底有几分相似。
印度答案
帕沙•查特吉刚刚在中国出版了第一本著作,《被治理者的政治》。其中重温了亚里斯多德的一项基本政治学命题,即"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而现今的政治理论尽管并没有接受亚里斯多德的政治理想,但是所有的社会治理仍然建立在"并非每个人都有统治能力"这一前提之上。
查特吉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他自己的政治理论:今时今日,世界上的大部分被治理者没有治理的能力,却有能力选择自己怎么样被治理。他为自己的理论提供了印度的论据,其中包括三个因为经济发展需要而遭遇动迁的印度居民的故事。这三个故事像极了中国一些地方目下的动迁现实。然而,问题解决的方式,却是纯粹印度式的:这些居民通过选举,找到了自己与治理者之间的调解人,也即政治代表。
对中国人来说,帕沙•查特吉对被治理者的生存状貌的描述,某种程度上颇为熟悉,但是很难同意他的结论:"世界上大部分人民正在发明新的方式,根据这种新的方式,他们可以选择他们应该如何被治理。"查特吉认为,被治理者通过选举中的票箱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是一种新的民主政治---首先,这真的是一种新的民主政治吗?其次,这种民主政治的形式,似乎并未如他所乐见的那样,在亚洲正在生根发芽乃至遍地开花,成为"世界上大部分人民"的选择。
从这一点来说,帕沙•查特吉的著作给我的印象和尤努斯的著作《穷人的银行家》给我的观感类似。很难从旁观者的角度去阅读查特吉基于南亚地区的政治学著作,他描述的历史面貌与我的经验总是惊人的相似,而他尝试的解决问题的路径总是与我们的经验大相径庭:印度的问题也属于中国,印度的答案却只属于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