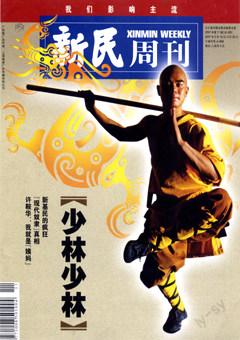只有人性的眼神在变迁
陆幸生
已有文章评说,这次奥斯卡获奖外语片《窃听风暴》是一次“伦理想象力”的胜利。从文化作品的“正面”理解,想象力是针对世俗生活的实际匮乏所作的理想式样的虚幻补充,也就是《红楼梦》所谓的“假作真时”。影片中的特工窃听者维斯勒,因为听到耳机中传来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而泪水盈眶,因为看到布莱希特“初秋九月”的诗句而心弦震颤,因为对于男性长者自戕的哀鸣,因为对于女性丽人遭辱的愤懑,最终他背弃命令,隐瞒和虚构每天的窃听报告,使得一份发生在眼皮低下的揭露文字,得以跨越高高的柏林墙。窃听者拯救了艺术家;在观众眼里,窃听者也拯救了自己。影片结尾,当年的窃听者如今是统一后德国的一位动作机械的送报人。影片没有使用一寸长度的胶卷,来记录他可能必定会受到过的审查和惩罚,这可被视作编剧、导演和观众都非常愿意而且喜欢给予的,对于人性的一次奖励。

影片是好看的。只是,将这部电影故事的脉络发展和结尾定格,最终定位在“一个不是根据生活本身而是根据生活逻辑、伦理逻辑编造出来,而它相当具有说服力”的位置,这实在是评论者出于“伦理想象力”过于大胆的“艺术”判断。剧中人物、情节、场景等等安排和结构,是作品创作者们的天然自由,只是,影片交代的年代背景是确凿的,这个背景当然包括了“四年后”柏林墙倒塌的史实。既然是电影艺术家的手“触碰”到如此宏大当代事件的真实墙壁,作为观众的我们便无法断说,那堵存在过的真实墙壁是由于伦理逻辑的“编造”而倒塌、而被拆除的。
作为境外的电影奖项,对于全球范畴“外语片”的抉择,奥斯卡有自家标准;这多元世界多元规则的选择题的解读,不是这篇短文能够承担的。只是,对于“编造”的结论,人们大抵都会不屑。
《窃听风暴》的男主角,窃听者维斯勒的脸部几无任何表情。这是他工作特质的标志,也是他保护自己的必需。影片中,在柏林墙倒塌后的时间段里,维斯勒出现在屏幕上的,都是背影。即使他沿街送报行走,给观众的也仅是侧影。只有在最后,手捧剧作家的著作,导演给了他一个特写,这是维斯勒在影片中唯一的微笑。结尾的对话是意味深长的:
服务员:书要包起来吗?
维斯勒:不用了,这是写给我的。
包裹或者包装,都被卸去。对于人性,无论怎样地深说“浅说”,其底里永远是一块不会干涸的沼泽地。而维斯勒绿色眼球闪动着的,就是这样一种温暖的复杂光芒。
《窃听风暴》让所有男人都活到了最后,好人剧作家活着,坏人文化部长活着,从坏变好的人维斯勒更活着,而仅有的女人死了。极具风范的女演员主角,在影片中富有象征意义地洗了三次澡。首先为庆贺演出成功,等候自己伴侣、剧作家归来的“爱”;其次是遭受文化部长车内强暴后的“自我肉体扫除”;最终是被不可抗拒力强迫签字,继出卖肉体后,更出卖了灵魂,准备了断此生的最后净身。风暴掠过是废墟,死去的女性是永远不能重建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