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四周年祭
梁 强
颜色革命国的分化
格鲁吉亚警察前不久在第比利斯街头采用暴力手段强行驱散反对者的示威活动,造成现场600多人受伤,当局还采取包括关闭私营电视台、通缉早前取保候审的政敌等种种措施打压反对派,尽管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出版物对此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绝大部分观察家都认为,这即便不是萨卡什维利走向独裁统治的第一步,也是格鲁吉亚民主进程的大倒退。
萨卡什维利通过2003年11月23日“玫瑰革命”上台后,许多西方媒体认为,这样一位行事果断、年轻有为、具有美国背景的领导人将带领这个高加索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从而将格鲁吉亚从1991年独立以来连绵的国内动乱和分裂危机中拯救出来。但最近一个月里萨卡什维利在第比利斯所做的一切显然不是西方成熟民主国家惯用的方式,其对国际舆论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第比利斯当局这几年在国家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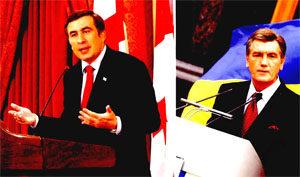
对格鲁吉亚当局指责最为激烈的恰恰是它的颜色革命“盟国”乌克兰。该国的报纸认为第比利斯当局2007年11月7日的镇压行为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首先,它歪曲了原本是和平抗议的颜色革命的性质,从而给俄罗斯以新的证据来继续攻击这场革命,而这是所有革命者都不希望看到的。同样,这样的行为也使得格鲁吉亚本国的国民将自己的总统仍然视为一个传统的独裁者,而他领导的革命所要争取的民主只不过是一种表象。第二,萨卡什维利制造了在颜色革命国使用武力的先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倒退,这样的决定在将来必将付出昂贵的代价。第三,也是最危险的,萨卡什维利采取了封锁媒体和管制新闻的措施,这样的举措只能发生在那些极权国家,用来对付本国持不同政见的人身上,但现在却成为民主国家的一个污点。
乌克兰媒体的激烈批评不是无的放矢。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虽然最为成功,但却是先天不足,民主选举和大众政治的结合一度造成一个立场激进的少数党上台组阁,这在民主政治更为成熟的西欧几乎不可能发生。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妥协”才成为新政权建立后最常用的一个词,不仅要与战败者妥协,胜利者内部也要妥协。因此,这个国家即便经历了长期的宪政危机,现在也仍然能处在一种微妙的稳定当中。而格鲁吉亚当局现在采取的这种以武力解决冲突的方式让乌克兰媒体担扰,第比利斯所发生的一切将影响到乌克兰政治的健康发展,萨卡什维利的行为如果得不到有效的阻止,很有可能成为乌克兰政治生活效仿的恶柄。
颜色革命4周年之后,颜色革命国都先后步入不同类型的政治危机(吉尔吉斯斯坦在最近的两年里之所以保持相对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南于外部力量干涉,而不是新生政治体制自然运转的结果),俄罗斯卡内基基金会研究员卡马斯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对这些颜色革命后新上台的政权采取了一种过于激进的政策。比如,美国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报告认为,“任何国家都有选择谁是自己盟友和实施怎样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自由”,并要求美国对前苏联那些认同美国这一立场的同家采取更强有力的支持。虽然布什当局也确实在一如既往地贯彻这一政策,但这种支持往往过于主观和单一,不管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条件如何,都鼓励其尽快加入北约和欧盟,这不仅造成了他们与俄罗斯之间的敌对,而且也造成了本国发展道路上更多磕磕绊绊的出现。
对于颜色革命国来说,不管出现怎样的分化,革命不管来了还是走了,实际上都不是决定这些国家民主进程的唯一因素。历史证明,要真正建成能够平稳运转的民主社会,取决于革命成功后的多种因素,并且这一进程也很有可能遭受挫折。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革命已经过去了4年,但转向民主甚至是法治国家的进程,在这些国家却依然是一个远未完成的任务,它要比革命者们当初所宣称和设想的复杂得多。后颜色革命国的转向
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2000~2005年发生在塞黑(2000)、格鲁吉亚(2003)、乌克兰(2004)、吉尔吉斯斯坦(2005)等国的颜色革命,曾经一度掀起了欧亚半个大陆的革命风潮,追隨这种风潮的大多都是年轻人,他们乐观、爱国、充满激情和信仰,决心推翻那些盘踞在他们头上的虚伪、反动、官僚主义和极权统治的老一辈们。这样的革命对他们有益,但这场革命的最后结果却是以革命者们的失望而结束。除了颜色革命国本身的分化外。原来预想的后颜色革命国纷纷转向,成为阻止颜色革命蔓延的新堡垒是最主要的原因。
德国汉堡大学政治学教授克拉斯杰夫认为,颜色革命尽管充满着激情,但却建立在错误的政治变革模式上——人民大众政权有时候确实能改变历史,比如俄罗斯1990年代初发生叶利钦对保守派的革命——但如果革命的源头和援助都完全来自外国,那结果很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民主并不一定就必然“生产”民主,或者说带来民主。此外,伊拉克战争对美国软力量和美式民主合法性的削弱,以及美国对独联体国家采取的双重标准,也使它对这一地区的政策丧失公信力(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完全是出于战略利益的考虑,切尼指责克里姆林宫是极权主义,却赞扬哈萨克斯坦在民主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外围因素让传统的反美情绪找到了新的增长点,从而极大地抵消了美国所希望的民主化进程的效果。最后,欧盟扩大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也使得该组织对这些国家的吸引力降低,颜色革命国在入盟道路上面临的新的竞争和其它的遭遇,让别的独联体国家不再相信当初西方领导人的保证,“如果你们像我们一样,就将成为我们的一分子”。
再者,如同出过天花就自动免疫一样,后颜色革命国家的领导人很快就学会了如何预防和阻止新的颜色革命在本国发生。俄罗斯官方2005年初组织的一次颜色革命专家研讨会上得出了如下四点结论:第一,非政府组织与本国境内社会组织的联系是革命的主渠道;第二,非政府组织对政治选举的结果造成了很大影响;第三,国内和境内不受控制的媒体对本国的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四,专政政权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开始时未能果断采取强力措施,从而导致这一运动迅速扩大。颜色革命在格、乌、吉成功上演后,这些国家新的领导人采取了一切措施来排除这些因素在本国的影响,包括限制外国和当地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对国外记者进入本国和在本国采访加以限制,通过新的选举法禁止媒体在选前进行民意调查和公布结果,并限制国际观察员和新闻记者对计票的监督权,分化反对派政党的联合,将潜在的政治对手以种种罪名予以“政治流放”,资助成立维护现政权的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以争夺对社会力量的行政主导,通过立法和收购加强对本国媒体的控制等等。所有这些举措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地利用自己所占据的行政力量,确保其政权统治的稳固。
颜色革命当初的主要指向国俄罗斯,这时也成为前苏联地域内那些渴望维护自己
政治统治稳定国家的靠山。这些国家在冷战刚结束时对于俄国的政治经济压力的第一反应是请求美国的保护,但克里姆林宫成功地利用它们对于颜色革命的恐惧,使它们相信美国正是这些革命的幕后操纵者,从而让这些国家重新回到莫斯科的羽翼之下。对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来说,他们宁肯与克里姆林宫对本国的控制作妥协,也不能接受被国内的革命运动所推翻的命运。而克里姆林宫也准备投入更多的钱,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专家,来帮助那些一度脱离莫斯科道路的前苏联国家重建经济,就像当初西方对这些国家所做的一样。
新政权合法性的获得
颜色革命国的分化,后颜色革命国的转向,其实体现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即如何确保政权的合法性。一般来讲,政权合法性的获得主要通过三种手段。
一是民主的手段。颜色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权力交接是直接导火索。颜色革命的发生,与前苏联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老一代政治领导人退出政治舞台的权力更替,以及这些地区逐渐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政治精英努力走上政治舞台的历史性进程,在时间上紧密地契合在一起。但政治体制的落后,使得这些国家每一次正常的权力重新分配——如议会和总统选举——都无法按照真正民主的方式进行,造成新的政治力量难以顺利过渡到前台,成为了政治动乱的导火索。乌克兰的例子最为明显,在“橙色革命”之前,乌克兰经济连续5年保持增长,平均失业率也只有3.8%,這个国家爆发革命的导火索,更多是来自普通民众心中多年酝酿起来的追求政治民主和更多公民自由的政治诉求。
因为这种天生的民主性,颜色革命国的新政权虽然在革命成功后面临着种种危机,但却并没有遭遇到严重的合法性问题。反过来,虽然后颜色革命国对和平性质的民主运动的打压,可能在短时间上能维护现有集权统治的稳固,但却很难确保这一体系的长治久安。前苏联地域内民众追求民主化的进程注定是无法阻挡的,对这种历史潮流的人为遏阻,结果可能导致新的革命运动的产生,而它的手段或许将不再是和平的和民主的。
二是政权的功能性手段,具体来说就是要确保所代表主权地域内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颜色革命在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爆发的重要原因是国家长期处于赤贫状态,有限的经济增长也很难被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困阶层所分享,因此,贫穷和贪污腐败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很容易就制造了革命的土壤。尤其是在吉尔吉斯斯坦,相比于集权统治,贫富差距所引起的广泛社会不满更是这个国家爆发革命的直接原因。反过来,当后颜色革命国纷纷采取了诸如提高社会福利,改善普通人生活条件等“安民富民”措施后,这些国家群体性抗议运动明显减弱。当然,这到底是因为政权职能的改善,还是因为搭上了国际能源及矿产资源价格迅速上涨的快车,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
三是民族主义的手段。苏联解体一度导致莫斯科的附属国发生剧烈的社会转型,原先起社会维系作用的传统道德观念、习俗和组织体制无可挽回地被削弱和毁坏,大众心理严重不适甚至强烈动荡,在此情况下,民族主义凭借其广泛的认同感,给这些新生民族国家提供了强大的凝聚力。而“促成一种民族主义产生的往往是对另一种民族主义的敌视”,因此,在颜色革命中,毫无例外地都表现出了明确的反俄倾向。尽管在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过去两年后,民意重新回归亲俄罗斯的一边,但反美却又成了一种替代性的民族主义潮流。
这样一种指向性过于明确的民族主义,对于客观上需要在俄美之间维系平衡的颜色革命新政权们来说,的确是代价太大的。乌克兰人再也无法从莫斯科那里得到廉价的天然气,而格鲁吉亚在得罪了俄罗斯这个主要的贸易伙伴后,经济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现在几乎完全依附于华盛顿。这种依附并不是双边贸易上的,而是对美国单边援助的依附,因此它毫无疑问要对国家的主权造成损害。更关键的问题是,美国再富有再慷慨,也无法保证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无法让阿布哈兹和南奥赛梯回到第比利斯的法权之下。萨卡什维利也许是尚未认识到这一点,也许是他认识了这一点但却不得不利用强硬民族主义来捍卫他在国内的政治支持率,总之他在南奥赛梯问题上的立场使他与普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处于敌对中。两人有限的会晤,也是由于普京想向美国人表明,他并没有关上谈判的大门,但会谈不会带来任何的结果。萨卡什维利今年年初公开的反俄讲话更是刺伤了普京,莫斯科一直没有对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提出过异议,但今年夏天俄罗斯外交部首次表态,“问题在于这种完整是否真的存在”。
相比之下,亚努科维奇在成为乌克兰总理后,乌克兰的反俄和亲俄民族主义获得了一种调和,在俄乌天然气供给问题上双方实际上都摒弃了简单的民族主义立场,而成了实用主义者。这种调和的联动效应很明显,克里姆林宫对当初干预乌克兰选举和企图与乌克兰、哈萨克、白俄罗斯建立经济联盟的政策予以反思;白宫最终也赞成亚努科维奇与尤先科达成妥协,在前者上任后,北约再没有在高层会议上提及乌克兰何时加入北约的问题;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也达成协议,决定在2008年之前不会举行任何有关加入北约的全民公决。
如果说颜色革命之初给中国带来挑战更多的是在对外政策领域,媒体和大众也更多的是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那么今天在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分化和转向的情况下,我们同样需要审慎思考那些颜色革命国家曾经的历史背后的问题和教训。
俄新社驻华记者2006年的一篇报道中曾如此写道,“那些注定要发生的事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在中国,也许会以某种缓和的形式得到解决,也许相反。作为邻国,我们有必要对任何一种可能的方案都做好应对准备。”
我们准备好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