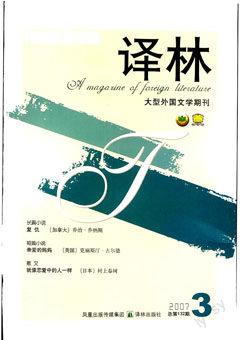复仇的困惑
赵丽萍 唐克胜
加拿大记者、诗人、编剧兼专栏作家乔治·乔纳斯的《复仇:一支以色列反恐突击队的真实故事》,据说是根据一位以色列前特工“阿弗纳”的叙述写成的。小说出版后,以色列政府断然否认小说的真实性,称阿弗纳并非突击队队长,说这本书实际上是根据某组织成员的异想天开编撰而成的。不过,乔纳斯说,1981年夏天,他的出版商要他去见一个人,说那个人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要告诉他。经过一系列精心安排,他们在北美的一个城市见面了。在一间小办公室里,他见到了那个人。那个人向他讲述了以色列反恐战争中一次重大而有趣的事件,那就是1972年十一名以色列运动员在慕尼黑被杀之后以色列迅速组建的一支反恐突击队的活动。
在随后的几年中,乔纳斯亲临欧洲和中东考察,并在当时被称为“铁幕”下的两个城市里待了一段时间。他跟那个人频频在世界各地见面,并在后者的指引下,先后采访了六个人。同时他还采访了很多专家、官员和其他有关人员。经过对暗杀现场的实地考察和一系列采访之后,乔纳斯认为那个人的故事大体是真实的。至于那个人为什么愿意把这段经历讲出来,乔纳斯猜测,一半是为了钱,一半是为了重温往日的兴奋与刺激。
在2005年版的《复仇》中有那个人,即“阿弗纳”写的一个前言。前言中没有刻意去证明他的故事的真实性(好像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倒是目前越来越猖獗的恐怖活动,让他十分忧虑。他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自己执行的那次任务。他说:恐怖分子溜进奥运村离现在已经有三十三年多了。他们在那里制造了慕尼黑惨案,杀死了十一名参加1972年奥运会的无辜的以色列运动员。他还说,在惨案之后的几十年中,他经常反思以色列当时让他和另外四个人去欧洲寻找并暗杀据说策划了这次惨案的十一个恐怖分子的做法是否正确。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就像那次任务一样,非常难以回答。
无论“阿弗纳”的故事真实与否,都不影响它成为一个精彩的复仇故事。尤其是故事中展示的复仇者们的困惑,更是值得人们深思。在人类历史的悠悠长卷上,复仇曾普遍并且长期存在。尽管在当今社会复仇已经受到国家法律的禁止,但以复仇为主题的故事仍一如既往地让今日的人们深深感动,如古希腊的《安提格涅》、《赫库帕》,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以及近代的《基督山伯爵》等等。在中国,复仇甚至是受传统道德伦理认同的。有仇不报非君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血债要用血来还,诸如此类的成语、谚语不仅记录在我们的词典中,也流淌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液里。无论在西方文化中还是在东方文化中,复仇者曾经都是与英雄画等号的。而在《复仇》中,复仇的目的和意义却遭到了复仇者们的质疑,他们在杀死一个又一个恐怖分子之后,不仅没有感到胜利的喜悦,更没有为国效力的神圣感,而是莫名的恐惧以及久久挥之不去的困惑。正是这种困惑,使复仇者们不是走向了毁灭,就是变得惶惶不可终日。
故事由两条线索组成:一条是突击队的复仇行动。1972年9月5日,八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潜入慕尼黑奥运村,杀害了两名以色列运动员,并抓获另外九名作为人质。在随后的解救行动中,九名人质全部被恐怖分子杀害。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戈尔达·梅尔随即命令特工组织“穆萨德”实施报复。于是,一支由五名特工组成的突击队成立了。一场血腥事件刚刚结束,另一场杀戮就要开始。以色列政府要向巴勒斯坦人实施报复。突击队的任务就是暗杀以色列政府确定的与慕尼黑惨案有关的十一名恐怖分子。任务结束时,突击队干掉了名单上的五个恐怖头子,与其他突击队联手干掉了另外三个。剩下的三个人,一个自然死亡,两个被暗杀。被暗杀的两个人,是否为“穆萨德”所为不得而知。
另一条线索是特工们在复仇过程中所经历的心理上的变化过程。具体地说,就是他们在从一个追杀恐怖分子的刺客到变成一个被恐怖分子追杀的目标的过程中,从光荣领命到徘徊迷惘直至走向毁灭的心理变化过程。小说除了人木三分地描写了复仇者们杀人时的残酷、冷漠和精确之外,还真实地、细致入微地记录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倒下去之后在他们心理上的反应。尤其是主人公阿弗纳的心理活动,犹如一条在巨浪中颠簸的小船,此起彼伏,贯穿故事始终:恐怖主义固然可恨,但以暴易暴(所谓的“反恐”)、“以牙还牙”是否是解决问题的惟一方法?以生命换取生命是消弭了失去所带来的伤痛,还是只能加深业已存在的裂痕?生存的权利,是否因为种族的分野就变得模糊不清,甚至不再重要?犹太人被屠杀灭绝的历史,是否可以被当作犹太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道德资源?阿弗纳是奉命追杀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刺客,到头来却变成了被恐怖分子追杀的目标。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质疑。但国家的召唤又不能弃之不顾,国家的使命也不能不服从。他为此感到困惑。《复仇》想要表达的,或者说,要引起人们思索的,也许就是这样一种困惑。
关于巴以冲突这一世纪难题的起因,我们从各种报道中已经熟知。他们之间“以牙还牙”的事实,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比如,就在前不久,以色列南部海滨城市埃拉特发生一起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的四人死亡。但关于这些暴力事件参与者的心理活动,却很少有人涉及。《复仇》无疑给了我们一次走进他们内心世界的机会。
毫无疑问,阿弗纳是怀着复仇的正义感和对国家的使命感接受这次不寻常的任务的。他从部队服役归来后,希望能在以色列航空公司找一份工作。即使做不了飞行员,当一名空勤人员也行。因为这样他就能四处旅行。说不定还能碰上已成为飞行员的战友呢,说不定碰上之后,战友还会载着自己在机场上空转一圈呢!他太喜欢旅行了。正在等待航空公司的答复时,他收到了以色列特工组织“穆萨德”的一封信。尽管当过特工、对特工的艰苦生活和特工组织滥用年轻特工爱国热情的黑暗现象深有体会的父亲一再阻挠,阿弗纳还是加入了特工组织。梦想终于变成现实。阿弗纳当上了一名空中警官,负责保护飞机乘客的安全。虽然未能做一个飞行员,但总算能飞了。飞机不只是在机场上空转圈,而是飞到了世界各地。仅仅几个月之内,阿弗纳就飞遍了全世界,而且自己没花一分钱。他甚至有幸给以色列总理当过一两次保镖。阿弗纳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对自己的家庭生活也非常满意。他刚刚结婚。妻子是个漂亮的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关于他的工作,虽然他什么也没说,但妻子理解他、支持他。
自从后来见到梅尔总理之后,阿弗纳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无忧无虑的生活结束了。“穆萨德”令他率领一支突击队,干掉他们确定的十一名恐怖分子,为在慕尼黑奥运会上死去的以色列运动员报仇。这是一项,用梅尔总理的话来说,“改变犹太人历史”的重任。他经过二十四小时的考虑之后,终于答应退出“穆萨德”,并承诺自己今后的所作所为跟“穆萨德”无关,一切后果由自己承担。为了
国仇家恨,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这条远离亲人、无法告人、无法诉说、孤独寂寞的不归之路。旅行对他来说不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次次惊心动魄、心惊肉跳的追杀。
复仇者们出师大捷,并为此深受鼓舞。他们在门廊里把一个手无寸铁的目标干掉之后,又接二连三地用电话炸弹、汽车炸弹、在床垫下放炸弹和街头突袭的方法残忍地干掉了另外四个恐怖分子。
随着恐怖分子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复仇者们开始感到惶恐不安。用阿弗纳自己的话来说,这种感觉很奇特,以前从来没有过。在部队里没有、在“六日战争”期间没有、训练的时候没有、做一名普通特工的时候也没有,甚至在执行这次任务之初也没有。它是一种“悄然存在、让人萎靡、几天都挥之不去的焦虑”。他起初以为是吃了什么东西所致,但他很快发现,这种感觉是恐惧。他意识到,要杀掉一个人太容易了。只要有几个人,有一点点钱,一点点决心,就可以找到一个人把他杀了。难怪恐怖分子那么容易得逞的!既然他们能这样毫不费力地把恐怖分子干掉,那恐怖分子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他们干掉。他们能买到恐怖分子的情报,为什么同样有钱、顾及更少的恐怖分子买不到他们的情报?他们随时可能在街道的拐角处看见一支枪,正对着自己。晚上熄灯以后,他们的床也可能被炸到天花板上去。复仇者们惶恐了,不安了。当搜查毒品的德国警察将他们团团围住时,他们几乎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了。当一个黑人小孩不慎把球扔进他们的窗户里时,他们“立即趴在地上,双臂抱头,等着那颗手榴弹爆炸”。当邮递员来检查丢失的邮件时,他们赶紧在卧室门后做好埋伏,以防不测。阿弗纳在床上再也睡不着觉,只有搬到壁橱里才能睡着,因为他时刻担心有人在床底下放炸弹。
他跟妻子的团聚也不全是欢乐。考虑到任务结束后,自己再也不可能回以色列生活,他动员妻子到美国生活。妻子从来没有在以色列以外生活过。她孑然一身地住在美国,人地生疏,举目无亲,不知道阿弗纳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他第一次回美国时,看到妻子孤独脆弱的身影,心里痛苦极了。他不知道这种频频更换姓名与身份、跟哪怕是自己的亲人都无法诉说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而在他妻子的眼里呢,他在过去的七个月中好像老了十岁。虽然实际只有二十六岁,而看起来却像三十四五岁的人了。他自言自语地说:“看来你愚弄得了你的脑子。可你愚弄不了你的身体。”
仿佛阴魂一般不散的惶恐与不安让阿弗纳开始对这次任务的正义性感到困惑,对这样的报复行动能否消灭恐怖活动提出了质疑。事实证明,他们的困惑和质疑并不是毫无根据的。阿弗纳在伦敦大街上被恐怖分子跟踪了。紧接着,三个特工一个接一个地被恐怖分子杀害了。第一个特工死在恐怖分子雇来的女人设下的温柔陷阱里。第二个特工在研制新式弹药时被神秘地炸死。第三个特工在冰天雪地的深夜里散步时遭人暗算。阿弗纳虽然感到震惊、愤怒,但在强大的、无形的恐怖势力面前,却又无可奈何。连是谁杀害了自己的同伴都不得而知,更别提报复了。阿弗纳更加困惑了,既对同伴们神秘的死亡感到困惑,也对这种循环往复、无休无止的复仇怪圈感到困惑。正是这种困惑,坚定了他后来离开特工组织和选择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的决心,从而完成了人性的自我救赎。
表面上,三个特工是被恐怖分子杀害的。但实际上,杀害他们的恰恰是这种困惑。随着暗杀行动的连连得手,特工们变得神情恍惚,举止古怪,神秘莫测。看着一个个生命倒下去,他们变得越来越沉默、惶恐与不安。他们心灰意冷,疑心越来越重。他们随身带着枪,充满了杀气。这种困惑无法与外人言说,不能向家人倾诉,害怕与同伴沟通。孤独像一张巨大的、无形的网把他们紧紧笼罩。他们变得孤僻、厌世、迷惘,甚至绝望,于是企图从女人身上、从工作当中、从全神贯注的思索之中得到一丝慰藉,结果却为恐怖分子所害。小说自始至终都没有交代三个特工到底是谁杀死的,不仅没有交代,还大肆渲染,故布疑阵。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特工们正是死于这种困惑呢?困惑久悬不决必成困境。特工们走不出困境,只有走向毁灭。
拜伦说:复仇是一盘菜,最好等冷却之后再来吃。复仇也许是一盘菜,但得有失去人性和灵魂的冷血杀手才行。否则,即使冷下来的菜也吃不下去。《复仇》中的特工们都是有血有肉的热血男儿,他们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家人。于是,死亡似乎是他们的惟一选择。
没有走向毁灭但已心如死灰的阿弗纳最终离开以色列去了纽约。他不能找工作,因为他不是美国的正式移民。他跟那些从墨西哥来的非法移民一样,成了美国庞大的地下经济中成千上万的从事低级工作的外国人中的一员。但他不认为这是剥削。相反,他心存感激。他不介意开出租车或刷房子得到的钱比正式移民少,也不介意工作时间比他们长。正是在开出租车或刷房子的时候,他慢慢意识到,这些是他可以干一辈子的活。
每次看见父亲坐在折叠躺椅上,半睡半醒地梦想着红宝石,等待电话铃响的时候,阿弗纳就庆幸自己终于走出了复仇的怪圈。这种觉醒来自于他对复仇行动的作用和意义有了比较透彻的了悟,来自于他对人生不可摆脱的荒谬的认识。他认识到,复仇根本不能最终消灭恐怖分子,也无法消灭世界上的恐怖活动。一个恐怖分子倒下去了,另一个恐怖分子又会像指甲那样很快长出来。当笼罩在神圣的国家使命上的面纱被撕下来以后,现实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用暴力来遏止暴力是完全不现实的,它除了能引发新一轮的更加猖狂的恐怖活动之外,还把复仇者摆到了与恐怖分子同样残忍的位置上,跟恐怖分子变成一丘之貉。随着现实本来面目的逐渐显露,复仇者内心的动力渐渐消弭了。
《复仇》无疑是一场悲剧。正如其他悲剧一样,它解决不了现实的生存困境,只能暴露残酷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它是悲剧创作者情感的表达,同时也以“同情”的方式引发接受者情感的表达。这种表达是情绪的宣泄与净化,也是对处于悲剧困境中所显示出来的生命力量的哲学思考。在这场“有价值的东西被撕毁”的悲剧中,毁灭的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应唤起我们对人之所以为人的理由和尊严的重新审视,对生命以及生存之本质的理性思考。
(赵丽萍:河北张家口教育学院中文系,邮编:075000唐克胜: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邮编:518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