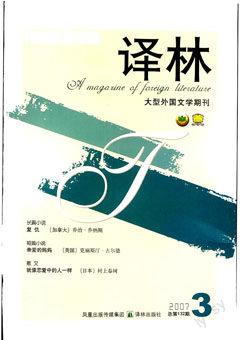旋转的万花筒
早在1991年,生活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英国作家尼尔·盖曼(1960—)就以其奇幻系列小说《睡魔》中的《仲夏夜之梦》收获了世界奇幻奖,之后推出的《乌有乡》、《好兆头》、《星尘》等作品,无一例外地成为欧美幻想小说读者追捧的对象。进入21世纪,尼尔·盖曼风头更劲,《美国众神》、《卡罗兰》、《绿字的研究》(载于《译林》2006年第6期)接连获得欧美畅销小说领域的各类重要奖项。特别是20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美国众神》,不仅在当年拿下欧美最具影响力的恐怖文学大奖布拉姆·斯托克奖,次年更是包揽世界幻想文学领域两大最高奖:星云奖和雨果奖。最有意思的是,这部小说同时得到了来自主流文学界异乎寻常的好评,情形类似1969年冯尼古特推出《五号屠场》后,主流批评家们竞相刮目,很快用黑色幽默作家的牌子替换了原来的科幻小说作家标签。现在,尼尔·盖曼也凭《美国众神》技惊四座,为自己赢得“后现代实验作家”的称号,成为美国文坛上醒目的新一代明星作家。他在接受采访时毫不掩饰地对记者说,“这部书让我十分骄傲。”
这部受到广泛欢迎的小说像一架结构诡异、内容庞杂、镜像离奇的“万花筒”。作品内部世界的光怪陆离让人心醉神迷,作家转动万花筒的手法——尼尔·盖曼写作时采取的叙述姿态——也颇令人玩味。
故事以名叫影子的主人公刑满出狱为起点,沿主人公出狱后的行动轨迹铺设情节主线。影子在监牢中苦熬三年,惟一的企盼是出狱后能和妻子劳拉共同开创新生活。然而他刚刚获得自由,就被告知劳拉在一起车祸中亡故,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妻子劳拉在他服刑期间曾与他最好的朋友私通。突如其来的情感真空使影子陷入恍惚迷离的状态中,完全不能融入现实人生。他只能确定自己“不应该干什么”,但在“应该干什么”上却懵懵懂懂,随波逐流。因此,当一个名叫星期三的古怪老头子主动找上门来,给他提供一个听差兼司机的工作时,他迟疑了没多久就接受了。
星期三其实是公元9世纪时随维京探险者一同来到美国的挪威古神奥丁。像他这样被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带到美国的古老神灵还有很多。盖曼在故事中设定神与人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控制”的关系,神灵依赖于人类的信仰而存在,被信徒遗忘,就会渐渐失去活力,直至死亡,而一旦人类在生活中产生新的依赖对象,便会对应出现一尊新的神。在“江山代有新神出”的背景下,流落到美国的古神们信徒日少、香火难继、度日维艰。为了重振雄风,星期三准备策动一场新旧神灵之间的战争,打垮信用卡之神、高科技之神、媒体之神等新生代神祗。而雇用影子,正是星期三计划中的重要一环。
我们看到,尼尔·盖曼抛出两个悬念来吸引读者。其一是影子能否找回缺失的心灵?其二是星期三的如意算盘能否实现?随着影子坐上星期三的汽车,读者带着这两个悬念,将目光集中在影子这个焦点人物身上,开始了与神共舞的公路之旅。《美国众神》的万花筒旋转起来了。
情节行进的线索非常清晰,走的是“公路小说”的路子,按主人公的足迹和所见所闻安排生活场景。这种移步换景的叙述模式早在16世纪西班牙“流浪汉小说”时期就趋于成熟。当然,穿行在美国州际公路上的汽车速度更快,场景变换自然可以显得更加突兀和新奇。“垮掉的一代”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是美国公路小说的典范,书中人物那种“在公路上狂奔,不知下一站在何处”的迷乱情状,把失落自我的人在找寻自我时的疯狂与骚动表现得入木三分。尼尔·盖曼现成套用“在路上”这个意象来写影子,毫不费力地突显出主人公漂泊无依,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困惑和痛苦。另一方面,用这种随时问和空间变化而快节奏转换场景的情节推进方法,也更容易将零碎繁杂的人物和事件串连起来。
单凭这种传统结构方式,当然显不出尼尔·盖曼的写作智慧。读者会发现,由“公路之旅”串连起来的只是小说中的“前台”世界——美国的城镇乡村,神灵们在这个世界里基本上与常人无异,像《红楼梦》中的跛足道人闯入红尘,最多只能施展一些小魔法。另有一个“后台”世界——由神灵们幻化而出,像《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由于超越时空,因此无法清楚地串在时空线索上。从阅读的角度说,理解后台世界,才能对各种角色在前台世界的行动和命运认识得更深入。比如《红楼梦》,如果没有“太虚幻境”这个后台世界为小说中人物的活动提供依据,那我们看到的前台“贾府”发生的种种细节就会变成一盘散沙,所有的恩恩怨怨和家长里短也就成了偶发的琐屑事件,难以聚为一体。按这个道理,我们不妨把《美国众神》的后台世界看成万花筒的筒柱,而把前台世界看成筒中的花,如果筒柱塑不成形,筒中的花就只可能是一堆零碎。
作家以三种方式刻画小说中的后台世界。第一种与情节主线联系紧密,是奇幻小说中常见的可以增加读者阅读新奇感的转换方法:人物从某个时空奇点突然从前台转入后台,比如小说中影子坐上“旋转木马”和将汽车开下路基等处,与哈里·波特推着行李车冲向火车站台的墙壁一样。
第二种是“贾宝玉梦遇警幻仙姑”式,通过对主人公梦境的描绘,暗示其后的情节演进。尼尔·盖曼对影子的梦精雕细镂,不吝笔墨,更内在的原因在于:睡梦中的影子才真正拥有“自我”,拥有火热的内心情感,而前台现实人生中的影子则像他自己的名字一样麻木不仁、空洞模糊。这是一个“在醒来时死去,在睡梦中复活”的双面人。怎样从这个怪圈中挣脱而出,是主人公找回自我的关键。在这里,后台梦境与前台人生形成一种互动关系,一个接一个的梦不断推动影子在现实人生中振作起来,迷雾重重的现实又催促影子到梦中去揭露真相。最后使影子获得救赎的也是一个梦,被钉在树上三天的死亡之梦。这个梦完成了他的人格回归。尼尔·盖曼通过对后台梦境的铺陈,成功地深入主人公的内心,使故事中最不易处理的性格转变难题迎刃而解,水到渠成。
第三种方式完全脱离情节主线,以“来到美国”的黑体字与主人公“在路上”的故事隔开,用后现代写作常见的拼贴方式问杂点缀于文本之中,这部分内容记叙世界各地的古神们最初来到美国的经历。有意思的是,尼尔·盖曼找了个替身——埃及冥界之神艾比斯——来充当“来到美国”部分的叙述者。叙述者的变化导致了叙述姿态的变化,如同换一只手来旋转万花筒。艾比斯笔下记录的是各地古神刚到美国时受人爱戴的甜蜜岁月,颇有几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感伤情调。每到这个部分,文本叙述者的声音就从急速的公路快板转入“追忆逝水年华”的抒情慢板,既起到了调整叙事节奏、变换阅读趣味的作用,也使后台世界显得更加生动清晰,富有层次。
尼尔·盖曼采用拼贴方法处理文本的时候十分随意,不受拘束。除了若干“来到美国”的章节,他还用了少许“美国某处”、“穿插事件”等黑体字作拼贴标记,以电影镜头式的叙述姿态映现出一些游离于主线之外的蒙太奇场景,犹如万花筒中突然分离出一小块不守规矩的碎片,略略调动一下你的目光之后,又不动声色地将你的注意力转射到主人公影子这个焦点上去。
有一个现象比较有趣:喜欢《美国众神》的读者相互间不太容易找到共同语言。这似乎也是一种“万花筒效应”,说明不同的读者迷恋的镜像不同。有的喜欢小说中颠覆神祗的喜剧场景,看到穷困潦倒的神灵们靠吃馊饭陈菜度日就忍俊不禁;有的喜欢小说中奇异场景的描写,对人神同性恋、解剖女尸等细节处的花样翻新赞不绝口;有的单喜欢湖畔镇谋杀案,还有的只喜欢骗子讲的小故事。对于为什么这部书受到主流文学界的青睐,也是见仁见智,有的认为小说视野宏阔,写出了当代美国精神;有的认为小说充分体现了后现代文学创作的特点,成功地破坏了叙述常规,运用了拼接、戏仿等标志性的后现代创作手法;有的认为美国众神的象征意义很深刻,提出了全球文化怎样融合并存的严肃命题。应该说,上述各种阅读偏好和读后评议都有道理,都能从《美国众神》中找到充足的依据。当然,这种现象本身说明:《美国众神》的确令大多数观众眼花缭乱。尼尔·盖曼,正像他笔下塑造的爱变硬币戏法的主人公一样,用指东打西的魔术手法转动这架万花筒,成功地演讲了一次“庄严的谎言”。
(郭卫文: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阿坝师专中文系,邮编:62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