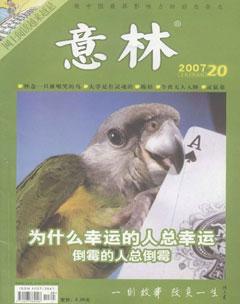跪娃
黄方国
跪娃3岁起就没有了小腿和脚,走路完全用膝盖。跪娃7岁那年,父母相继去世,从此跟了哥嫂过日子。哥嫂都嫌他。他的日子过得就越发艰难。那么小的年纪,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煮早饭,割猪草,煮猪食。稍有差错,嫂嫂就打他,哥哥也帮着骂。但打得再狠,他都不哭。春去春来,花开花落,他始终一歪一歪地忙碌在这个小小的村子里,对任何人都是一副仰视和讨好的模样,只要有人给他点吃的。或者说几句同情的话。他便感激得伏在地上磕头。
跪娃经常瞒着哥嫂,把割的猪草悄悄地倒在人家的街阴下,知道实情的人若夸他几句。他便直起背着背篼的腰杆讨好地仰望着对方笑,笑得别人的鼻根和眼眶一阵阵地酸涩。
我初次见到跪娃是个雪后的上午。他背着猪草靠在教室的窗子下面,稚气的脸冻得通红,扣不住的烂棉袄外面捆了一根长长的草绳,每个膝盖上都系着一只塑料鞋底,裤角上布满泥点。跪娃很矮,窗子很高,他忘神地跟着教室里的学生念着课文,连我走到面前都不知道。我蹲下身子问他:“这么冷的天。你在这里干什么?”他顿时全身紧张,也不说话,一歪一歪地从我身边走开了。刚好下课,涌出校门的学生们追过去,七手八脚地往他身上扔东西,边扔边喊:“跪娃跪娃,活着活受罪。干脆死了吧!”跪娃没有回头,任凭那些纸团从头上不断落下,一歪一歪地在泥水四溅的地上走得更快,连猪草也撒了出来。我大声地叫住学生,命令带头的学生把猪草给他捡进背篼里。
我进教室拿了一本语文书给他,说:“你来读书吧!我给你垫学费!”跪娃抬头,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我,在证实我不是戏弄他以后,他接过书,突然全身扑在地上,朝我磕了三个响头。我去拉他,他始终不起来。一阵雪风吹过,跪娃的头发乱飞,我的泪一下流了出来。
跪娃想给我送点烟感恩,但他没有钱。那天下午他哥嫂不在,他割了好几背篼猪草,反复地倒给院子的一个老人。老人询问究竟,他低着头不做声,问急了,他看着晾在老人屋边还没有干的叶子烟不转眼。老人明白他是要烟,就叫他自己扯,跪娃马上跪在地上磕头……
跪娃晚上来到我寝室。从怀里拿出那把叶子烟。放在我面前,然后仰起头,笑容满面地看我,好久都不说话。
那天晚上,我把他留在我那里住了一夜。跪娃说:“老师,我的爸爸妈妈是好人,你也是好人!”跪娃说:“我想读书。我爸爸妈妈说,只要我读书了,就算我这个样子,也会有出息。”跪娃最后说+“等我有了出息,我就报答对我好的人,给他们买最好吃的东西,给他们买最好的衣服。”灯光摇曳,照着他的脸,照着他的天真,也照着他掩藏不住的幸福。
次日一早,我去找他的哥嫂,他们找着借口不同意。晚上又去,他们还是不同意。我走出他的家时,看见躲在窗子下偷听的跪娃难过地低下了头。第三天,我看见跪娃背着背篼远远地站在学校对面的土堆上朝学校这边望,一望就是半个小时,只要一看见我他就躲了。过一会儿。又看见他站在土堆上朝这边张望。
下午,我叫上村长一起去找他哥嫂,他们不表态,让我问跪娃。跪娃进来。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不敢说话。我鼓励他说实话,于是他跪到哥嫂面前,磕了几个响头,大声说:“哥哥嫂嫂,我要读书!读书以后我干活一定比以前更卖力气!”嫂嫂顿了好久才说:“好吧,你要读就让你读好了!”走出门,跪娃拉着我的手。仰头看我,看了一遍又看一遍,看了几遍,叫了一声“老师”。泪水飞溅,低头不再做声。
傍晚,一个学生来叫我。说跪娃不见了。
院子里有人告诉我,说我们一走,跪娃的哥嫂就开始打他,撕他的书。跪娃挨打是常事,但他们从没听过他如此伤心绝望的哭泣。我一个激灵,说到他父母的坟前去找。
那天的月亮很圆很明,但挂在天上有种说不出的空寂,清冷的光芒照着跪娃父母的坟头,高高的蒿草不断地飘摇。跪娃果然倒在坟前,可他撞坟死了。还是那身打扮,头靠在坟头上。从额上流出的鲜血一直流到他放在身下的左手上,手上依然紧握着那本语文课本,只是书已经被撕得残缺不全了。我泪眼朦胧地抬头看月,一阵冷风拼命卷起来,吹起他的头发,吹起他的衣领,吹起破碎的书页,一直吹进我的心里……
云舒摘自《幸福生活》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