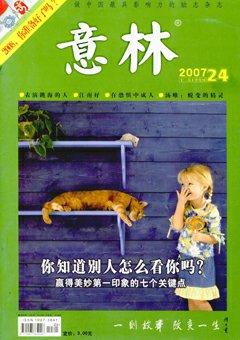漫天飞雪般的纸钱
和洪范
儿子被执行死刑的通知,是清早收到的。
母亲和父亲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好觉。不是他们提前接到了类似于口头通知之类的什么信息,而是出于一种预感。准确地说,是内心深处倏然而起的一种震耳欲聋的战栗。那战栗,在女人心里闪电一样掠过的时候,击中的目标不仅仅是自己,还有自己的男人。
“他妈……他妈……”断断续续的语音与节奏里,霹雳着令人心悸的雷鸣,刺人眼瞳的闪电,惊冽冽地终于没有把完整的话说出来。女人用眼角笑笑,笑得让男人不可理解,瞠目结舌。但是他觉得她那笑里,涔涔地流着鲜血。只有他知道,那血,是从她身上流到儿子身上,又从儿子身上回流到她身上,然后不容她选择地从她眼角流出来的鲜血。
“我出去一下,就回来……”女人说。
男人说:“你去,你去……”
女人没有说自己出去做什么。
男人也没有问她出去做什么。
女人真的出去一下,就又回来了。她抱回来几领白纸。
男人很着急的样子,终于没有着急起来。他看着她不看她的眼睛,诘问中透出一种黑白分明的理性坚定。但是仍然以小声征询的口气对女人说,他值吗?他值得你为他烧钱落纸吗?女人一声不吭。一声不吭是具有绝对性质的认定,同时具有包纳天地人间的时空。她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一样,把纸放在小饭桌上,又去拿剪刀,又去找多年不用的针线箩筐。
女人很沉静,凑着发黄的15瓦电灯泡,坐在小饭桌旁专心致志地做纸钱。她先把一张张白纸用手抚平。本来那些刚买来的白纸就是很平展的,她以为还有必要再次被抚平一下的时候,就显示出她对自己将要进行的作业格外慎重。这是一种古老文化沉淀在人心里的仪式,礼仪之邦的后人,对一种不可逆转的事实进行奠祭的时候,那种成为痛苦的沉重,就会在未来时空里被减轻重量,充满柳暗花明的希望。
母亲在为儿子做纸钱的现实过程中,心理上是黯淡而痛苦的。然而之于心理上的未来时空,却是想怎么美好就怎么美好的希望,以至于她感到的那种月朗风清。人的生命现象是妙味无穷的,只要能把一种铁定无疑的结论赋予人在欲望上走向美好的变数,那种痛苦造成的沉重就会被减轻许多重量。她读过初中,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原本不相信人有什么来生,但是,在她的儿子一定会被处以死刑的事实面前,她突然盼望儿子以至于所有人都有再次投胎转世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她心头一闪的时候,也就是她预感到儿子明天会被执行死刑的那一个瞬间,她就千真万确地相信了人们为什么会说人有前生与来世。
儿子无疑是把今生活错了,活得大错特错了,错得必须让他离开人世,结束今生。生离死别是一种物极必反,不允许他继续在今生活下去的时候,就会让嫡亲的亲人看到他生命将重新开始的希望。的确,她甚至盼望儿子的死讯快一点到来,快一点到来的时候,也就是儿子生命轮回里再一次新的开始。为了祈望那个新的开始,她以无限的虔诚在做纸钱。做纸钱前,她洗了几遍手,几次脸,她没有去记,也无须她用心去记。干干净净是对无所不在的神祇的虔诚和尊敬,哪怕些许的纤毫尘埃,她也怕影响儿子未来本该转运的契机。
她手中的剪刀先是剪很圆的弧线,圆到不用圆规,而能达到使用圆规的效果。然后她在圆里套着剪菱形的花瓣,椭圆的花瓣,丝丝缕缕的花瓣,各式各样的花瓣。剪着剪着,她仿佛闻到了淡淡的花香,越来越浓的花香。不是一种两种三种花香,而是百种千种万种花香。她在纸钱里剪遍自己所认识的花,似乎少剪一种,就会影响到儿子来世的命运。她觉得还要在纸钱里剪一些“卐”字,“卐”字在线条曲折弯转的过程中,那种由下到上由上到下的走向,一如人生艰辛跋涉里的命运。人在幸运与背运的轮回里才能活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于是,运在否极处的人意味着运在吉泰上的转机。儿子年纪轻轻就把做人的命运活到不能再低的低处,虔诚地为儿子祝福,来生一定是蒸蒸日上,阳光明媚。鸡叫第一遍的时候,她就把纸钱剪好了。鸡叫第二遍的时候,她似乎还没有做完所有的工作。鸡叫第三遍的时候,她装好了纸钱,静静地在等。还没有听到村治安委员的脚步声,她就轻轻地开了屋门、院门。
她淹没在人声鼎沸的县人民广场,高音喇叭里的一切声响,都涉及她的儿子。
高音喇叭里最后说的是“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八个字。“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的回声还在广场内外回荡的时候,警车一起哇哇叫了起来,引擎声响成一片。
她在潮水一样涌动的人群里,拼命挤到刑车旁,一声声呼叫着儿子的名字。一把把雪白的纸钱抛向空中,漫天大雪一样纷纷扬扬落向万头攒动的人群。
“老天爷呀,行行好,叫我儿来世做好人!”
“老天爷呀,行行好,叫我儿来世做好人!“
她跟着刑车跑,旁若无人地跑,把一个女人的三个身份:女儿、妻子、母亲,跑得仅仅剩下一个母亲。她一把把把纸钱撒向浩渺的空中,漫天大雪一样飘飞的纸钱,千姿百态里是她千言万语的祈望。鞋跑掉了一只,她光着一只脚,头发跑散了,胡乱地遮着她的面颊,她已经不需要属于自己的脸。
“老天爷呀,行行好……”
“……行行好,行行好……”
“行行好,行行好”里,满口白沫的她,一头栽到地上。
她的声音喑哑了,已经没有了任何分贝。但是,翕动的惨白双唇,依然很好地保持着“行行好,行行好”的口形。一片雪似的纸钱,飘飘荡荡地老也落不下来。终于落下来的时候,竟然落在属于她心的那个地方……
(薛小玲摘自大河论坛图/陈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