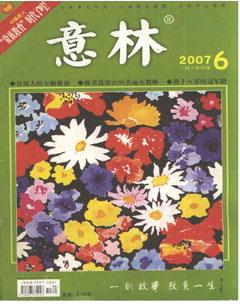一辈子的浪漫
吴淡如
有个作家,在旅游时有过一次自认为“大概非死不可”的体验,他说在他快要失去知觉的时候,他脑海里浮现的不是父母妻子,而是没写完的故事。
不了解创作者艺术特质的人,听起来好像很无情无义。
创作者大概都能体会其中的意义。凡是人,便不难找出一条生路,但那没写完的稿子,能倚靠的只有写出他的那个人。
他是个好父亲好丈夫好儿子,然而他在濒死剎那,想到的是自己没写完的故事。那一刻他更加确认自己的职志,写作是他惟一想要发光发亮的舞台,他应该淌血尽力才是。
不是每个人都渴望一样的东西。凡是在精神世界上已经找到方向,总想活得有目标的“狂热分子”,都喜欢求仁得仁。
对他们而言,最美丽的死亡,应该在他们最热衷的舞台上降临,让他们得以终生奉献,谱出最后一个炙热的休止符。
仿佛是命运的巧合,在阿尔卑斯山发现了冰封了五千多年的冰人欧兹的德国登山家赛门,六十七岁时回到了发现冰人的阿尔卑斯山山区,只身攀爬超过两千米的高山,失去了音讯,后来有人在顶峰附近的山沟发现他的遗体,那个地点就在他发现冰人、因而扬名世界的山区附近,所以当地的山友盛传,他故意在此走完生命的终点。只有如此,才能死而无憾。
要不,年纪那么大了,为什么还要挑战危险的山区,其实在他心里,狂热与死亡,已是同一义。
不是很久以前,全球十大摄影师之一的理查德·艾佛登也在工作中死去。八十一岁的他还在拍照,他说:一天没拍照,就像整天没睡醒一样,连生命的最后片段,他都在为摄影工作。
他在二十多岁时就已成名,此后近六十年,他的朋友说,他用“蜂鸟击翅”一样的精力,从不间断地在拍照,从来不曾厌烦,也不想退休。
米开朗基罗到了八十几岁,临死之前还为手上未完成的雕刻作品费尽心神,希望那座“圣殇像”和以前不一样。
毕加索画了一辈子,在他去世之前,仍不断想着,怎样创新他的艺术,他的心态永远是个好动的孩子,不肯玩重复的游戏。
画家雷诺阿晚年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手指已不能握画笔,他还把笔绑在手上,坚持继续作画。
爱了一辈子,直到最后一刻,那就是真爱了。
并不是所有的人到老了都想含饴弄孙,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安安稳稳死在家中的床上。这些求仁得仁的人,为世界开创了不一样的形貌。
求仁得仁,生命的句点形状依然闪烁如金,在我心中,这才是一辈子的浪漫。
(曹炜明摘自《了解人性的八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