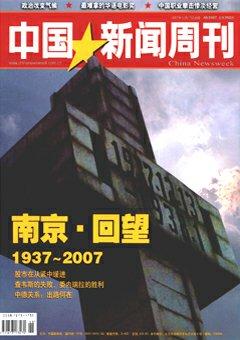南京·回望1937~2007
陈 晓
一个屠城的梦魇,回旋在我们脑际70年;一段数十万人的血泪和屈辱,我们诉说了70年。70年前的梦魇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伤痛又该如何记忆?这是我们问了几十年的问题。
2年前,张纯如英文写作的纪实文学登上《纽约时报》书评排行榜,今年,好莱坞纪录电影《南京》在东西方院线放映;去年年底,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接待了8个西方背景的摄制组。那段被忽略的历史,突然进入了全球视野的历史讲述中。
2007年,中国对南京大屠杀记忆和讲述的接力棒也传到了更年轻的导演手中。
南京,成为2007年艺术关注的一个焦点。它已不仅是只属于中国人的历史。
当我们的历史学家和艺术家不再仅仅把愤怒和屠杀场面作为历史表达的惟一内容时,我们也许才会真正进入这段历史——那段我们与其他经历了战争的国家和民族都共有的历史。

跨越70年的记忆与讲述
2007年,对南京大屠杀记忆和讲述的接力棒传到了新一代导演的手中。他们对这段历史的思考,开始从单纯对灾难场景的控诉,进入更加理性的层面。面对虐杀,我们是否在灾难中表现出了自我拯救的希望?
2007年冬天,天津睦南道的一栋西式小洋房里,电影《南京!南京!》正在拍摄。
这是迄今为止对这段历史最年轻的影像讲述者的创作:主创组的年龄都在20多岁到30多岁之间,而扮演在片中举起屠刀的日本年轻人,年龄也在19岁~35岁之间。70年前,也是一群二十多、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作为大屠杀的主角,扮演了施暴者和受难者的角色。
“我看旧照片发现,被屠杀的人绝大部分特别年轻。屠杀的实施者也都非常年轻,目光凝视对方,只是语言不同,灌输的教育不同,信仰不同,就叩动扳机、挥舞军刀。这两组年轻人,想起来让人不寒而栗。”《南京!南京!》的导演陆川说。
2007年,世界共有7部有关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片投入拍摄。在中国,讲述这段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更年轻导演的手中。而他们开始从对灾难场景的再现和控诉,进入更深层次的追问:这样大规模的虐杀,是战争中的暴行扩大化吗?在灾难中,我们是否表现出了自我拯救的希望?
以史为鉴,我们需要了解的不仅仅是屠杀本身,还有1937年的战争,1937年的中国。
70年前,谁,经历了什么?
2007年12月8日傍晚,《南京!南京!》片场休息,但原因却不一般。
从南京来的一个特约演员,在剧情的感染下,说出自己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剧组正在做她的思想工作,希望她能对着镜头讲出她家女性亲属被日军凌辱的过程。南京研究大屠杀的学者张连红说,目前所知的整个南京遭受过日本性暴力并愿意说出来的女性不过12人。那么,这位老人是第13位。陆川说,这是一个“残忍的惊喜”。
顺着挂着古式西洋闹钟的楼梯,沿着支着安全区值勤记录黑板的楼梯间,穿过裱着西门子公司老照片的客厅,记者见到了这位老人。她穿着淡绿色长棉袍,米色围巾,银灰色的头发盘在脑后,面庞线条优美。她已经收起激动的情绪,准备进入镜头讲述,脸上的表情克制,平静。高圆圆扮演的女教师问她:“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一开始,她缓慢、清晰地说:“昨天晚上,一帮日本兵……”很快,随着语速的加快变成痛哭,后面的话都淹没在哭声里,短短几分钟的讲述,只能分成好几条来拍。
发生了什么?这是我们问了几十年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我们有着不尽相同的叙述版本。
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文部省对送审的高中二三年级历史教科书,要求把描述日本侵略历史的部分予以淡化或删改。随后,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建立。1988年,导演罗冠群在参观完纪念馆后,怀着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愤怒、震惊,拍摄了《屠城血证》,成为当年国内票房十大卖座片之一。1995年,吴子牛看完300万字的史料后,以对30万亡灵的内疚之心,拍摄了《南京大屠杀》,这则消息当年上了日本报纸的社会版头条。
影片把这些血淋淋的历史从文图史料变成了逼真的影像画面,观众真切感受到屠城的过程。
但这并不是那段历史的全部。面对30万人的离去,70年后的我们绝不是只要从中听到哭喊,看到血泪。
因此,在2007年陆川的历史影像中,纵使有“残忍的惊喜”,这位老人和她的家庭的故事也只有短短几分钟。陆川在军队呆过,在他的讲述中,水上、角川、伊田……这些太阳旗下手握军刀的士兵,成为了那段历史的一个重点。“我们在非常认真地拍日本人,非常认真地拍日本士兵。我们所有的日本演员都是从东京请过来的,而且我给他们的戏份都非常重,因为要看到他们在战争中的变化。”陆川说。
普通人还是嗜血士兵?
刚开始聊天的时候,夏村真广(注音)规矩得有些拘谨地坐在酒店的床边,21岁的脸上透着干净,害羞、紧张。因为出演《南京!南京!》中的日本士兵水上,他第一次来中国,也第一次了解南京大屠杀。来中国后的第三天看到剧本,夏村真广大哭,用英语给陆川写一封长信,说他演不了这个角色,说太可怕了,“导演你放我回日本吧……”
夏村真广最终还是扮演了水上,这个他认为“非常可怜,生错时代的年轻人”。他需要在电影中杀人、强奸。对夏村真广来说,这是一条可怕的心灵之路。他以前学服装设计,在日本浅草的一个市场上发现了和服的奥妙和美丽,因此对自己国家传统的优美充满热爱。他还喜欢骑自行车环游日本,去公园的池塘边观察小动物,一看就是3个小时。他说自己不喜欢战争,原因是胆怯,不敢去面对战场上的杀戮。但他也固执,自己相信的东西,不管对错,一定会去做。他讨厌这部分性格。但他所讨厌的这部分自己,成为联结起士兵水上的路径。“我以前写日记,看完剧本后,我把角色和我的日记做比较,发现我和水上有相似之处——会固执地听从上面的命令。虽然不想打仗,但会去慢慢适应战争环境。”夏村真广对本刊说。
一同来到中国的年轻人中泉英雄,也在扮演的角川中,找到了他可以接受角色的普通人的部分:“内向,怕杀人,也怕被人杀。变化是在战争中,最后会崩溃。”
在日本1937年拍摄的的纪录片中,12月13日攻入南京的部队里充满了这样的年轻人:战事未起时,他们彬彬有礼,心中充满着对周围事物的爱和温暖;从军之后,他们慢慢学会服从神授的君权,成为虐杀的野兽。
如何区分开施暴阵营中的士兵和人民?一直是表达这一段历史的难点。不管从中日邦交,还是从哲学意义上的人性,发动战争者和被卷入战争的人民都是不同的两类群体,前者要承担所有的罪恶,后者则要承载战争中的温情和战争结束后重新生活的希望。
吴子牛的《南京大屠杀》拍摄于1995年。是年5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访华,表示要把战后50周年作为日中关系的新的出发点。同年9月,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指出,“要使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吴子牛告诉本刊,在1995年,他把日本人民和嗜杀的日本士兵分得很清楚,因此他将主人公的妻子设计为一位日本人,和她的中国丈夫共同经历了7周梦魇般的屠城,并生下一个叫“南京”的中日混血儿。
但战争的可怕和邪恶之处正是:它让世界上没有人民和士兵这样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人民和士兵是一体的。普通人也会拿起战刀。
《南京!南京!》剧组的日本年轻人需要接受从日本请来的教官的军事训练,陆川要他们找到从普通人到将杀人当做游乐的心灵依据,“你会目睹这些孩子在变化,当他们真的开始喊口号,开始瞪起眼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的那股劲真的是挺不一样的。”
木幡龙在剧中扮演一个“表面自由放肆,但内心很复杂”的日本军官伊田。虽然对“是否相信南京大屠杀”这个问题,木幡龙“不想回答,对不起”,因为他说“在日本国会图书馆中看到了很多完全不同的说法”,但他认可伊田这个角色行事逻辑的真实。在拍摄中,有一段强奸的戏,他甚至自己加戏,给自己设计了更强化“坏”的戏份。陆川说,“我都想不到他会这么演,那是他自己设计的——我既然要演坏人,这样才坏呢。”

什么样的军队和国力的对抗
但,这也不是南京大屠杀的全部。
南京大屠杀是一场军事失败后的衍生品,“如果我拍的日本人还是那种蓄着渣胡子,头脑简单,只剩凶狠的,如果我们真是曾经输给这样一个军队,那才是真正的悲哀。”陆川说。
横山伸治在中国学习电影7年,虽然各种说词不一的资料,让他不确定南京30万人被虐杀是否属实,但他出任了《南京!南京!》的副导演。“如果这部电影还是把日本人的形象从始到终贯穿着愚蠢地残暴,我没有兴趣。”他说。
还原两支军队的形象,就要拨开漫天的血腥,看清1937年的中国和日本。当我们真正做到从细节上去还原这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战争胜败的秘密就清晰地写在军服的质地、设计、颜色,军队的枪支、弹药,甚至一张普通士兵绘制的图纸上。比如1937年的日本军服,专门在腋下设计了一块三角布,让步兵这块特别耐磨。1937年攻入南京时战事刚开始时,士兵的衣服都是呢子的,最后打到1942年穷了,才穿的棉服。
在南京大屠杀的所有回忆中,国民政府是被隐没的一方:他们在南京城留下一个仓皇撤退的背影后,似乎就从这段历史的叙述中消失了。但细节告诉我们,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和国家在抵抗:守城的五支中国部队,除了中央军的军服还比较靠谱之外,从广东四川调来的部队的服装都特别凌乱不堪,服装有四五种颜色,十几种款式。中国军队刚从军阀混战的狼藉里脱身,各路军队的枪支都是不通用的,子弹也都不通用,因为不同的军阀造枪支子弹的工厂都不一样,基本上是不同的生产线。
“这是国力的PK,这仗没法打。”陆川说。
自我救赎的星光
目前的史料显示,在屠城中的中国人,“几乎都是被动的受难者。”罗冠群说,这是他导演《屠城血证》时遇到的一个难题。面对一个如被下了咒语般顺从的屠杀,罗冠群采用了虚构的手法。“这是我国第一部表现南京大屠杀的片子,我必须要正面、全面,既要表现日本士兵的残暴,也要表现中国人民的气节。不然感情上过不去。而综观整个抗日战争历史,我们也是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件。”
因此,在1988年的影像叙述中,南京大屠杀中的中国人是勇于反抗的:照相馆老板14岁的女儿被强奸,小儿子被打死,他用儿子佩玉的碎片扎向日本兵的眼睛。另一个角色“小广东”对日本士兵举起了斧头,男主角展涛在烈火中撞响了巨钟……
1995年,吴子牛再次回望这段历史,他觉得这是一部给后人看的电影,不能“从血腥到血腥,从悲凉到悲凉”,“极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让他在片尾设计了孩子的意向,给影片希望。片中男女主人公带着在战火中出生的中日混血的孩子,逃出死亡之城,上到扬子江上的小船,背景音乐响起“不要哭啊,南京”,“这是唱给孩子的,也唱给城市的,还有下一代,还有希望。这是我片子中惟一的亮色。”吴子牛说。
到了2007年,陆川试图以仿纪录片的形式做一个剧情片。他将影片都洗成了黑白,并且剧中的每个细节都有史料出处。因此,胶片中没有响彻紫金山的豪迈钟声,在真实的屠杀中也没有找到中日友好的民间感情的象征。
“我在看这些史料的过程中,基本上是沉浸在黑暗中,你看到的是虐杀虐杀,强奸强奸,反抗就是集中在紫金山保卫战那段时间。12月13日南京陷落之后,你就发现基本上整城的中国士兵和百姓就顺从地被驱赶着。我甚至看到日本兵有这样的记录,一排20个中国人,把头砍掉,再上来20个中国人,把尸体抬到坑里,跪下,再把头砍掉。杀一下午,没有一个人去跑,没有一个人去闹,当时看到这些,真的是觉得巨郁闷。”
陆川在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员孙宅魏的研究中,看到在一场对四万人的屠杀中,日军有仅亡一两人的记录。上了4年军校的陆川就想:“如果是集体暴动,可能还是会死掉很多人,但是我相信没准能跑掉1000人。四万人暴动,日本人怎么打啊,子弹都穿不过的人墙啊。”
但是沉入历史最黑暗处,也会发现星点的亮光。在对史料进行梳理的时候,陆川逐渐发现了一些让人荡气回肠的救赎:城内7周大屠杀时,中国人惟一一次持枪抵抗的行动,是在几个日本兵抓人枪杀时,正好有几个中国兵藏在墙后面的地下室里,他们开枪打死了那几个日本兵,这在当时造成了全城混乱,传说中央军进城了。
还有一个叫陈瑞方的女子学院的老师在日记里写到,当时安全区的中国男人被以士兵的名义抓起来,日本人要把他们带走枪杀,经过拉贝他们的反复交涉,日本人同意让安全区的妇女来认,是她们的丈夫或者儿子就可以留下。结果有1个女人换了6身衣服,救出了6个男人。
还有魏特琳写在日记里的,日本人来金陵女子师范大学的安全区要妓女,有20个妓女主动站出来跟着他们走了。“这些女的是自己站出来的,她们站出来救了别的女人。但是你想象,这多可怕啊,不是去接客,而是被轮奸。”
这些是中国人救中国人的故事。虽然“真的是凤毛麟角,但是我还是在电影里用了,还是非常希望能写出一些自我拯救的故事。”陆川说。
吴子牛说,拍片子就像播种一样,是要讲节气的。时代不同,同一段历史的面貌也总有不同。
(实习生李楠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