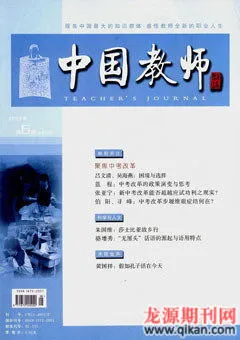中考改革步履维艰症结何在?
中小学生中盛传一首歌谣:“上学真苦恼,书包压弯腰,睡得迟,起得早,功课没完又没了。”“上学真苦恼,书包压弯腰,背起炸药包,我要炸学校!”80多年前,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发出了近代中国的第一声呐喊:救救孩子,把孩子从封建礼教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幸福地度日。80多年后的今天又有专家再次呐喊“救救孩子”,是要把他们从“考试地狱”中解救出来,从沉重的学业负担压力下解救出来。
近年来,我国教育改革浪潮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特别是从2001年正式启动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虽步履蹒跚,但颇有壮怀激烈气概,始终被置之于评判的峰顶浪尖,是各方关注的焦点。目前的现状是,考试越来越盛,负担越来越重,教育再次惨遭“寒冬”,以至怨声载道,民间狂呼“教育打败中国”,社会名流、高官、学者纷纷上书中央进谏,更有科学家力主:课改“立即停止实验”。新课改何去何从?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使考试如此怪异?是谁制造了教育怪圈?必须寻根探源,把握本质,科学判断,勇于突破。
中考改革之困,困在外力
教育需求使考试陷入迷惘。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沸沸扬扬的教育评价与考试改革,使学生、教师和家长的混乱和迷惘愈益严重,与其说是一时性的东西,不如说是本源性、历史性的现象。考试向来就是工具而已,固然考试受着多种相关因素交互影响,承担着太多的社会使命,它可以改变命运,调整社会财富二次分配,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紧密挂钩,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调节器和个人命运的杠杆。社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需要多少,都要通过考试来挑选、检测、分流、反馈。在我国,考试作为朝圣之路,“学而优则仕”堪称考试的政治、伦理、哲学基础,是考试精神的全部,被历朝历代所采用。不论身处社会三教九流的何种阶层,不论自己家境地位如何卑微;只要肯下功夫苦读四书五经,在科举考试中,如果金榜题名就会一步登天。历史上说某位领导好,常誉为“某青天”“某父母官”,当过一点小官的文人墨客,才常常抒情“达则兼善天下”,以救世主自誉。读书做官,自然成为一条朝圣之路。由于这种中国文化的原始积累,当代中国教育也一直在走精英教育这条老路。多年来,这条路一直很窄,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报考人数最终达到570万,录取人数是27,297万人,考试录取比例只有29:1。28年后的今天,这个比例从29比1提高到了到2比1,高等教育已趋大众化,为什么学业、考试还是拼死拼活?随着高考瓶颈的出现,升重点学校的压力一路下移,从幼儿园到大学,最好要念的全是重点学校。
考试问题是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把教育物化为“本本”,把素质物化成“分数”,为什么,高分低能者,报名牌大学能进,考公务员能中?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机关选拔栋梁唯分是从?责任缺失使然。从表面看,教育屈服于考试,素质教育僵局待破,似乎是考试制造了教育怪圈。但说透了,考试只是评价、选拔、分流、反馈的手段而已。无疑,在考试背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发挥着巨大作用。人生来具有趋利性,希望过人上人的生活,严酷的竞争,日益高涨的学历要求和证书标准,何人敢拿着命运开玩笑?首先闯过考试之“坎”,才谈得上展现综合素质。所以,考试不是始作俑者。
僵化呆板的用人标准体制促进考试走向异化。现行政治体制制约人事管理体制,用人制度制约考试选拔制度,考试制度制约教育各个方面的制度。一个文明的制度平台,必然引导人们以能力素质取胜。所以,国家提出政治文明建设。在这个逻辑背景下,我们如何能够背着沉重的行李奔跑更远?怎样带着镣铐把舞蹈跳的更美丽?在诸多改革泡沫破裂后如何抉择?必须锁定考试的永恒视阈,在体制内寻找平衡点。
中考改革之惑,惑在高度压力下核心价值定位不明
教育改革迅速发展,各种追问最后都要归于价值理念上。中考改革中各种争论,质疑、批评,反映出中考的精神和改革所追求的主流价值观。面对争议,我们要思考容易迷失方向的三个问题:一是教育的功能。21世纪的世界日益形成超越国境的、巨型的经济联合体。无论是在本国国内或是世界各国都在实施“规制松绑”和“地方分权化”,国家在教育体制方面的中央集权控制倾向正在减弱,社会经济结构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本源性问题使全社会都在反思:教育是什么?学校干什么?知识有何用?二是评价与考试的精神。考试与评价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应该使学生更爱学习、更有活力、全面发展。评价与考试的背后是选拔标准问题,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什么样的教育,通过相应的考试选拔方式引导和强化这种教育。考试本身永远没有错误,关键是考什么和怎么考,由此不难看出,现今中考方向有待调整。三是问题的实质。随着实践的深入,中考改革面对的矛盾和任务更加复杂和艰巨,现实功利、生存竞争、大众文化对素质教育的冲击等等。但其社会根源只有一个——激烈的生存就业竞争在教育领域的反映。因为在开放性的社会中,个体的社会地位主要由通过教育取得的人力资本决定。特别是社会地位初次配置中,教育是最直接的因素;在教育的多重价值中,配置人的社会地位是其最显在的价值。因为现实的制度设计要求通过考试才能获得更高更好的教育,“教育支配社会地位”就可能异变为“考试支配社会地位”。这正是评价改革面I临的最严峻的考验,这一考验将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存在。
中考改革之难,难在文化重构滞后和变革基础缺失
“文化是制度之母,教育是立国之基”。考试是中国古代的一大发明,西方有学者称其为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中国教育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孔子开创的自由讲学,有教无类,一个是李斯坚持的学在官府,以吏为师。正是通过教育,一个民族找到了他们的共同生存的意义和未来,并体现于每一个个体的行为之中。与此同时,考试一直与政治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无时无刻不被置于道德评判台上。在教育变革中,往往由于其特殊性常常使变革无法正常开展。新中国成立,在重建道统、政统、法统的同时,也开始重建学统。中国的教育几次翻烙饼,从形式上看,已和大清国的时候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但附加在教育上的教化与意识形态传承的功能依然如故,相应的是高度集中、严密控制的教育体制,从每一所学校能否存在、学校领导的选择到招生标准,招生名额、课程设置、教材内容等,都实现计划控制和干预,教育因丧失其独立性而难以按自身规律去发展。目前,望子成龙、乃至逼子成龙的观念,在我国仍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在相当一部分家长心目中,上了大学才是成“龙”,升学成了许多家庭最为迫切的利益,他们更相信“应试教育才能改变命运”。更严重的是,从小学到大学,一种把学生思路圈进预定的狭窄小道,使人精神狭隘并导致智力局限性的倾向贯通在教育的各个环节,导致了教育功能的萎缩和扭曲。素质教育,课程改革,中考改革,都面临着文化重构的考验。强化教育的独立性和育人功能,,发挥考试的检测、分流、反馈作用,重构现代考试文化,是中考改革能否到位的基础工程。
中考改革之失,失在怠于操作层面研究和制度突破
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最大的瓶颈问题,仍是绕不过的评价机制与考试制度。考试并不是最科学的评价,却是当前最为人们认可的评价。考取优质高中越来越成为挂在家长心中的一把尺,是悬在教育者头上的一把剑,能不能以及如何在现有框架内有效地应对考试?能不能以及如何把课改所追求的长远利益与家庭追求的当前利益高度一致起来?中考改革必须解决好“破”与“立”的关系,并进行超越和突破。既重视科学、合理的考试对学生学习状况检测、诊断、反馈和激励的作用,又要防止过多过繁的考试加重学生课业负担和心理负担,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既要理解家庭、社会对应试升学的复杂心态,又要坚决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积极探索建立科学、多元、公正的教育评价体系,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的质量观和正确的成才观,正确处理好学习与评价的关系、全面育人与应试升学的关系,防止和杜绝以分数或升学率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形成有利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有利于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正确导向和工作机制、监控机制。教育部门、学校不能迁就落后的社会心理,而必须站在超越应试功利的高度,站在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发展、促进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高度,始终坚持中考改革的主导价值,进行制度突破,发挥其巨大的优势和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