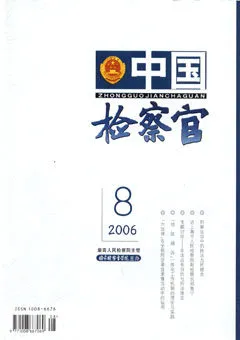和谐社会呼唤现代赦免制度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中,只有宪法、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对赦免制度稍有涉及。我国现行法律对于赦免的施行既无实体规定,也无程序规定,赦免制度已完全被边缘化了。现代赦免制度正具有调节利益冲突、衡平社会关系之重要刑事政策机能。在特定社会政治、经济、社会形势下,适当地运用赦免制度,可以很好地缓解社会矛盾、调节利益冲突,从而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本文拟就如何重构我国的现代赦免制度,从现代赦免制度的类型、程序、法规设置等角度提出我们的初步构想。
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使大赦在宪法中拥有一席之地,并通过专门赦免法对于大赦制度作详细规定,但同时应以周密的程序对其适用给予严格的限制。同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行专门的赦免法,其中应就大赦的范围、效力、程序、法律后果等作出详细的规定,从而规范大赦权的行使。作为现代赦免制度的一种具体形式,大赦具有导致罪刑皆免之效力,它不只是免除刑罚执行,而且使罪和刑都归于消灭。进而言之,凡受大赦的,如果是已受刑的宣告者,宣告归于无效;如果是受到追诉而判决尚未宣告者,追诉权归于无效;如果是在侦查或在提起诉讼中的,应作不予起诉或撤销案件处理,追诉权也归于消灭。如果大赦未附加任何条件,那么在大赦时尚未发现的行为,大赦后不再追究;如果对行为已经提起追诉,有管辖权的法院不得再行受理这种追诉。在考虑是否构成累犯时,因大赦而归于无效的有罪判决不再作为累犯的第一时间限制。当然,由于大赦的效力非常宽泛,因此大赦的施行应遵循一些限制性规定,诸如禁止溯及既往、禁止损及第三人权益、禁止司法机关再行追究等。另外,大赦应由全国人大根据社会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考量,而审慎地针对不特定犯罪人适用,以求保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大赦的适用范围应该有所限定。
在我国应着力发展特赦制度,同时严格规范特赦权的使用,力求形成以特赦为核心的现代赦免制度。首先,特赦是对法律过于僵硬状态的一种补救,是刑事制度运作不可缺少的安全阀,其可以有效弥补法律不足、救济法治之穷。其次,特赦的对象多是一些特殊犯罪人,如果不加赦免,将会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国防等方面的利益。此外,特赦的适用,可以促使犯罪人对社会感恩图报,珍惜得来不易的自由,强化教育改造的效果,从而鼓励其自新迁善,并达成预防其重新犯罪之刑罚目的。最后,特赦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救济司法误判、错判的功效。我国的特赦制度也可以包容普通特赦和特别特赦这两种情形,以普通特赦为常态,以特别特赦为补充。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根据具体个案情状的需要因情施赦,灵活解决社会政治、经济、外交等诸方面所面临的问题。
我国ilfBlmHqNCg712cXeJ9Hog==现代赦免制度中也应确立赦免性复权之形式。不赞成将赦免性减刑分别纳入大赦、特赦的范畴。赦免性减刑也应在我们力图重构的现代赦免制度中拥有容身之地。
一般赦免,可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立赦免事务委员会(或赦免事务室)作为常设性机构,专门负责处理具体的赦免事务。一般赦免案完成后,可以交由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根据《立法法》第24条的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一般赦免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我国个别赦免之程序可以实行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并行的模式。一方面,可以由赦免权人根据赦免事务委员会的建议,主动对特定犯罪人予以赦免;另一方面,也可以由犯罪人本人或者其亲属提出申请,或者由犯罪人服刑场所、有关检察机关等代为提请。当事人申请赦免或者有关司法机关依职权提请赦免的,赦免申请书及相关资料将被提交赦免事务委员会,由该机构负责调查和审查。赦免事务委员会在必要时,可以向原处理案件的法官、检察官调查,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还可以让公安机关等政府部门的职员进行调查并提交报告书。赦免事务委员会在具体审查能否赦免时,主要应考虑如下方面因素:其一,犯罪人自身方面的因素,如犯罪人的性格、悔改表现、再犯可能性、对社会是否仍有不满情绪以及社会生活有无障碍等;其二,社会对犯罪人的客观评价,如有无社会责任感、家庭责任感等;其三,原处理案件的法官、检察官的建议、意见;其四,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意见;其五,是否存在错判、误判,有无救济之需要;其六,其他应当考虑的因素。在综合考虑上述诸多因素的基础上,赦免事务委员会确定向赦免权人所提出的具体报告书和建议书,对案件有关情况客观给予描述,并表明其同意或者反对赦免的具体意见。赦免事务委员会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报告书和建议书。在接受报告书和建议书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应作出是否赦免的决定。如果决定给予赦免的,由国家主席以赦免令颁行。
在通过宪法解释确立现代赦免制度宪法地位的基础上,还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行专门的赦免法,从而系统构建现代赦免制度的详细内容。赦免法从性质上讲并非行政法,而是宪法性规范。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摘自《法学》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