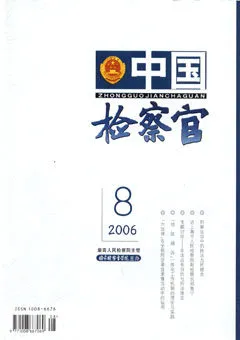“能而不予阻止者,有罪”
内容摘要:不作为犯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义务问题。过失作为能转化为故意不作为犯罪。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定刑对本来还构成的遗弃罪或者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一并作了刑罚评价。不能简单认为,纯正不作为犯就是行为犯,不纯正不作为犯就是结果犯。消极安乐死因不具有作为义务而不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放弃职守的,应以滥用职权罪论处。
关键词:不作为过失作为安乐死滥用职权罪
一、不作为犯理论的核心问题
处罚不作为就是强制他人进行一定的作为,是限制行动自由,因此,必须尽量慎重。现代刑法学的鼻祖费尔巴哈早在两百多年前就指出,犯罪原则上限于作为犯,不作为犯只是在依据“特别的法的根据(法律或者契约)”存在作为义务的场合,才例外地被承认。[2]尽管长期以来,关于不作为犯人们一直困扰的是处罚不作为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以及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等问题上,但现在人们的共识是,不作为犯的基本问题在于,在何等条件下不阻止构成要件该当结果的发生,能够与由于积极作为引起的结果等而视之。[3]换言之,不作为犯的核心问题在于作为义务范围的确定问题。
二、不作为犯理论的具体展开
(一)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
为什么要区分作为与不作为?处罚不作为犯以具有作为义务为前提,因此,如果认定行为属于不作为,则必须认定其负有作为的义务,否则不能处罚,此其一。其二,由于不作为不同于作为的行为构造,行为类型不同,则着手的认定、完成与未完成形态的认定、因果关系的认定等,都会显著不同。
但区分作为和不作为并非易事。一个人不小心把警察的脚轧在车轮下面,当被告知应当马上启动车辆以救出可怜的警察的脚,但这个人拒绝这么做,而是下车自己溜达。这个人的行为是作为还是在不作为?结局是,这个人被控袭击警察罪。[4]汽车司机在十字路口遇到红灯时,仍然向前行驶,导致行人死亡。是作为还是不作为?从不应当向前行驶而向前行驶(不应为而为)来看,属于作为;从应当刹车而不刹车(应为而不为)的角度来看,则属于不作为。[5]笔者设想,一个人交通肇事把另一个人轧在车轮下,下车一看,原来是他早想杀害的仇人,于是他就独自到边上溜达去了。如他所愿,他的仇人死于非命。那么这个人的行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呢?是负过失作为的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还是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还是数罪并罚?不无疑问。
国内有者认为,使法益状况恶化的场合,就是作为;没有使法益状况恶化的场合,就是不作为。[6]笔者认为,这个标准基本是可行的,但是,在具体情况下还少不了进行规范性评价。例如,没有任何过错地把人轧在车轮下,[7]刑法不能评价无过错行为,但可以评价发现有人被轧在车轮下后而不迅速将车开走的不作为,只需评价一个不作为。如果是司机过失地把人轧在车轮下,发现情况后还不迅速移动车轮,那么,既应该评价交通肇事的过失作为,还应评价后续的不作为。
(二)过失行为(包括不作为)能否以不作为转化
1过失致人伤害、失火等先行过失行为能不能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不作为的话,是否就构成故意的不作为犯罪?
学者基本上认为作为义务的来源包括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一个人失火后,坐在旁边看着大火熊熊燃烧而不扑救,大多数人会倾向于以放火罪定罪处罚。但问题是,泥瓦匠不小心从屋顶上掉下的砖头砸在行人头上,不下来也不吆喝别人施救,而是坐在屋顶上眼睁睁地看着行人流完最后一滴血死去,恐怕不少人就倾向于定过失致人死亡罪了。但是笔者认为,在能抢救而不抢救以致放任其死亡,按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明显违背一般人的法感情。因为人们通常认为带邻居家小孩游泳,行为本身连违法都算不上,在小孩发生危险不予救助以致小孩被淹死,却能以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定罪。两相比较,刑罚的评价过于悬殊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过失致他人健康以至生命法益处于危险状态下,能予救助而故意不予救助的,应当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这样会导致处罚过重呢?笔者认为,尽管人们通常认为不作为的犯罪比作为社会危害性小,道义上的可非难性也较轻,尽管国外也有可以轻处不作为犯的立法例,如德国刑法第13条第2款的规定,但是我国刑法关于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是死刑到3有期徒刑,因此,用故意杀人罪予以定罪,从定性上可谓恰如其分的评价,从处刑上也可以不至于处罚偏重。
2交通行为导致事故发生后为人逃逸的,能否以故意不作为论处?
国内学者在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能否定故意杀人罪的问题上,主流学说在这一问题上似乎有些犹豫。[8]一方面认为,肇事者有救助义务,另一方面又担心如定故意杀人罪,就会使大多数的过失犯罪由一罪变成两罪。其实,既然失火行为者有意不救火,能转化成放火罪,连没有过错的先行行为导致法益处于危险不救助的,也能构成不作为的杀人罪,那么,交通肇事后,在被害人的健康或者生命处于危险状态,不积极救助,导致被害人有由轻伤转化成重伤,或者由伤害转化成死亡,又有什么理由不能定故意伤害(重伤)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的呢?毫无疑问,日本的主流观点不承认一般情况下交通肇事逃逸行为按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论处。但是笔者注意到,在日本刑法典中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刑是50万元以下罚金,而业务过失致人死亡的却处5年以下惩役、监禁。很显然,对交通肇事这种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是远远高于普通过失犯罪的,[9]因此,在日本,一般的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伤的行为,观念上认为以本来的业务过失致人死伤定罪处罚,就能做到罪刑相适应了。然而,在我国,普通过失致人死亡的最重法定刑只有7年有期徒刑,和一般的业务过失犯罪最高法定刑持平。因此,立法者认为,若对一般的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最重只能处7年有期徒刑,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事实上,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在人来人往可能被救助因而只是给被害人的生命造成危险的犯罪,可评价为遗弃罪,[10]若是在人烟稀少,被害人的生命完全依赖于肇事者的救助,在这种情况下,不予救助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就应该以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但立法者考虑到如定两罪,在理论上恐怕很难得到支持,实践中具体情况下到底是构成遗弃罪还是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也是个问题,[11]故选择了现在这种对所有的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专门规定了七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的法定刑,以便能对交通肇事行为本身以及交通肇事逃逸致被害人死亡的的遗弃或者故意不作为的杀人一并做出刑罚上的评价。
此外,如果司机没有任何过错,事故由“被害人”负全责,司机对对方有没有救护的义务呢?如果司机“逃逸”致使对方死亡,能否给司机定罪,若定罪,又该定何罪呢?首先必须肯定,由于司机对事故的造成没有过错,故不能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司机的刑事责任。其次,我们考虑被害人是撞在正高速行驶的客观上对行人存在高度危险的机动车上,尽管司机没有任何过错,但面临一个若不及时救助就可能马上陨落的生命,况且救助对司机来说又不是代价太大的情形,笔者倾向于司机负有救助的义务,如不救助致使被害人死亡,可能构成遗弃罪。当然处刑上可以适当从轻。这个问题尚需继续研究。
(三)不作为犯的犯罪形态问题探讨
将不作为划分为纯正的不作为犯和非纯正的不作为犯,是由卢登(Luden )首先提出的。[12]在大陆法系国家,有观点认为,纯正不作为犯是纯粹行为犯的对应物,而不纯正的不作为犯是结果犯的对应物。[13]国内有观点认为,只有当不作为已经造成了危害结果时才构成犯罪。[14]从要求不作为与作为具有等价性而言,该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作为是否与作为等价,并不只是取决于是否发生了结果;当刑法规定某种犯罪的成立不要求发生危害结果时,没有造成危害结果的不作为也可能成立犯罪。[15]其实,不作为犯,既可能是行为犯,也可能是结果犯,既可能是危险犯,也可能是实害犯。[16]如遗弃罪,是行为犯,也是实害犯,不作为的杀人,是结果犯,不作为的放火,既是危险犯,也是结果犯。既然如此,我们在分析具体不作为犯的既未遂或者预备、中止时,就只能从刑法的目的,也就是从法益侵害的程度以及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法益的角度进行具体地分析。笔者倾向于,将遗弃罪以及不作为的渎职犯罪,如重大责任事故罪、玩忽职守罪,作为实害犯处理。即只有造成实际的较为严重的损害的,才成立犯罪。偷税罪、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不退去的侵犯公民住宅罪,要么不造成严重后果的就不构成犯罪,要么作为危险犯对待,而不宜认为一产生作为就既遂因而不再有未遂、中止存在的余地。对于不作为的杀人罪,和作为的杀人罪一样属于结果犯。而不作为的放火罪,和作为的放火罪一样,属于危险犯。只是不能认为,一造成危险状态就是既遂,致使放火人丧失成立犯罪中止的机会,而不利于有效保护法益。
不作为犯是属于即成犯、状态犯,还是继续犯?笔者认为,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而言,原则上和相应的作为犯一样。对于纯正不作为犯,基本上可以考虑属于继续犯。当然,这只是大致的处理原则,对于具体的不作为犯罪,还应当根据法益保护原则,进行具体地分析。
(四)不作为与安乐死问题
不作为怎么和安乐死联系起来了呢?先请看英国的一个案例(Airedale NHS Trust v Bland(1933)Hl)。这个案例是关于撤出从医学角度没有治愈希望的维持生命装置所引起的争议。[17]英国学者介绍说,在阿里戴尔NHS信托公司诉布兰德(即上述案例——引者注)一案中,区分不作为和作为是做出重要判决的基础。B是希尔斯巴洛体育馆不幸事件的受害者,三年半的时间一直处于植物人状态,从医学角度看,没有恢复或改进的希望。在B的父母的支持下,信托公司(The Trust)申请宣布同意他们合法地停止继续给B人工呼吸、营养、输液和医疗,从而使B安静地死去,最高法院为B指定的临时监护人不同意该申请,认为停止供给食物将构成谋杀罪。法官批准了该申请并进行了宣布。上议院维持上诉法院的决定。存在杀人的故意是无疑问的。采取上述作法的目的是终止B的生命。为了杀人注射致命药物或实施任何类似行为,一般认为构成谋杀罪。但是上述作法被认为是不作为,而不是作为。高夫勋爵(Goff)说:“问题不是医生是否采取措施杀死他的病人,或采取措施加速其死亡,问题是医生是否应该或不应该继续给病人提供可以延长其生命的医疗。”高夫勋爵还说,终止医疗很难说是为了病人的最大利益,但是,可以合理地认为,继续治疗,不是为了病人的最大利益。“终止”和“不继续”的意思看起来似乎相同。但是,前者表达的是作为行为,这是不能允许的,而后者表达的是不作为,是允许的。[18]
由上述案例笔者想到,在国外称停止继续治疗或者撤出维持生命装置的所谓的消极安乐死,其实是一个不作为问题。而不作为的行为即是一个对构成要件的解释问题,[19]也是一个不作为与作为之间的等置判断问题。病人的家属在通常情况下,也就是说,有治愈希望和有救治必要的情况下,不予救治,显然构成遗弃罪。但是如果没有治愈可能和救治必要,似乎就没有理由仍认为,存在救治的义务。因此,在医学上认为没有救治必要的病人,其家属放弃继续治疗,不构成不作为犯罪。对于医生来说,更是只对有救治必要的病人在特定情况下负有救治的义务,[20]因此,医生按照病人家属或者其他监护人的意思撤除救治装置,显然不能构成包括不作为在内的犯罪。
换言之,在我们讨论安乐死的合法性问题时,首先得将上述对没有救治必要的病人停止继续治疗或者撤出维持生命的装置的所谓的消极安乐死排除在外,否则,难以开展关于安乐死的卓有成效的讨论。
(五)违反作为义务的罪名确定问题
有救火义务而不救火,就应以放火罪论处吗?在日本,火灾发生之际,受公务员要求援助救灾者,未回应该要求时,成立轻犯罪法第一条八款所规定之不救助罪(纯正不作为犯),而未援助之结果,纵使致房屋完全烧毁,亦不直接发生不作为放火(刑法第一零八条)之作为义务。[21]笔者由此想到,睡在隔壁房间的已与妻子分居的丈夫听到歹徒正在强奸自己法律上的妻子而不予救助,构成强奸罪吗?警察听到正在遭受抢劫的被害人的呼救不予救助,构成抢劫罪吗?不存在共谋的情况下,说丈夫构成不作为的强奸,恐怕说不过去,因此以遗弃罪定罪较为合适。警察不救助什么,就相应构成什么犯罪,恐怕也不合适,而且处刑可能也偏重。有人说,警察过失不作为时,如轻信强壮的女被害人能够勇敢地战胜强奸犯,构成玩忽职守罪,故意不施救的,构成滥用职权罪。但是问题是,我们的权威教科书认为,滥用职权罪的客观行为只包括两种情形,一是,行为人不依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非法地行使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二是,行为人超越其职权实施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22]由于警察并没有积极地利用职权,看来定滥用职权罪有困难。定玩忽职守罪行不行?前述教科书又认为玩忽职守罪的主观方面限于过失。[23]看来这似乎又是立法的疏漏。我国新刑法规定了放纵走私、放纵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数十种故意不作为的渎职罪名,却没有规定故意不作为的兜底性罪名。抑或,立法者认为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两个罪名就全都可以应付了。那又成了解释论的问题。从字面理解,我们学界的主流观点对这两个罪名的解释似乎合情合理。但是,对于上述故意不作为的渎职行为无论如何都有处罚的必要,不处罚的话,显然违背一般人的法感情。
参阅国外的相关规定可以发现,俄罗斯的权威机关将其刑法典第285条滥用职权罪的客观表现形式解释为包括故意不作为。[24]德国刑法典第336条规定了不实施职务行为的犯罪。意大利刑法典第328条规定了拒绝职务行为的不作为的犯罪。等等。看来,在国外对于国家公职人员的故意不作为的读职犯罪基本上是有明文规定的。那我们国家呢?笔者认为是解释论的问题。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滥用职权的客观表现包括故意不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或者说任意放弃职责的情形。[25]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是极富有见地的,因此完全表示赞同。由此认为,警察等公职人员放弃职守,故意不作为的渎职行为,符合一般滥用职权罪或者特殊滥用职权罪的其他构成要件的,应当以该罪论处。
参考文献
[1]这是法国法学家罗瓦塞尔的一句名言,转引自(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著《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7页。笔者在这里只是借用一下,显然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
[2]转引自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xuk5DfhrX1UX4w8427ilxg==社1999年版,第93页。
[3](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著:《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720页。
[4](英)Julia Fionda and Michael J Bryant,Briefcase on crimi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