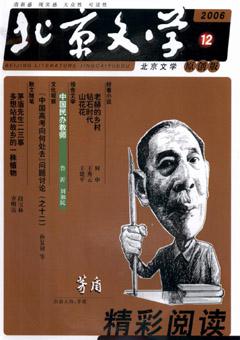娘家的点点滴滴
朱敏敏
娘家,一个永远充满着温馨的词;娘家,一个永远充满着回忆的词;娘家,一个永远让女儿充满愧疚的词……哪怕再过几十年,娘家的点点滴滴还是令女儿回肠荡气……
娘家的路
娘家的路起了个耐人寻味的名字——天钥桥路。
懂事时,和小伙伴们北起徐家汇,南至中山南路,把个天钥桥路来回走了两圈,怎么也找不到一座桥。最后见通向徐家汇的起点有点坡度,就一致“考证”为就是这“桥”。于是隔几天就来这里一次,幻想突然冒出个仙童,领我们进一回汉白玉雕成的天堂看看。父亲知道了,笑着对我们说:“这里原来的确有座桥,只是座小木桥,搁在臭水浜上,两人一走上去,木桥就‘咯吱、咯吱晃个不停。”
幻景一下子破灭了,我们几个伤心了好一阵子。
那时候,这条窄窄的石子路上没有汽车,只有三三两两的人力车、自行车在这里穿行,偶尔,也有几辆三轮车打这儿经过。沿街都是些又小又矮的平房,最高的就是娘家三层楼高的启明新村,最大的大概要数徐家宅院,那是个很大的本地院落,里面住着最早搬到徐家汇的徐氏后裔。他家有个石白,过年时,母亲总带着我拿了些糯米去那里舂粉。徐家很客气,从不收费,见我们母女俩身单力薄的,就叫了孙儿帮忙踩石臼,母亲就让我在一旁用条小棍轻轻地拢粉,我特别喜欢干这活,挺好玩的。
不过,那时候,最感兴趣的是领着弟弟去家对面的第四女中看传说中的嬷嬷。这一带许多人家都信仰天主教,家中有供台,徐家汇还有个教堂,可是看惯了都不如想像中的嬷嬷神秘。于是,我们常常躲在第四女中的门外,睁大着眼睛,静静地候着嬷嬷,一等就是几小时。可是,每次只见到放学后叽叽喳喳蜂拥而出的女孩子,从来也没见到嬷嬷。于是,讲的人又说嬷嬷晚上出来,晚上,我们是断然不敢出门的,我家后面不远就有守着牛棚的大狼狗,奶牛棚后面是农田,农田的深处是墓地,徐阁老的墓也安在那里,晚上风声乍起,树叶瑟瑟作响,我们就吓得靠紧外婆不敢吱声,哪里还敢出门看嬷嬷呢?
后来,先是南端迁了墓地、奶牛棚,渐渐地农田越变越少了。突然,有一年农田上盖起了几幢四层楼房,楼房底层开了几家商店。母亲非常兴奋,带着我们去参观了一回。我们不满足,瞒着母亲去买了几颗泡泡糖,一路吹着泡泡跳跳蹦蹦回到了家。
北端变化大些,有了文化宫、小商店、旅馆、徐闵线起点站。逢到夏季的夜晚,我们悄悄地溜进文化宫,女孩子追萤火虫,男孩子捉蟋蟀,倒也挺有趣的。
路也开始变了,先是石子路变成了柏油路,接着,柏油路拓宽。文革后,我去了农场。三年后,我背着行李调回了上海,突然,一辆56路公共汽车由南而北驶来,我傻了眼,伫立在路旁,静静地候着第二辆、第三辆。回到家,还没开门,邻居们看见我从农场回来,不说别的,一个个兴奋地对我说:“看见吗?我们这儿通车了。”
通车后的天钥桥路开始热闹起来,小汽车、卡车络绎不绝,马路两旁的矮平房渐渐少了,徐家宅院还静静地卧在那儿。
一晃十年过去了,我成家了,搬到了上海的另一头“东区”。路远了,来得少了,下了车,就尽量走近路,穿小弄到娘家,也忘了看看这条路。
突然,有一年回娘家时,15路电车停在了天钥桥路的北端路口,下了车,我蒙住了,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这条走了几十年的路竟然一点都不认识了,沿街的小店拆了,徐闵线终点站迁走了,高高的旅馆也拆了,取而代之的是汇联商厦、西亚大酒店、银行、煤炭科学大厦、证券交易所、邮电大楼,各式自选商厦,西式的面包房、布店、服装店、理发店……一应俱全。又一次拓宽后的天钥桥路上,原先几条蛰居的小石子弄都拓宽变成了柏油马路,电车、汽车、轿车不断穿梭。我来不及去娘家,带着孩子由北至南,沿着孩时“考证”的路线足足走了三小时,还只是走马观花式的。当孩子沉浸在汇联商厦儿童城的滔滔不绝的描绘中时,我的心止不住颤动起来,不由自主地走到了天钥桥路的“桥”上。
突然,我的眼前似乎出现了“天堂”:偌大的,法式的街心花园替代了铁栏栅围起的肇家浜,新六百商店、大千美食林、地铁站商城、东方商厦、太平洋商厦、徐汇文化活动中心,错落有致的万国建筑群,几十种车子飞驰而去……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寻找仙童进“天堂”的愿望,如今,梦想成真。东方商厦大厅里传来了阵阵悠扬的琴声和着华丽的万国建筑,我的身心似乎飘起来了。
许久,我慢慢地朝娘家走去,以前引以自豪的启明新村忽然变得那么矮小、那么破落、那么碍眼地缩在高楼大厦中。徐家宅院不见了,围墙里不时传来挖土机、打桩机发出的轰鸣声。
我突然感慨当初为娘家的路起名的人,尽管这一切是后人做的,是几十年后实现的事,可是能在五十多年前,上海西区小镇旁的一片废墟上,为一条小小的石子路起这么个充满憧憬的名,却也是件了不起的壮举。
外婆的小脚
小时候最爱看外婆裹小脚,那长长的白布从脚尖慢慢往后裹,把那“三寸金莲”裹成个“长脚小粽”,那情景令我好生羡慕,便央求外婆给我也裹一下。外婆苦笑着说:“真要那样,你哭还来不及呢!”
念小学时,我贪玩。放学后,书包背着,去同学家玩。外婆看见弄堂里有学童出现就开始盼着我回家,而我一玩就忘了时间,于是,外婆就到我常去的几位同学家寻我。同学家的楼梯是木制的,外婆走路力在后跟,一上楼,那“咚!咚!咚!”的声音就提醒了我,我正玩在兴头上,不肯回家,忙躲在门后,同学便倚在门口,待外婆一问她,她就撒谎说我不在,外婆也不再问什么,那双小脚又“咚!咚!咚!”地往回走了,我们又玩开了。回家时,天已黑了,外婆急着催我吃饭,似乎别的不再记起似的,我当然也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了。
那年中学毕业时,我被分在市郊农场。我看外婆难受,就对外婆开玩笑:“外婆,您不是喜欢吃蟹吗?那地方产蟹,以后我可以常给您捎蟹来的。”外婆怎么也想不通,要我陪她去学校找老师论理,我不肯,她便叫母亲陪她去了。我家离学校有四五里路,当时没车可乘,她硬是支撑着那双小脚赶到学校。老师那儿没有讲通,于是,她又抹着眼泪气呼呼地挪回了家。第二天,她那双小脚肿了,可她却没有叫疼,流着泪,怨着老师。以后的十多天里,天天如此,仿佛我一去,便不能回家似的。临走那天,她硬是要送我,“咚!咚!咚!”地赶到吴淞码头。待船开远时,我还看见外婆倚在石栏杆旁抹着泪,我的泪也止不住流了下来。那时,外婆已近七十了。
十多年后,我们几个外孙、外孙女一个个离开了娘家,有了自己的小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外婆因为年纪大了,小脚肿痛而不再出门,常常倚在窗栏边,眺望着楼下弄堂里的变化。我们回家走进弄堂,她便激动得什么似的,此后,一直陪着我们聊长叙短,此时的她是那么的神采奕奕。临到我们离
家时,那双小脚又挪动着忙开了,把亲戚送给她的零食一个劲地往我们包里塞,然后,默默地注视着我们,直到我们的身影渐渐地消失。
九零年的国庆,我们想带外婆去观灯,可那时已经封路了,我们就借了辆手推车准备推她去。可她却怕连累我们,不肯去。我们死缠硬磨了好一阵,她才整理一番随我们去了。从徐家汇到外滩来回长达四个多小时,外婆一直端坐着,静静地默记着沿途的灯景,眼光里充溢着自豪和幸福。以后,每每亲戚来访,她总要提及那段往事,总要夸外孙女事事想着她,外孙女婿办事诚恳,我们听了好一阵内疚。
电视普及后,外婆喜欢上了电视节目,总是静静地坐在一张藤椅上,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地接着看,一看就是好几小时。从那里,她走近了世界,从那里她的人生丰富起来。每当见到我们时,她就把那些电视节目中的大事、有趣事,一一地告诉我们。我们很惊喜外婆知道得那么多,可是心里也产生了些许痛楚,想想外婆如果不是小脚,她能直接在外面坦然地走走,她离世界就会更近点了。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九四年的一个晚上,外婆看了两三个小时的电视,扶着藤椅站了起来,突然,那双小脚麻了,没有感觉,不能站稳,她的腿软了,歪歪斜斜地倒了下来……外婆的右大腿骨折了。
骨折后的外婆躺在了床上。三个月后,骨接好了,大家都劝外婆锻炼,外婆也这么想。可是年事已高,又是小脚,怎么也动不了。外婆渐渐地放弃了锻炼,我们也渐渐地发现外婆确实难以锻炼了,外婆的那条受过伤的腿短了,那双小脚萎缩了。外婆只能躺在床上,或是被抱在躺椅上。我们去探望她时,她总是伸出手,握着我们,告诉我们,我们的父母是多么地不易,她拖苦了我们的父母,要不就静静地听我们讲外面的世界……过新年时,我们的孩子去时,她还用一只颤巍巍的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个红包给曾外孙辈,那时候,我感到外婆的眼中是一种强抑住伤感的笑容,我们的心里很酸苦、很无奈。
外婆躺在床上近四年,她的全身器官逐渐、逐渐地失灵了,但是,见着她的人还都说她美,说她秀气。渐渐地,外婆很少说话了,她整天静静地想着什么,也许她在回放她的一生。那双小脚呢?即使再热的天,总是藏在被子里。
九七年的劳动节,外婆已经有两天昏迷了,我们离开时与她告别,外婆的嘴张了下,床单里的小脚抽搐了一下,仿佛告诉我们,她的脚痛,不能来送我们了。我们以为,外婆还会醒过来的,没想到那天竟是和外婆的诀别。
外婆走了许多年了,现在,我每逢看到街上小姐们穿着长长的尖头皮鞋时,我就会想起外婆用长长的白布裹小脚的情景。外婆的母亲为了外婆的前途,裹了她的小脚,这一裹,九十多年,害苦了外婆,也害死了外婆。如今,一些小姐、女士,为了时髦穿起了窄窄的、长长的尖头皮鞋,不很舒服,不过一时的风光,为它受些苦,也认了,反正,时兴的东西,都是一时的,不舒服也很快会过去,不像我的外婆,会为它付出一生的代价。
母亲与编织
儿童节还没来临,母亲已经给我们姐弟四人的孩子各织了一件毛衣。儿子的那件是海军衫,蓝白相间,穿上它,一个威武的小海军出现在眼前;侄女的那件是蝴蝶衫,五彩缤纷的,穿着它,一朵花蝴蝶翩翩起舞;外甥的那件是燕尾服,深黑的,穿着它,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向我们走来;外甥女的那件是芭比娃娃的淑女长裙,玫瑰色的,穿上它,典雅高贵的洋娃娃活脱脱地站在我们面前。
母亲四岁时,外公就病逝了,生活变得十分艰难。十二岁那年,她进了编织社,学织毛衣。为了攒多点钱养家糊口,母亲拼命地织。夏天,酷暑难忍,母亲不能摇扇,满身痱子,母亲还在织着;冬天,严寒难当,母亲的双手冻得裂开了口,她还在织着。
织着,织着,渐渐地,母亲喜爱上了织毛衣,她织的毛衣,有了自己的风格,有了自己的品位。漫漫五十多年里,母亲编织着许许多多花絮,交织着一个一个爱的故事。
我们姐弟几个从小到大的毛衣都是母亲编织的,她不断地在这些毛衣上编着新的花样,翻着新的款式。特别是每年年底她总要花上几个通宵,给我们每人编结一件上乘的毛衣,惹得同学们羡慕极了。
记得那年我进了农场,闲时自己也学着织了件毛衣。春节回家,刚想拿出那件毛衣给母亲看,让母亲觉得我长大了,没想到母亲已从衣橱里取出一个塑料袋,透明的塑料袋里,一件天蓝色夹花绒线织成的花式毛衣,折叠得平平整整的。看得出从颜色、花样到款式,母亲都经过了一番精心的设计。相比之下,我的那件就再也不敢拿出来了。我把母亲编织的毛衣带到农场,女友们赞不绝口。母亲编织的毛衣是那么的精美,我把它视作一件工艺品。当时的农场工作又太艰苦,我一直珍藏着没有舍得穿它,直到回到上海后,才穿在身上,以此安慰母亲。
以后,我成家了,自然地也做了母亲,生活逼着我必须学会编织,而我的母亲,则渐渐地将心血倾注到外孙这一代。那年我四十岁时,母亲又送来了一件深玫瑰红的毛衣,远看近瞧很难辨出是手工编织的,花式如同花呢织物,款式又是大衣式,厚厚实实的,整件衣服显得那么和谐、统一,穿在身上显得雍容大气,精神了许多。母亲得意地告诉我:“这是新学的阿富汗花样,款式是当今最时髦的大衣式。”
年前回去时,母亲托人买来了编织机,正学着用机器编织呢!父亲告诉我:“你妈妈说,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穿机织的羊毛衫,她的棒针编织不能适应儿孙们的欢迎了,所以就学机织的了。”
前些天,在南京路上看见一家绒线店里,几位穿着时髦的女士,正在店里教人学织毛衣。店里的绒线制品可真不少,从婴儿的鞋袜到老人的帽子,从古朴的大褂到时新的连衣裙,应有尽有,编织得十分精巧,深深地吸引着来往行人,原来这家店是以教编织带出卖绒线的销路的。我看了后很是感叹,回家后就告诉了母亲。那天母亲正发气喘,马上整理一番,叫我陪她去观摩织品。父亲在一旁嗔怪道:“看看,多事了吧,没看到你妈妈正生病吗?”但是,我们还是陪母亲去了,谁又能阻挡母亲对编织的钻研劲呢?
这几天,父亲正帮助母亲整理她的编织技艺,看着满桌的小样照片,一床的各式毛衣,我不禁感慨道:“妈妈的生活质量很高啊!”
责任编辑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