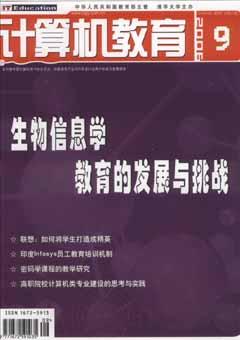高职院校计算机类专业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吴晓桃
记者: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类专业是如何设置定位的?
孙湧: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要问,开设某个专业到底想培养什么样的人,办这个专业的目的是什么?不能是为办专业而办专业,而只能是为满足产业分工和就业岗位群的用人需要,要关系到高质量人才培养问题。
我们在思考专业内涵定位时,原则是追随产业主流技术,并密切关注产业朝阳技术,这实际上是在考核专业领导的战略眼光。
朝阳技术是指充满机遇和风险,有可能推动新的产业大发展的那些技术。朝阳技术的市场份额需要从无到有、逐步扩大,有待我们慧眼识宝,有选择地进行师资技术储备,以便能够抢占先机,迅速形成专业特色。
主流技术是指广泛用于社会,研发的产品占据着庞大市场份额的那些成熟技术,它是由朝阳技术转变而来,代表了当前的市场份额。掌握主流技术的专业人才一般说来,必然拥有广阔用武之地和美好发展前景,若我们依据主流技术设置专业和培养人才,那么我们的办学和就业风险就不会很大。
2001年,深圳25%的信息产业都与嵌入式技术密不可分,国内却没有一所高校专业专门培养嵌入式技术人才,为此我们深职院率先而为,为产业发展服务。又如,PC从386开始就采用IA32技术,只有去博物馆才能找到采用IA16技术的PC,但国内高校到现在还在讲授IA16计算机体系结构技术,而我们从2003年开始再次率先国内高校全面讲授IA32技术,并出版了教材。
记者:学校依据什么原则来确定每个专业的能力构成和教学内容?
孙湧:在教学方面,普通高校强调学科建设,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完备性和厚基础。我们高职院校更加强调专业建设,强调就业岗位。比如软件开发不可能由一个人完成,需要一个团队来做,那么每个人如何扮演好一个团队成员的角色,如何扮演好项目领导的角色,就需要项目管理的知识和经验。项目管理属于计算机技术学科吗?回答肯定不是。如果学生去实施项目或者投标,它又涉及谈判、交际能力,要求方方面面、非常综合的能力。这种综合能力分解后我们称之为能力要素,这个能力要素实际上是属于不同学科的。不同的学科能力在我们这里融合为一个专业,或者一个就业岗位。我们的专业由多个学科能力综合而成。
记者:学校在明确了每个专业的目标后,又如何界定所教内容的程度呢?
孙湧:高职生源较差,许多学校都认为,学生太笨了,所以高职院校不能教授太深奥的内容,学生也不可能学会。事实上,如果你主观上认为学生不可能学会某项知识,那他最后往往一定学不会,因为你准备不足。我们深职院强调的不是老师会什么就教什么,也不是学生会学什么就教什么,而是强调市场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然而实际情况可能是,某个技术老师可能确实不会,那么可以让老师去培训去提高。
每个专业其实都面临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问题。很多人都说,高职学生层次不能高,而我们的观点并非如此。事实上,企业的首要任务是谋求生存和市场利益最大化,企业不可能牺牲自我生存权益来降低用人标准。因此,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准确定位专业内涵,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来确保毕业生能够承担起历史责任,这也是高职院校计算机类专业办出特色的前提条件。为此,关于专业教学内容深度,我们在战略部署上按照产业人才最高标准,在战术实施上却又脚踏实地按照现有条件逐步改善、逐步提高。如果我们认为学生学不会,制订的专业目标很低,那么我们永远都不会取得突破,形成不了特色。当一切按照最高标准来做的时候,通过老师水平和学生自信的提升,就可以逐步从基本标准向最高标准过渡。也许我们无法达到我们心中的最高点,但一定比没有标准要求所达到的水平高得多,更符合产业用人需要。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四个问题。其中,办学资源、实训设备、师资队伍这三个客观性问题是解决人才培养问题的外因,而内因则是学生的学习欲望和动力。学生不想学,再好的条件都枉然。
记者:在应对这些困难时,你们如何解决资源单一的问题?
孙湧:首先,每一个专业甚至方向都至少要与一个产业主流企业建立深层次合作关系,依托其主流技术办学,站在巨人肩上前进。比如软件专业跟Oracle、Sun、金蝶,网络专业跟Cisco、华为3com,嵌入式跟微软、Intel、ARM,计算机体系结构跟Intel等。合作伙伴一定要尽可能高层次。高层次合作伙伴的好处就是有很多企业资源,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前进。
在资源运作过程中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企业为什么要支持你?在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一见面,就说你要给我钱,给我设备。这样的话,难度就很大。政府有没有资源?有。它有政策,可以扶植你。企业有资源吗?也有,可以给你设备捐赠、课件开发,免费师资培养。但是,企业为什么要给你呢?很多学校说,政府不重视他们,企业不重视他们。在解决官、产、学、研关系的时候,我们又提出两个观点:
第一,从思想上,我们要为政府、为企业做事情,帮他们排忧解难。反正这些资源是要给出去的,不给你也会给别人,关键是要让企业、政府在给你资源时觉得物有所值,可以为他做事,而不能让政府和企业觉得你是个催命鬼,只会要钱、要物。依据这个理念,我们为企业和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使得他们见到我们不害怕。
第二,在行动上,要立足于捐赠,而不是采购。因为买卖是和Sales打交道,建立不了深层次校企合作,我们感兴趣的是合作。怎么建立合作?我们要捐赠。一开始捐赠会很难,谈判周期很长,有很多事情要谈一两年才会有结果。要企业捐赠东西,需要董事会讨论,要考虑捐赠得值不值。这是一个相对高层作出的决定,是一个集体行为。一旦东西捐给你了,企业就希望他捐的东西发挥作用。那么我们接着就让企业给老师做培训。那么昂贵的设备都捐了,还在乎这么一点培训吗?给一些教学资源让我们将你的设备发挥得更亮更有价值吧。这种培训,这种支持,不是一年两年的,企业只要希望他的设备发挥作用,他就会支持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面临一个心态问题。很多人说,我为什么要求你呢?我有钱,我自己去买。我买,我是甲方。那么就是企业来求你,来拜访你,请你吃饭。这种感觉是很舒服的。而现在要谈捐赠,我是乙方。有人会想,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好歹也是个领导干部,我为什么要求你呢?但是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为了给我们学校和学生带来更大益处,我们再苦再累也要做这事情。其实,企业也要生存,真正的慈善事业并不存在。要谋求企业支持,一定要想清楚企业利益在哪里,必须想明白这件事情后才能去拜访他。举个例子,思科为什么要做网络学院?因为他们希望他们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形成技术和人才垄断。为了追求更高的市场份额,甚至是垄断地位,他们选择了“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原则。这个小亏是什么,是我拿出一些资源给高校,这既有社会效应,同时,又让技术人员对他产生依赖。所以企业愿意支持高校发展。因此我们要去揣摩企业心态,揣摩他们的兴趣点在哪里。我告诉企业我能够实现他想要的,但是要实现他要的东西的时候,他要先支持我。
记者:你们如何解决实训环境规模不足的问题?
孙湧:在实训环境建设方面,首先立足于捐,然后才是通过设备采购予以补充。我们设备采购的三个指导思想是:
第一,实训室要规模,要做一个成一个,成一个做一个。比如在2001年,那时我们还没有计算机专用实训室。学校给了我们150万元,按照一般做法,就是一个专业撒一点,人人都有,但撒胡椒面是不会有好的规模效益的。所以当时我们把150万中的110万全部投到思科网络技术实训室建设。在建设思科网络实训室时,思科公司销售人员都觉得奇怪,是不是这学校钱太多了。当时思科的设备销售概念就只有校园网,还没有意识到,我校第一个拿110万资金大规模建设实训室,是给思科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销售模式,意义重大。
第二,实训室更要规模,而不是档次。很多人喜欢买最高档的设备,动不动就说我这个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但我们想法是只要够用就行,规模比档次更重要。如果学生实训是4人一组,往往容易产生一个人练三个人看。比如在建完Cisco网络技术实训室后,我们又用剩余40万元建设软平台网络异构实训室,让学生能够用AIX、Solaris、Macintosh、Linux、Windows等操作系统互联互通,教会学生系统的安装、维护等。性能差点、速度慢点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不是在校园网上大负载运行。电脑设备的速度和内存大小在这就不再重要,只要能够保证操作系统最先进就行了。有企业给我们做了很多高档次方案,我们说不需要,只要最低档次的设备就可以,所以价格非常便宜,可以做大规模,让更多的人在平台上实训。
第三就是以旧代新,扩大规模。什么叫以旧代新?就是采用淘汰下来的二手设备,这些设备可能用的时间并不长,把这些二手设备买下来供学生练习。由于是练习所用,要那么新的设备,那么快的速度干嘛?虽然速度慢点,但是价格却只有新设备的十分之一。这一点对没有足够经费的学校尤为重要,买一台新设备的经费,可以买十台二手的,而且对教学并没有影响啊。
记者:学校如何解决师资队伍能力老化问题?
孙湧:我们在师资培养方面主要有两种做法。第一,通过紧密型校企合作,低成本培养师资队伍并共享企业工程师。由于IT培训费用昂贵,一个培训动不动就要五千、一万的,紧密型校企合作可以获得大量免费企业培训,学校只出路费。原来派一个,现在就可以派两个或三个,确保教师紧跟企业技术发展。我们的观点是依托企业办学,企业资源要为我所用,但学校又不是企业的附庸和培训中心。
第二,对于主流技术,即使企业不免费,花再多的钱我们也要学习。如果费用很贵,完全依靠学校经费很困难,可以通过建立官、产、学、研新型合作关系,从政府那里寻求经费来支持老师进修。比如我们获得政府50万元软件产业发展经费,来保证我们老师的培训,接受最新知识和技能。接受最新知识的结果是什么?老师敢开课,能开课,开好课。
记者:学校如何解决学生学习动力缺乏的问题?
孙湧: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时,用我们俞仲文校长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是要证明高职学生素质有多差,而是要通过我们的努力,去帮助他们提高水平,低进要高出。”高职学生从小学到高中,所受到社会看法就是,“你这个家伙,你怎么老是学习这么差,太笨了。”自信心很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好的学习方法,没有好的学习习惯,缺乏自信心。许多学校都在说“三分育人,七分教书”,而我们是“三分教书,七分育人”。我们要教他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事,给他们自信。这是需要榜样的。我们通过创新大赛、兴趣小组来为学生树立榜样。只要学生想学,我们就配老师来指导他。等他们在比赛中拿了名次时,学生就会想,他进来的时候跟我一样,他为什么可以呢?不就是因为他努力了嘛。那我也可以努力,我也能行。
2004年我们网络专业首届毕业班毕业前夕,有两名在校大专生实现通过CCIE认证零突破。这一突破十分艰难,因为大量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程师都不一定能顺利通过CCIE认证,我们的学生不相信自己能过,因为前无古人嘛。我们一直鼓励他们,甚至老师帮学生垫付巨额考试费用。当胡冀南和赵鹏通过CCIE认证时,我们俞仲文校长就抓住这两个典型,给他们披红挂彩,树为学习标兵,报销了他们参加机试的1.3万元考试费用,同时还奖励1万元。虽然有的学生不知道这个CCIE能干什么,但他们认识这2.3万元钱啊,又有钱又有名,还上学习标兵光荣榜。马上,学生的学习欲望就被激发出来了,学习风气为之一变,从“前途茫茫要我学”变为“目标明确我要学”。再加上学生毕业后就业也好,更加刺激学生。比如赵鹏,2004年毕业后三个月就成为齐普生云南省分公司技术负责人。手下20几个本科生、研究生。2005年又升任公司南方区副总,待遇也上去了,年薪10多万。后面学生一看,CCIE的就业和个人待遇这么好,于是都来考。2005年,我们网络专业第二届毕业生24名同学(14.6%)考过CCIE,实现了CCIE的批量生产。第二年为什么那么多呢?因为学生想到,我的师兄都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呢?他们坚信只要我努力了就一定能成功。当学生CCIE越来越多时,激励目的达到后,金钱激励措施随之取消,学生已不在乎2.3万元,因为10万年薪比其他更重要,从而榜样的力量让学生明白自身努力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