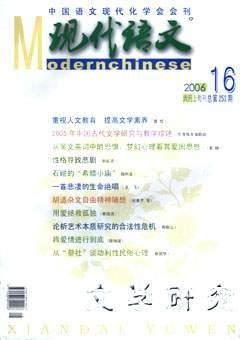揭开战国纵横家的神秘面纱
春秋战国之交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震荡的时期,自此直至秦汉统一的这段时间里,士阶层以它独特的社会角色和人格形态标志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是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顾炎武《日知录》)的时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社会形态迥然异于春秋之时。这“无定主”的“士”中就有纵横家之流,他们是诸子百家中最为活跃的一群。
何谓纵横家
《七略·诸子略》: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遭变用权,受命而不受辞。
《汉书·艺文志》: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颂《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下诈爰而弃其信。
《隋书·经籍志》:纵横者,所以明辩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汉书》以为本出于行人之官,受命出疆,临事而治。故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周官》掌交以节于币,巡邦国之诸侯及万姓之聚,导王之德意志虑,使辟行之,而和诸侯之好,达万民之悦:谕以九税之利,九仪之亲,九牧之维,九禁之难,九戎之威,是也。佞人为之,则便辞利口,倾危变诈,至于残害忠信,覆邦乱家。
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是战国时代的特征,纵横家是战国时代应运而生的产儿。所谓“横”,乃“连横”之简称,即以秦国为中心,分别联合山东任何一国,东西连成一条横线,攻击其他各国,如此分化瓦解山东六国,最后并吞天下,统一各国。所谓“纵”,乃“合纵”之简称,即山东六国从燕到楚,南北合成一条直线,联合抗秦,在强秦虎视眈眈之下,图谋生存。这正是战国时代政治斗争形势的生动写照。而所谓纵横家,则是为适应各国政治斗争的需要,或主纵,或主横,或奔走游说,或入朝干政,直接服务于统治者的一批谋臣策士。他们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智囊人物,他们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地理、风俗、民情,甚至国君的爱好、志趣,都了如指掌。在战国时代的政治、外交战线上,他们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战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社会转型、社会变化最剧烈的时代,其情形诚如顾炎武在《日知录·周末风俗》中所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主,而七国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春秋的新观念、新气象对传统的冲击,引起社会的强烈震颤,这种震颤在战国则发展成为翻天覆地的涤荡,业已残破的传统政治格局、传统阶层构造、传统思维方式、传统文化观念荡然而去,带有时代新鲜气息的政治格局、阶层构造、思维方式、文化观念春笋般拔地而起。学派林立,百家争鸣,一派开放向上的气象,纵横家也在这种环境中正式自立于诸家之林。
纵横家的政治活动
传统上认为,纵横家的活动仅仅局限于狭义的合纵连横运动,主要人物仅只苏秦、张仪、公孙衍等人,他们在学术上无重大建树,没资格与其他学派并驾齐驱。然而,战国的历史事实与合纵连横活动的全部内容表明,这种看法并不十分全面。
合纵连横是外交斗争,但绝不仅仅是外交斗争,实际上是战国兼并与反兼并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其中既有外交斗争、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又有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和各国之间的内部矛盾运动。这些斗争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具体内容,但彼此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相互依存,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共同构成战国兼并与反兼并斗争的广阔画面。这场斗争中,纵横家们是最积极、最直接、最实际的参与者,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关于其中重要的人物,我将其主要活动列举如下:
淳于髡,早年是齐人的家奴,婚后成为人家的赘婿,后因善于诙谐调笑而被进奉给齐威王。借助于在齐威王身边的有利条件,以隐言说动齐威王,助使齐国振兴。齐宣王即位后,他仍是辅国重臣。
张仪,三十岁成家之后出山游说,第一次他选中了楚国。他认为楚国雄据南方,疆域辽阔,物产丰富,甲士百万,战车千乘,积粟可支十年,且楚自春秋称王,素有吞并中原之心。根据这些情况,欣然入楚,稽留数年。殊不知楚威王刚愎自用,迷信武力,疏忽政治斗争,对纵横之士毫不在乎,沉湎于娱乐享受,不思奋发,重用疾贤妒能之辈。在楚受辱后西至秦国,游说秦惠王。秦惠王重用张仪为相,让他充分施展连横之策,创下不世功业。
苏秦,洛阳贫民,在外出游说数君而无效的情况下来到燕国,燕昭王对他恩宠有加:“迎之于郊,尊现于庭”。经过数年的合纵游说活动,苏秦受到燕、赵、齐、韩、魏国等君的重视。苏秦在游说楚王东过洛阳时出尽了风头,不禁苏秦感慨地说;“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
冯谖,投奔孟尝君后因其才能无人赏识,“食以草具”,三次弹剑柄而歌要求提高待遇,均得到了满足。食有肉,出有车,母有养。
纵横家的思想品格
一个纵横家,由布衣贫民到高官显要,由默默无闻到叱咤风云,把满腹的经纶化为成功的实践,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需要经过游说、入仕到施展才华这样三个阶段。这个过程荆棘丛生、险情四伏,每一步都需要绞尽脑汁、认真对付。倘若有半点不慎,便有可能惨遭横祸。从他们迈出第一步之时起,面对的不仅是外交活动,而是与政治、军事紧密联系的综合性活动。他们在得势之后,直接参与合纵连横斗争,还要参与国家的重要决策,同时也无法回避内部的政治斗争。因此他们是外交、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活动家。纵横家所从事的活动及其人生道路,是一个复杂的运作过程,他们面对的常常是棘手而又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所以他们基本没有也不需要有价值评判的底线,只要能够取胜,会不计一切手段。他们的思想品格基本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他们以个人的名利为人生奋斗的终极,国家宗主观念淡薄。战国时代,朝秦暮楚、楚才晋用的事非常普遍,择主而侍无可厚非。纵横家像多数“士”人一样,并不以去国离乡为遗憾。所不同的是,对于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人来说,他们各有其社会理想,而且对实现其社会理想有系统的理论构想和欲以身心投入的崇高感;而对于纵横家来说,乱世反倒提供给他们更多的利益选择机会,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实现某种社会理想或者国家的前途、命运,而是个人的荣辱得失,急功近利是其一大显著特点。虽然战国时代的社会舆论不将人的服务范围与人的节操问题刻意相连,但并不意味就提倡随心所欲,漠视个人操守。由于人文环境的限制,再加上对理想的执着信念,孟子等人不能不四处游说,但他们注重个人名节,很少出尔反尔;纵横家则不然,他们以视为攸关的名利大小择处而栖,除了出于斗争中的防范和利益冲突所需,他们并不关注个人的节操问题以及群体的命运,苏秦、张仪、范雎、公孙衍、陈轸等皆是如此。当然,作为身家性命的依托和计谋得以实现的暂时所需,究其实为利益所需,纵横家们在某段时间里,主要为某一诸侯国服务,但情形则如《汉书·艺文志》所言:“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纵横家们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尤其最终凭此获得相应的富贵显荣,走出狭隘的家国之域,即使如履薄冰、燕巢幕上也在所不惜,因为承担风险,也享受锦衣玉食。由此看来,纵横之士们虽然在功利目的的驱使下,不乏扭曲变态的极端人性表现,但确实体现了一种拼搏进取的实践品格。
第二,轻仁义而贵权变,热衷于计谋策略,是纵横家的又一显著特征。春秋战国之际,社会风尚和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春秋时期虽霸主迭兴,战乱不息,但传统的礼仪道德尚未泯灭,人臣“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尤以义相支持,歌说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进入战国,“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蒙有温情面纱的传统礼仪道德沦丧殆尽,“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战国策·刘向书录》)至战国中晚期,列国“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矫称蜂起,盟誓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史记·六国年表·序》)在实用主义功利思潮泛滥的环境中,纵横家随波逐流,他们为获取功名,游说列国,“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 (《战国策·刘向书录》)见风使舵,巧言诡辩,挑拨离间,背信弃义,各种谋略诈术无所不用其极。苏秦反间于齐,张仪戏弄楚怀王,就是纵横家善用权谋的典型事例。
第三,纵横家多是“士”阶层中由庶民发迹的,但他们不愿苟全性命于乱世,洋溢着个体精神,膨胀着自我表现欲。动荡的战国时势中,纵横家是赶潮一族,他们渴望飞黄腾达,决不肯浪费时间为礼乐文明的沉沦而伤悼,更不想恪守伦理教化。时势造就了他们,他们从过去相当于不成文的国际法典的“礼”中解放出来,毫无“为富不仁”的心理恐惧,如苏秦、张仪、范雎等均是生于困顿的“无恒产”,而后得以显达的士人。在纵横家身上,尽管过多地暴露了人性“恶”的一面,但在那个天下大乱战争性质难以界定的时代,这也未尝不是一种生存方式的积极选择。纵横家们从事着无任何精神负累的智慧、心理和辩术的竞技,体现的是彻头彻尾的、除游戏规则之外无任何遵循的个人意志。在这里,人为了获得自由,成为自在、自为的主体,以舍得一身剐的无畏精神释放着自己的能量。他们大多博闻广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事,且能通权达变,使知识真正成为人们拥有的活的因素,再加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言辩,焕发出自由色彩的生命活力。
(张宪华,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