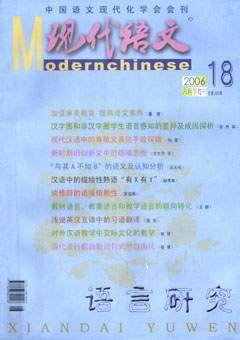“永远”的句法功能研究
[摘要] 迄今为止,所出的各种工具书、语法书、教科书,几乎都一致认为“永远”是 一个表示将来的时间副词,其主要语法功能是做状语。然而,我们通过对目前的语言实际情况的观察发现,“永远”一词除做状语外,还经常充当定语、宾语,偶尔充当主语、谓语。我们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用语的逐渐变化,现代汉语“永远”一词的句法功能正在逐渐扩大。
[关键词] 永远 句法功能 词性
迄今为止,所出的各种工具书、语法书、教科书,几乎都一致认为“永远”是 一个表示将来的时间副词,其主要语法功能是做状语,用来修饰动词或形容词。(见参考文献[11])《现代汉语八百词》的解释是“表示时间悠远,没有终止。指将来。”《现代汉语虚词例释》的说明也是“表示状态、动作一直延续下去,没有终止,或者强调持续不变。”《现代汉语虚词用法小词典》的解释也大同小异:表示时间久长,情况一直延续下去,没有终止或持续不变。《现代汉语常用虚词词典》《现代汉语虚词》《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也大都如此。以上所列工具书中的例子中,“永远”的语法功能无一例外地都是放在动词或形容词前充当状语,这样似乎会使我们轻易地得出一个结论:“永远”是一个只能放在动词或形容词前充当状语的表将来的时间副词。
然而,从语言的实际情况来看,尤其是从变化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语文建设》1996年第12期发表了裘荣棠先生的《让人疑惑的“永远”》,该文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永远”一词句法功能的复杂性,总结出了社会上流行的“永远”的两种新用法,其后周洪波先生(1997)对“永远”的词性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究和分析。张谊生(2000)对其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作了探讨。近年来,流行一时的女性小说中,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里出现了“永远”的又一种新用法,即“永远”充当主语。这些不由得引起了我们对“永远”一词的句法功能问题的兴趣与思考。
现代汉语中的“永远”到底具有哪些功能呢?我们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用语的逐渐变化,现代汉语“永远”一词的句法功能正在逐渐扩大。
一、“永远”的句法功能
为了对“永远”的句法功能作出更为准确、客观的判断与分析,有前辈通过计算机对《人民日报》1995年的语料(不含广告)做过检索,在统计出的936个用例中,大部分是作状语,修饰动词、形容词或者动词性短语、形容词性短语,但也有一小部分是做定语(28个)、宾语(6个)或谓语(2个)的。(见参考文献[13])为此,我又对《人民日报》1998年1月份的语料(不含广告)做了检索,统计出的结果也大致相同。但是,我们再到网上搜索一下,会发现情况就大不一样:“永远+的+名词”和“动词+到+永远”这两种用例高达几千上万条,而“永远”充当主语和谓语的用例也大大多于《人民日报》。这说明,从句法分布看,“永远”虽然主要是充当状语,但也经常会用作定语和宾语,还偶尔地充当主语和谓语。
(一)永远”充当状语。
“永远”首先是一个时间副词,所以其主要语法功能是充当状语。
“永远”充当状语时分布是比较自由的:既可以带结构助词“地”,也可以不带。例如:
(1)熬过隆冬之后,春天的草原上的生机将给世界再一次惊喜。因为他们,告别被永远地推迟。(《足球》2002年6月27日)
(2)圣诞夜的烟囱无论擦得多么干净,窗户无论怎样地敞开,那鞋袜里的礼物永远是劳动的成果,而非圣诞老人的恩赐。(《人民日报》1998年1月)
既可以是连用形式,也可以是重叠形式。例如:
(3)于是我想分担她的那份疼痛,每每想念时,一份真真切切的痛楚就会如约而来,我痛着,那痛的电波如外婆温暖的手一样抚着我,我就盼着一直一直永远永远地痛下去,让我切切地感觉外婆还在我身边,减轻我十五年来的愧疚……(雯清《你永远软软地束缚我》)
(4)婶婶常劝她去整容,但若渲总是不肯,她要这一伤疤留着,永永远远地提醒她,铭记惨剧的发生。(唐絮飞《今天不想谈恋爱》)
据我们观察,不带结构助词“地”的用例远远多于带“地”的用例,在我们搜集的百余条“永远”充当状语的例子中,只有极少数带“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认为有以下两种原因:一是出于韵律和谐的考虑。其实几乎所有“永远”直接充当状语的句子都可以加上“地”,而句子仍可以讲得通,但不如原句那般顺口。如:
(5)她永远像带着一副假面,就连睡觉的时候,也不肯脱掉。(张洁《祖母绿》)
(6)她永远(地)像带着一副假面,就连睡觉的时候,也不肯脱掉。
二是“地”的强调作用。我们知道“永远”本身是个程度很深、语气很重的词,几乎相当于英语中的最高级,所以我们在要强调某个动作或状态时,在动词或形容词前加上“永远”便可。但如果觉得单用“永远”还不能表达出所需表达的强烈语气,那么在“永远”后面在加上结构助词“地”,语气就更强烈了。如:
(7)这个周日,52岁的“超人”因心力衰竭在纽约去世,永远闭上了眼睛。
(8)这个周日,52岁的“超人”因心力衰竭在纽约去世,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成都晚报》2004年10月12日)
另外,“永远”的连用形式和重叠形式也能起到加强语气的强调作用,后面可带“地”,也可不带,但两者之间也是略有区别的:不带“地”的句子比较口语化,如:
(9)永永远远走自己的路。
带“地”的句子则显得更书面化,如:
(10)可外婆毕竟是永永远远地去了,留给我的遗憾,也就永永远远地无可弥补,永永远远地刺痛我愧疚的心。(潘虹《遗憾到永远》)
(二)“永远”充当定语。
“永远”充当定语时,既可以修饰谓词,也可以修饰体词,如:
(11)你是我永远的表达。(马莉《你是我永远的表达》)
(12)达到这种境界,就会像孩子一样纯朴真诚,有一颗永远的童心。(萧关鸿《永远的童心》)
既可以是连用形式,也可以是重叠形式。如:
(13)当我发现我有永远永远的爱情,我就明白了,时尚的女性都在告诉世上的男人她们的每一根头发都是属于钞票的。(《歌宁文集》)
(14)永永远远的花期。(山城子《永永远远的花期》)
既可以带标记的,如(11)(12)例,也可以不带,如:
(15)永远高三八(网站名)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永远”放在谓词前作定语时,都是有标记的的,这是因为在短语中,如果去掉“的”,整个短语的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如“永远的沉睡”是定中结构,而“永远沉睡”就成了状中结构了,而短语的功能也由指称转化为陈述了。
(三)“永远”充当宾语。
“永远”充当宾语时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一般都出现在表示时间推移的终点或方向的介词“到、至、向”和表目的的介词“为了”等词的后面。如:
(16)我和你手牵手到永远。(网站名)
(17)这个秘密她将保留至永远,对谁都不透露。(楚妍《落跑大姐头》)
(18)因为使我飘扬的是我的心情,使我颤栗的是我的意念,文学的美丽给我的性灵所筑的道理延伸向永远。(小怡薰《与文学对视的日子》)
(19)我等你不是为了相聚,而是为了永远。(燕红君《等你是为了永远》)
“永远”还可以出现在判断动词“是”后充当宾语,如:
(20)在周小欧自己弹着钢琴唱起《走过昨天是永远》的时候,那悠扬的旋律和真情的呼唤感动着台下的歌迷,记者看见有歌迷流下热泪。(《扬子晚报》2005年3月7日)
(21)西谚有云:“书比人长寿”。文化是永远的,读书也不会是短暂的。这样看来,文化与读书也将是一个永恒的文明主题。(王建辉《文化与读书》,转引自张谊生用例)
例(21)张谊生认为“永远”同“是……的”一起充当合成谓语,现在学术界一般不采用“合成谓语”一说,我们认为这里的“是”充当谓语,“永远的”充当宾语。
还用少数用例,“永远”充当宾语,前面既不需介词也不用判断动词。如:
(22)纵使在城市中流连多年,却依然看不见下一个永远。(张信哲《下一个永远》歌词)
“永远”的连用形式和重叠形式也可以充当宾语,大都是出现在介词“到”之后,如:
(23)尼罗河神将赐予最大的幸福给埃及的人民,现在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这种祝福将持续到永远永远。(落枫薄荷《寂影》)
(24)我要与她一同居住,无论安乐困苦,丰富贫穷,健康衰弱,我都爱护她,安慰她,尊重她,保护她,专一于她,直到永永远远。(中台人的证婚词)
还有一种情况是“动词+永远”,如:
(25)Hot挚爱永远!
我认为应该看成是借助一定的语境而在动词“挚爱”后省略了“到”,也就是说“永远”是“到”的宾语,而不应另处理为补语,使问题复杂化。
“永远”充当宾语时,显然它的词性也不应是副词了,而前面提到的形容词也不具备充当宾语这种功能。我们以为,“永远”在这里已经转化为名词:“永远”与“到、至、向、为了”构成介宾短语;放在判断动词“是”后面,“永远”解释为名词也可以说是合情合理;而在例(22)中“永远”前用了名量词“个”修饰,把它解释为名词应该是更没异议了。
(四) “永远”充当谓语。
“永远”可以直接充当谓语,如:
(26)苏州是永远的。比许多雷霆万钧的炮声更永远。(王蒙《苏州赋》,转引自张谊生用例)
但充当谓语的用例十分罕见,还带有一定的个人言语行为和词类活用的痕迹。
(五)“永远”充当主语。
“永远”充当主语比较少见,在我搜集的几百条用例中,只找到三四例,如:
(27)永远到底有多远?(歌曲名)
(28)下一个永远就是现在,因为只有一个永远。(张信哲《下一个永远》歌词)
(29)永远,是条可怕的鸿沟,横亘在我们和我们最爱的人与事之间。(潘虹《遗憾到永远》)
其中,(28)例中“永远”充当主语和宾语的用法同现,前一个“永远”充当主语,后一个“永远”充当宾语。
二、两点补充
1.通常认为,副词是由实词虚化而来,因为实词是有实在的词汇意义的词,而副词的词汇意义是虚的,(这里暂不讨论副词的虚实归属问题,但它的词汇意义是虚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发现副词“永远”并不能找到它的实词原形,并且它从一产生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副词;在古代汉语中,我们也找不到“永远”的用例。而和“永远”意思相当的另一个单音节副词“永”却至少在春秋时代就出现了,例如:
(30)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诗经·卫风·木瓜》)
在现代汉语中,“永”还在继续使用,意义、用法跟“永远”相同,例如:
(31)只要你和我们永在一起棗看我们上补青天,下填沧海,和我们在一起生活,一起呼吸。(李瑛《难忘的一九七六》)
但使用的频率却远不及“永远”高,“永”的后面一般只能带单音节词,例如:
(32)人民的痛苦和灾难,恐怖和贫困,却像一江春水流不尽的血泪,也永逝不返了。(彭敏《长江万里话新桥》)
在一般文章里,“永”后边多跟否定形式,比较:
(33)永不掉队 ※永跟队伍前进
永不离开 ※永在一起
永不后退 ※永向前
带※的格式,换成“永远”就符合习惯了。“永远”作为一个后生的副词,应该是单音节副词“永”发展而来,是现代汉语词语双音节化的结果。
2.无论是词的语法意义还是句法功能,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定式。我们通过对“永远”动态发展过程的探索和分析发现,“永远”已经逐渐实词化,这与其它的副词是不一样的:一般副词的语义发展过程都呈现为一个由实转虚的连续统,而“永远”的语义发展过程却呈现为一个由虚渐实的连续统。也就是说它的词汇意义越来越实在,这从它充当主语、宾语、定语的用例中可以找到有力的佐证。
参考文献:
[1]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1957级语言班编《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商务印书馆,1982年.
[2]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二十三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
[3] 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古代汉语虚词》,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
[4] 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现代汉语虚词》,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
[5] 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4年.
[6] 裘荣棠《让人疑惑的“永远”》,《语文建设》1996年第12期.
[7] 裘荣棠《谈“永远”的形容词用法》,《汉语学习》1997年第4期.
[8] 王自强编著《现代汉语虚词用法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
[9] 武克忠主编《现代汉语常用虚词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
[10]袁毓林《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11]张谊生著《现代汉语副词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
[13]周洪波《“永远”的词性问题》,《语文建设》,1997年第7期.
(彭玉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