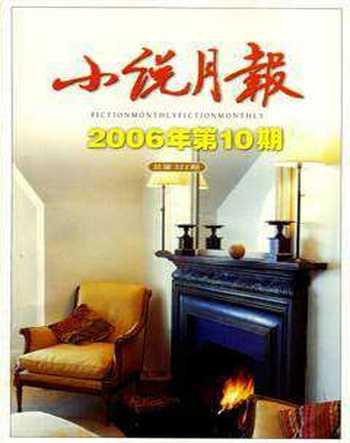接生
儿子新婚后三天,携带着他的高中同班的女同学去南方打工,甩下一句话:你们硬逼着我结婚,我就给你们一个形式,我有我的幸福追求。她什么时候愿意离婚,我回来办手续。
儿媳妇也不愿意这桩婚事,听说她也有一个相好的同学。可她温柔贤慧的性格拗不过她的爹妈,就泪流满面地进了这个家门。
结婚三年来,儿媳妇孝敬她两个老人,知热知冷,体贴得无微不至。里里外外一把手,把家里活儿安排得井井有条。谁见谁爱,谁见谁夸。可谁知她却怀孕了。儿子三年不在家,她怀的是谁的孩子呢?一气之下,她赶走了儿媳妇。
她从空荡荡的干草房里出来,穿过一排畜圈,跌跌撞撞地走到坡跟前。割光了草的坡地变成了荒坡,她像一叶孤立无援的舢板,漂在海洋一般的荒坡下,用那双失去光泽的老眼久久地打量着坡顶。离坡顶很远的山谷里,有她的老头夏天割晒下给牲畜过冬的干草,那些干草就像是她扯了线放出去的风筝,飞得高了,却拽不动线,她没能力弄回来。她老了,连走路都费劲,不可能走到山谷去运干草。看来,圈里的羊和马,这个冬天得靠空气维持生命了。
她的眼睛似两只干枯的深井,射向坡顶的天空。天空像捂着一张肮脏的羊毛毡,羊毛毡的边沿与地连在了一起,灰土土的,分不清哪是天哪儿是地。风拖着乱蓬蓬的灰云,从坡顶滚下来,眨眼之间,针尖似的雨滴扎到她的头上、身上,还有眼睛上。她连躲雨的劲都没有,任雨滴把自己身上还有脚下的土地淋洒得千疮百孔。她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仿佛呼进呼出的空气在穿透一层滞重的乌云,她半张半闭的灰白眼窝里,慢慢地起了大雾,像开水壶里的蒸汽慢慢涌泄而出,弥漫了深秋枯燥的天空,还有脚下的荒坡。
她那刚强了一辈子的老头,此刻正躺在炕上等死,初秋时的那一跤把他摔成了废物,除过那双已经不认识人的双眼每天早上还能睁开,漫无目的地落在某个地方外,连句正常的话都不会说了。不管曾经是怎样的强壮,如今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哪里经得住这一摔,躺下后再没起来。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她的天随之塌了。
现在,家里就剩下几匹马和圈里的几十只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以前,羊和马都是老头经管着去放,她和儿媳妇只顾操持一日三餐,给老头把家看好,叫他从风里雨里回来能吃上热汤饭,睡上热炕头。老头瘫痪后,儿媳妇走了,马羊没人放了,在圈里饿得叫唤声响成一片,听得她心里凄凄凉凉。开始她心里光顾伤心,还没啥反应,后来才意识到这个家里现在就剩她一个健全的人,她再也没有任何依靠。在羊群咩咩的叫声里,她抹干眼泪去打开羊圈的门,羊像云朵一样涌出来,她的心也被这些汹涌的云朵堵得结结实实。这样没有缝隙透进阳光的日子过得一天像一月,一月又像一年,漫长得她的心里都发了霉。
毛毛细雨下得真不是时候。母羊们该产羔了,她连一点准备都没有。往年,这都是老头操心的事,该怎么弄,老头一个人都会弄好,根本不需要她过问。羊是他们家最重要的财产,一直由老头掌管,她一个女人家,做些掌管财产以外的家务事,从不过问,也无心探听财产的细枝末节。
可眼下,老头以这种决绝的方式让她接管了家里的全部财产,没等她从慌手慌脚中镇静下来,还没弄清楚有多少只母羊,就到产羔期了。她不怕给母羊接羔,她是生过孩子的女人,没啥怕的。可怕的是这场连绵不绝的秋雨,下起来没完没了,草场、羊圈,到处湿漉漉的,通往塬上塬下的坡路滑得不敢走。她没有经验,应该在产羔前把远处山谷里的干草运回来,她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事呢,她本可以赶着一大群羊边放牧边套上马车往回运草,但山谷离得太远,一个来回得一整天,瘫痪在炕上的老头没人照顾,谁知道他会出什么事情。她不能扔下老头去运干草。拖了一天又一天,想不到一直拖到了雨季。现在,她弄不来一点干草,供母羊铺在身下生产。毛毛细雨使地气一天冷于一天,羊羔落在冰冷的地上,将会是什么结果。
几天前,她都在注意那些拖着大肚子的母羊,如果哪个卧下不动,她往起赶,母羊不情愿起来,两眼湿湿地望着她,咩咩地叫唤个不停,她知道它快要生了。母羊们的临产,使她眼前不断闪现出挺着大肚子的儿媳。儿媳妇也快临产了,这使她的心又疼痛起来。儿媳妇怀孕后,她的心脏开始犯病,有时疼得她想死,或者像老头那样人事不省,人世间的什么疼痛都感受不到才好。眼下,她无处逃避,面对一只只待产的母羊,她流着泪将它们一只只弄到自己住的屋子里,给它们接生。屋子要比羊圈暖和得多。可是,后来生产的母羊越来越多,窄小的屋子里根本盛不下那么多羊,她只好放弃对羊们的心疼,没黑没明地在羊圈里接羊羔。圈里又窄又小,没法把正在生产和待产的母羊分开,有时往往几只母羊一同产羔,羊羔又没暖和的地方可以放,躺靠在母羊肚子跟前冰冷的地上,瑟瑟发抖,连叫声都带有裹着寒气的颤音,听得她的心也跟着颤抖。其余的羊并不因为那些母羊们的生产和小羊羔的出世而多些自觉性,它们因为寒冷不停地拥来挤去,寻找取暖的好位置,为此踩死了小羊羔。看着刚出世不久就惨死的羊羔,她那双空洞无光的褐色眼睛像打量与她不相干的世界,目光中流露出无奈与苦闷,嘴里的上下牙发出很响的磨擦声,她紧握着两只血乎乎的手,一副无助的可怜样子。她从没经历过这些事,以前,老头子不让她参与这种场面,现在,她不知道怎样才能渡过这个难关。
要是有些干草就好了,可以把母羊和羊羔放在干草上,这样就不会侵占那些冷漠的大羊们位置了。可是老头就像是考验她似的,没等把晒好的干草拉回来就出事了,把理应由他打理的一切,连声交待都没有就一股脑儿全扔给她。这可是一副无法估量的沉重担子,她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她更没有应付眼前这个事实的经验。
她绝没想到,缺少干草的后果会这么严重。有一些刚生产过的母羊,为哺养自己的孩子,尽快下奶,吃了带雨水的湿草,竟然拉起肚子。一天过去,羊圈里到处是稀黑的稀粪,几天下来,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她提着马灯,在羊堆里穿来挤去,把那些被大羊踩死的羊羔,还有被饿死冻死的羊羔清理出圈。羊圈里臭气熏天,她的眼睛跟着这些气味始终没干过。如果不是照顾老头,她连口饭都吃不上。几天下来,瘦削的脸越发尖削起来,脸色枯干蜡黄,两眼窝深陷下去,枯井似目光都是直的,头发也白了不少,在寒风中零乱得像冬天的荒草。她看着院子里堆积的死羊羔,腿脚酥软,不管不顾地往泥水地上一坐,寒气从泥水里慢慢洇上来,穿透所有的阻挡,渗透进她的血液,她的每一寸肌肤。她无法抵挡这样的侵袭,所有的委屈全涌出喉咙,她放声大哭起来。她要用哭声化解心中的憋闷,可她的哭声没人听得到,在这个独家独户的地方显得异常寂寞,在凄风冷雨的山坡上荡来荡去,慢慢地化在雨水中,消逝了。
肿着眼睛回到屋里,她对着老头又哭开了,把满肚子的委屈湿淋淋地全抛给老头,哭诉得直到喉咙干疼,嗓子都哑了。老头连眼都没眨一下,眼神不动不摇,依旧痴痴的,脸上是没一点感情的冷漠。她把眼泪抹干,不再哭了,就是哭死,老头也不会像以前一样给她说几句安慰话的。
她开始后悔,不该将儿媳妇赶走,要是儿媳妇没离开,不能替她分担点接羔的活,起码可以和她说说话,帮她分担一些忧愁吧,她也不至于被眼前的痛苦淹没。
她快支撑不住了,她发现已经开始死母羊了。
死的第一只母羊,产下一对双胞胎,此时,双胞胎羊羔还不知道失去了母亲,它们叼住母羊干瘪的奶头吮吸着,吸不出奶水,它们的小脑袋用劲往上顶几下,继续吸。没有它们希望吸到的东西,才吐出死母羊的奶头,咩咩哀叫着,去抢别的母羊奶头,与那只母羊产的羔子顶起架来。
羊羔失去母亲,等于没了亲人,它们永远都不知道父亲是谁,就是知道了,又能怎样?它们的父亲很冷漠,根本不会顾及父子关系,来抚养自己的孩子。她不忍心看眼前的惨景,想把失去母亲的双胞胎抱回屋子里养活,她弯腰去抓那两只羊羔,它们却警惕地跑开,到别的母羊身边,发出凄惨的哀叫。她追它们,又怕踩到别的羊,绕来绕去,肮脏的粪水溅了她一脸一身。最后,那对双胞胎总算被她抓住,她已累得喘不过气来,在追抓羊羔时,内心积蓄的愤怒之情使她两眼发黑,手上用力差点把两只羊羔捏死。她恨这对拒绝她疼惜而跑来跑去的双胞胎,恨这些在她措手不及时产羔的母羊,恨躺在床上没有知觉地撇开尘世烦恼的老头,恨身在她家肚子里却怀着别人种的儿媳妇,更恨丢下媳妇去城里打工,一去三年不回家的儿子。想起儿子,她的怒气更像烈烈燃烧的大火,想扑都扑不灭。追根溯源,家里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因儿子而起,如果不是他三年不回家,儿媳妇又怎会耐不住寂寞怀上不知谁的男人下的种?
刚开始发现儿媳妇不对劲,她给老头说时,老头反而埋怨她,说她好歹是做婆婆的,儿媳妇就跟自己的闺女一样,哪有自己的妈乱猜疑自己孩子的。
儿媳妇是个规矩的牧人家女儿,嫁过来后对公婆一直很孝顺,尤其是对婆婆言听计从,从来没惹她生过气。她相信儿媳妇是个好女人,但她没有乱猜疑,她生过儿子,还生过一个女儿,是过来人,对女人怀孕有些经验。种种迹象表明,儿媳妇怀了身孕,可老头就是不相信她的话,只埋怨儿子三年都不回家,是个没心没肺的白眼狼,生了这样的儿子,委屈了这么孝顺的儿媳妇。
不久,儿媳妇的肚子明显鼓了起来,连瞎子都能看出,他们的儿媳妇怀有身孕。老头这下慌了,叫她去问儿媳妇,儿子不在家三年了,她的肚子到底是咋回事。
还能是咋回事,肯定是别的男人下的野种,这是明摆着的,她的儿子结婚不久就离家打工,一去三年不回,儿媳妇怀的不是野种是什么!
她尽量控制住愤怒,找个机会心平气和地和儿媳妇谈论肚子的问题。她都觉得太难为情,不好直接开口,用另外一种方式问儿媳妇,是不是生了啥怪病,肚子咋不对劲。
没想到儿媳妇一点都不掩饰,说她怀孕了。
儿媳妇坦然的态度,似突如其来的一记耳光,打得她半天回不过神来,她结巴了半天,才问,你——咋——怀——上——的?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该不会说你怀了三年孕吧。
儿媳妇镇定地说:我进这门,原准备牺牲我的爱情、幸福,过一个平常人的日子,服侍二老,安度晚年,相夫教子,终其一生。过来后,才知道你儿子也不愿意这桩婚事,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出走。我非常痛苦,忍辱负重地饮泪度日。我在进这个家门半年后就给你儿子写信打电话,叫他回来办离婚手续,他说:他负责工作的那个部门事情多,业务忙,老板一时三刻不准假,一拖三拖,一年半时间过去。去年腊月,他准备回来,在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这件事后,我初中阶段的一个同学走进了我的生活。他很爱我,我也很爱他。我结婚三年了,他一直没有结婚。
儿媳妇说得很平静。她软瘫在地,脸色蜡黄,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连连说:罪孽!罪孽呀!
儿媳妇突然止住哭声,扑通一下给她跪在地上说:你老人家和我爸想好,你们能容得下这孩子,我和这孩子他爸结婚,这孩子他爸就是你们的上门女婿,我们俩人尽心尽力把你们俩人养老送终。你们容不下我和这孩子,我走。
她倚着门,半躺在地上,挥了挥手,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你走。
儿媳妇把她扶好,轻轻地闭上门走了。
那道把她和儿媳妇隔开的门好像落进了她的心里,把她的心隔成了两半,一半是伤心的碎片,另一半是愤怒的碎片。从此,她就像做了一个黑暗的梦,身不由己,在梦的笼罩下,她呼吸不畅,好像雷阵雨前的天气似的,阴沉,憋闷。
不能让这个怀着别人孩子的人在自己家里生活。她把这事和儿子的死一并告诉给老头儿,老头儿一下子垮了。他的脸阴沉得像块浸透了污水的抹布,随时都能拧出脏水来。他心里的痛苦没法说出来,就借酒浇愁,有次,他割草时喝多了,失足摔下山谷,以一种决然的方式将自己从愁闷中解脱出来,变成永远不知道痛苦为何物的事外之人,却把一切屈辱和艰辛留给了年过半百的老伴。她能忍受贫穷、苦难,却承受不了屈辱。老头失去当家做主的权力,她横下心将儿媳妇赶出家门。
儿媳妇要犟就犟到底,她没回娘家,也没去找肚里孩子的父亲,一个人挺着日渐突起的大肚子,住在坡下一间别人废弃的羊房里。
毛毛雨下到后来,变得越来越冷,深秋的寒意被冬天的冷峭彻底替代了。寒流堂而皇之地到来。第一场雪悄悄落下,带来寒雾,把山坡、沟谷、羊肠似的小道全部吞没,没有了天,也没有了地,只有寒冷,匕首一样尖锐的寒冷。
她惶惶不安地在又臭又冷的羊圈里又忙碌了一天又一夜,一双老花眼被臭气熏得睁不开,她寻了两根细草秸,湿了唾液沾在上下眼皮之间,即使这样,还是觉得眼神越来越模糊。她到羊圈外头抓了两把雪沫往脸上搓,强烈的寒冷使她重新打起精神。回到羊圈,挂在柱子上的马灯,散发着昏黄而温暖的光,可她的心被外面的雪侵占了,这淡而散的温暖无法驱散她透心的凉意。她真想让自己就这样倒下去,哪怕像老头子一样躺着痴着傻着,这辈子再也没有了烦恼。她原来认为的幸福就是蓝天、艳阳,她站在草坡下等待黄昏染红草坡时,老头子赶着羊群归来。可现在周围一片黑暗,她所做的一切可能徒劳无益,在这一群羊面前,她无路可退,在自己这个惨淡的家面前,她毫无选择。
昏暗的马灯照着母羊们的脸,它们或微闭着两眼昏迷,或已经接近死亡。她拖着两条浮肿的腿勉强支撑着身体,像个醉鬼,一瘸一拐地穿行在浑身打颤的母羊之间,两只手麻木得几乎不听使唤,剪刀在她手里像条活蹦乱跳的鱼,不能利索地剪断母羊与羊羔相连的脐带,她看到一只母羊被脐带拽得痛不欲生,像她自己身体里有一根带子拽着似的,她咝咝地吸着气,丢开剪刀用牙咬脐带。她的牙还算整齐,咬得满嘴腥气,终于咬断脐带,解除了母羊的痛苦。母羊们生产的惨叫声,慢慢幻化成女人生孩子时的呻吟。她的耳朵里灌满了这个久违的声音,似乎看到正在生孩子的儿媳妇疼得大喊大叫,痛苦得扭曲的脸。她的心颤抖了,咬不动脐带了,她的牙失去了锐利,像剪刀一样钝了、锈了,张开了就合不上,大张着嘴却无能为力。她像刚生完羊羔的母羊一样,身体虚弱,缺乏力气。她的牙还是锐利的,她的目光却痴呆,在劳累中分不清白天黑夜,有时,她能在一瞬间进入梦乡,无论是正在接羔,还是收拾死去的母羊,她的大脑会一片空白,对什么都没了感觉。在她用尽一切能用的办法,就是挽救不了那些可怜的生命时,看着一只只羊羔或母羊死去,刚开始的那种疼痛慢慢地淡化了。有时,她竟然会昏睡一小会,很快,她会被羊的哀叫声惊醒,或从羊圈外冲进的凉气把她刺醒,醒来的时候,她一眼看到的是面前母羊的肚子,奇怪地,她脑子里会闪现儿媳妇挺着的大肚子。天气越来越冷,一个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的女人,在那个废弃的羊房里该怎样生活?这个念头一闪,她吃了惊,随即赶紧收回纷乱的心思,继续忙碌眼前的活,羊们都在等着她接羔呢,她不敢分心。有些事一旦想起来就很难驱除,每接一只羊羔出来,儿媳妇鼓突的肚子就会奔出来在她眼前晃动,直晃得她心慌手软。这个时候,她还是忍不住放慢手脚,向羊圈外张望一眼,其实什么也看不到,儿媳妇住的废羊房离这里还很远呢。
她抱回屋的那对双胞胎羊羔,最终还是辜负了她的怜惜,死了。它们吃不到母亲的奶,她给烧了些面糊糊,饥饿使它们勉强吃了一些,不久,先是其中的一个开始拉肚子,像它的母亲一样,拉得遍地都是稀屎,接着,另一只也开始拉了。它们本来就体质虚弱,不到一天时间,就躺下走不动了。
偶尔,她回屋给老头做饭,看到这对小羊羔的情形,心里酸酸的,这两个没有母亲的孩子,飘渺的眼神落在她身上,细弱的哀叫声轻风一样若有若无。尽管这几天她看惯了羊们的生死,心已钝得几近麻木,可面前这两对哀怨的眼神使她终于没能忍住眼泪的喷涌。她把虚弱的它们抱在怀里,像抱着两个幼小的孩子,边烧火,边流泪,边抚摸梳理它们身上的脏毛。
她很累,手还在下意识地梳理羊毛,感觉却飘忽起来,身体摆脱了疲累变得轻松起来,慢慢地,一切都与她无关了。雪不下了,寒流消失了,温暖的风从坡下吹来,染绿了坡顶,顺着开阔的草坡看上去,她看到辽阔湛蓝的天,洁白柔和的云,她感到了温暖,心情舒畅起来。怀里抱着的小羊羔软乎乎的,她低头一看,哪里是小羊羔,分明是一个光着身子的孩子在她怀里乱拱,伸展着手脚哭叫。她被小孩的哭叫声吸引着,这是多么诱人的情景啊!是她的孙子吧?!她感到身上增添了某种勇气,有种看不见的东西注入她的身体里,使她有了使不完的力气。她睁开那双无神、滞呆、枯叶般干涩的眼睛,看到人世间的一缕温暖。她爬起来,“咚咚”脚步有力地向外走去,向湿滑的坡下走去。寒冷算什么?泥泞算什么?她要去坡下那间废弃的羊房,把儿媳妇接回来,她要亲手将自己的孙子接到这个世界上来。
原刊责编常智奇
【作者简介】温亚军,男,陕西岐山人,1967年生,1985年入伍至今,曾在新疆服役16年。著有长篇小说《伪生活》、《无岸之海》、《鸽子飞过天空》等五部,小说集《寻找大舅》、《硬雪》、《燃烧的马》等,有作品被翻译成日、波兰文。其短篇小说《驮水的日子》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本刊曾选发过其中篇小说《苦水塔尔拉》、《生物带》等。现为中国武警杂志社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