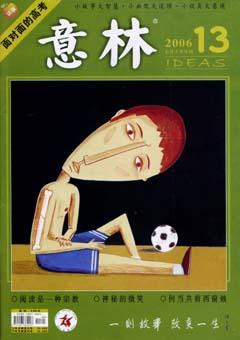楼梯上的扶手
爱德华·齐格勒
译/任晓林
我的腿跛得厉害起来,上下楼梯拉扶手使的劲越来越大,走楼梯、跨台阶、去溪边也越来越不利落。从我三岁那年得了病留下后遗症后,我这两条病弱的腿就成了我的伙伴。如今我四十五岁了。
我的儿子麦修具备所有我所缺乏的自信。他今年十七岁,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体格健壮。我不在场时他常常口若悬河地显示他的口才,但我们在一起时,他却有点像粗犷而口讷的运动员。他是个活跃的曲棍球运动员,还是个抓鱼能手。
我们有过几次不快,但除了火头上的交锋,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
他一天天长大,而我却一天天衰弱。看着晃晃荡荡的楼梯扶手,我的担心与日俱增,修扶手已不能再等了。我去请过几个木工,可谁也不想来干这点活。我走楼梯更小心谨慎了。
我虽然跛,不过在晴朗的夜晚我还能搬着我那老式的望远镜爬上松林边的小山,把望远镜放在三角架上,寻找新的球状星云和双星。
麦特(麦修的爱称)常来帮我架望远镜,有时他会留下来。也是在这样一个夜晚,他又要我讲他和天狼星——那颗天空中最亮的星之间的故事。
西瑞依斯(天狼星)是麦特的中间名字,是为纪念他出生在蓝白的天狼星和壮观的猎户座星光下而起的。麦特就是在这座小山下面的小松林里出生的。
那天他母亲沙莉是半夜以后醒过来的。因为是第二胎(当时两岁的安德鲁正睡在他的童床上),她很冷静地按经验估计新生命大约还得过几个小时才会降生。
那时我还没醒,对于将要在我身边发生的戏剧性事件毫不知晓,是她用变了调的尖声叫醒了我:“快起来,孩子就要降生了!”
那时我的腿比现在灵便,我跳起来穿上衣服,抓了车钥匙就冲下楼去。沙莉已经给医生打了电话,又叫了一个邻居来照看安德鲁。
等那邻居来了以后,沙莉和我就去开车。我们那辆月白色的老福特停在50英尺外的松林旁边。我坐在方向盘后面,“上车吧,沙莉,我们走。”我说。她还在犹豫。
“我……我不能坐了。”
“你怎么了?”
“婴儿的头就要生出来了……你最好还是过来接着吧!”
这时沙莉已经爬上了前座。
“你快过来呀!”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充满了惊恐和紧张的声音。
在这秋夜的星光下,我过去接住了婴儿。这个小小的且有着体温的小东西还没有完全生出来,就发出响亮的哭声。我右手托着他的脑袋,左手托着后背,惊奇地看着那个圆润光滑的肚子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能哭会喊的婴儿。
我小心翼翼地提着婴儿的脚后跟,托着婴儿的头,借着星光我看到小身体上那个小雀雀正对着我。“是个男孩!”我喊了起来,热血涌遍了全身。
接着我把他递给了他母亲,给他们披上了大衣。一会儿救护车到了,医护人员接替了我。忙乱之中我的汽车钥匙丢了——失落在这个夜晚,这片松林,这腔兴奋之中。
这就是婴儿在洗礼时被命名为麦修·西瑞依斯的缘由——因为他降生到我的双手中时,天狼星正在我的头顶上照耀着。
麦特为他的中间名苦恼了好多年。当他长到能忍受别人的取笑时,他已经为他取了天上最亮的星星的名字而高兴了。
有天晚上,我工作完后正准备攀扶着楼梯上楼去休息时,发现扶手不晃了。“沙莉,”我喊道,“你知道这扶手修好了吗?”
“对,你去问问麦特。”
麦特回来后,说扶手是他修的。
“那我该为你做什么呢?”
“不用,你已经为我做过了。” “做过了,怎么会呢?”
“你知道,我降生在你的双手里,使我没落在地上。所以我想我该报答你。”
接着是一阵沉默。在沉默中有一种强烈的感情在我们之间流动,这种流动虽然看不见又听不见,但却能被我的心,我的骨髓所知觉,所感动。
今天离这故事发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年。楼梯扶手依然牢固。天狼星也仍然在松林上升起——秋天里晚些,冬天里早些,春天里更早。而我每次看到它,心里就充满谢意。
(野风摘自《黎明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