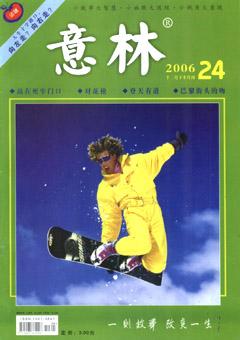美妙的瞬间
詹尼弗·安德森
译/胡英
鳐鱼是我最喜爱的动物之一,但人类对它们知之甚少。鳐鱼以浮游生物为食,不适于人工豢养。它们徜徉在广阔的海洋里,如谜一般神秘莫测。
鳐鱼腹部有独特的图案,每条鱼的图案独一无二、决不重复,因而可以此辨识它们。1992年,我一直在辨认摩罗开尼岛出没的鳐鱼,有几条已经熟识,但大多数仅有一面之缘,就再没看到过。
此刻,一条非常大的美丽鳐鱼正在我下方。我开始透过呼吸调节器呼叫:“嗨,上来,我在这儿!”过去我曾用这种方法吸引鲸鱼和海豚的注意,这些小精灵在水下十分“健谈”,有时为了探寻声音的究竟,它们真会游过来。
我不停呼叫这条鳐鱼,当看到她在水中挪了位置,我便判定她产生好奇了。于是我开始挥动双臂,招呼她游上来。
过了片刻,她抬身离开了原先漂乘的水流,兜了很大一个圈,慢慢游近了我。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缓慢地往复,越升越高,直到我正下方。
我发觉她比我们以往在摩罗开尼岛周围见过的鳐鱼大得多,两端翅尖相距足有十五英尺。这条鳐鱼我过去从未见过。我总感觉她还有别的异样,却说不出是什么。
当我的大脑恢复运转,能够集中精力时,我看到她背部有一道很深的V字形伤痕,上面的肌肉全没了,此外还有多处伤痕,遍布全身上下。我第一反应是她遭遇了渔船袭击。但当她游得更近,距我们仅十英尺远时,我才发现问题所在。
几只鱼钩从眼部嵌进了她的头里,一根极粗的渔线直扯到了尾部。她带着这根渔线翻滚,结果被从头到尾缠了五六圈。渔线从她背部撕开道道裂口,嵌进身体,那些V字形的大块肌肉就是这样被挖去的。
我感到一阵恶心,甚至有片刻不能动弹。我知道痛苦煎熬中的野生动物决不容人再来伤口撒盐。但我必须采取些行动。
忘了还背着氧气瓶,也忘了自己身在何处,我朝这条鳐鱼游了过去。我游得很慢,始终不停地对她讲话,仿佛她是我从小养大的一匹马。当我伸手触到她时,她全身颤抖起来,就像我的马那样。我将双手放在她身上,然后整个身子贴了上去,始终不停地对她讲话。我知道她随时可能挥起巨翅将我击倒。
等她平静下来,我取出带在呼吸管上的小刀,扯住一根渔线。渔线绷得很紧,简直像吉他弦线,我的指头很难伸到线下面。她又颤抖起来,这提醒我要轻柔些。显然,一丁点儿外力都会令她痛苦不堪。
我割断第一根渔线时,渔线勒进了她的伤口。她猛地挥了一下有力的双翅,将我抛下来,刷地游走了。我以为她就这样走了,所以当她转身径直朝我游来,又回到我身下时,我吃了一惊。我继续开始工作。她似乎知道这会很疼,似乎又知道我能帮她。想想这生灵竟有如此智慧:懂得求助,又懂得信任!
我割断一根渔线,再去割另一根,当她忍受不住时就会游开,只为喘息片刻后再回来。我从不追赶她,也从不强制她,我给她行动的自由,而她每次总会自己回来。
当顶部所有的渔线都割断后,在她再次离开时,我钻到她身下,去拉那些从她背部伤口穿过的渔线。渔线周围的组织已经开始长起来,使得这些线很难松开。我用一只手扶住她的下颌,身子抵在她身体上。
她尽力保持静止不动。所有的渔线都松开后,我放开她,看着她在水里打了个圈。她本来可以走了,渔线会统统脱落。但她又回来了。
鱼钩还在她身体里面。一只刚悬了个边儿,很轻易就拿掉了。另一只埋在她眼旁,倒钩扎进去至少二英寸。我开始小心翼翼地取出鱼钩,尽量不伤着任何地方。她一开一合地眨着眼睛配合我,终于,鱼钩取出来了。我将重心放在鳐鱼身上,一手握着鱼钩,另一只手收拢那些渔线。
我本该永远留在那儿的!那一刻,我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爱这只鳐鱼。她令我如此感动,竟允许我为她做这一切。但现实无情地将我唤醒。氧气一点点耗尽,我极不情愿地回过神来,强迫自己离开。
起初,她还待在我身下。接着,当她意识到她自由了,便一下子恢复了活力,那股劲头是我怎么也想像不到的。
我以为她又病又弱:她的嘴被渔线绞住了,那些线一刻不拿掉,她就一刻不能进食。但我错了!她伸展她那强劲有力的双翅,用力挥打两下,沿着摩罗开尼岛的挡波堤扶摇直上,径直奔人大海,消失在我的视线之中!
此前的一切都令人惊异,但我还能说清。此刻的瞬间却变得如梦般奇幻了。
我转过身,看到她缓缓向我游来。她几乎毫不费力地挨近我,停了下来,她的翅膀刚好触到我的头。我凝视她那又圆又黑的眼睛,她也深情地望着我。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激流涌遍了全身,只觉得那是一股温暖和友爱的能量,从她那里流进了我心里。
她就那样和我待了片刻。我分不清那是一秒钟还是一小时。然后,就像她刚才回来时那般美妙,她抬起搁在我头顶的翅膀,离开了。一个鳐鱼式的感谢。我做了个蹩脚的“安全停留”,悬在水中,试图弄明白这一切。
遗憾的是自那天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我仍在寻找。我的潜水衣从未这么久不曾更换,虽已破旧不堪,我却舍不得换掉,我怕她会认不出我。我呼唤见到的每一条鳐鱼,它们差不多总会这样那样地跟我打招呼。但总有一天,那会是她。如果她听到我的呼唤,她会停下身,当她记起那个她曾交托自己、替她解除痛苦的人,她会朝我游过来。
至少,这在我的梦境中曾经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