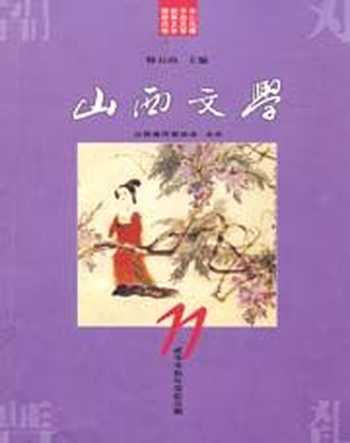下乡纪事
石 愚
1975年秋天,我到沈庄下乡,正式的说法,是参加了县委驻沈庄批林批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此时文化大革命已是强弩之末,农业学大寨口号虽然越喊越响,却只能是虚张声势,真正能落实的,也就干部下乡一条,叫做“农业要大上,干部要大下”。也是的,物资匮乏,资金拮据,化肥农药奇货可居,拖拉机按计划分配,全县每年也就七八台,能落实的,就是干部下乡了。那时县干部的人数不及现在的三分之一,也已经人浮于事了。对县领导来说,把身边多余的人打发下去,既图个清净,汇报工作时,也可以扎扎实实来一段“一年来,我们狠抓干部蹲点,全县半数以上大队派驻了宣传队”之类的话。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宣传队进村的时间是在秋收以后,人员是“乱搭班子”,不算来自五湖四海,也可谓是士农工商五花八门。我们宣传队共六个人,队长谷子秋,县革委水利办公室副主任,五十上下年纪;副队长老刘,土产公司副主任(当时不称经理),四十出头;队员除了我,还有文化馆的下放干部梁之音,县水泥厂的女技术员吴金果,借干李小串。借干,是“借调干部”之意,不是借自什么单位,而是借自农村,相当于干部中的临时工。四清时有过一批借干,后来都转了正。这批借干听说也是很有希望转正的。
宣传队进村,烧了三把火:访贫问苦,摸清底子;批判斗争,打击敌人;壮大队伍,健全班子。忙过一阵子,就过年了,然后就无所事事了。按说没事干,就可以尽情享受田园风光,岂不美哉?实则不然。最大的问题是吃饭。既然下乡,就要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所谓同住,并不是和贫下中农睡一条炕,而是随便拣一家有空房的农户住下就行;所谓同劳动,也不过是每天到地里转转,高兴了再指手画脚说几句,用不着真干的。真正不得不实行的是同吃这一条,就是和农家同吃一锅饭——当然是派饭,从村头吃到村尾,一家一户挨门吃,周而复始。
对吃派饭最感兴趣的是小串。她在村里长大,从小看着大人们诚惶诚恐地招待干部吃饭,现在自己骤然间也成了被招待的对象,自然兴奋。她只是说这村的饭差,远不及她家管干部的饭好。副队长老刘哑然而笑,问:你家管饭是啥时候?小串说是四清时候。老刘说这不就对了,那时候是啥时候,现在是啥时候?咱们这个宣传队又咋能和四清工作队比呢?人家是正规军。我问:那咱们是什么军?老刘说:你这大学生,还得好好深入实际咧!这还用问?杂牌军嘛!大家先是笑,接着沉默。
对吃派饭最头疼的是梁之音。老梁是下放干部,原是省歌舞团的小提琴手。他属于1969年那批下放干部,刚下来时和插队知青一样,安插在各村当农民。老梁当了一年社员,就安排到文化馆,待遇已算优厚。他是南方人,说一口鸭鸣似的南方话,群众听不懂,而当地方言他也听不大懂,于是只好少说话,面对群众则常常不说话。这还罢了,最糟糕的是他那一副小提琴家的派头,总是高昂着头,目不斜视,似乎永远地坐在舞台上演奏;和人说话,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别说群众,宣传队的人对他也敬而远之。我算例外,同是知识分子的缘故吧,喜欢和老梁拉拉家常。我也怕吃派饭,主要是怕吃那玉米面发糕,俗称“四面挨刀”的那种食品。以我的记忆,这种食品实在是七十年代才开始流行,取代了原先家家户户笼里都有的白面馒头。八十年代后这种“四面挨刀”才终于消失。
老梁是南方人,本来连馒头也吃不惯的,这阵叫他吃那种纯玉米面的发糕,已是苦不堪言,问题是有时连这也吃不上,得挨饿。原来,宣传队六个人分作三组吃派饭,两人一组,老梁和吴金果一组。吴金果是邻村的人,在沈庄有好几家亲戚,这且不说;她男人是公社供销社的主任,那是人人巴结的角色,她因而也很受欢迎,不论到谁家,饭菜都差不到哪里去。可惜吴金果总有这样那样的借口回家,同样因为丈夫的原因,队长谷子秋对此网开一面。这就苦了老梁,管饭的人家都合谋刁难他。按规矩,谁家管饭,饭熟后便打发孩子去叫,若吴金果在,肯定如此;但若只老梁一人时,那就糟了,决不会有人叫的。老梁这么着被饿了几次,学乖了,就主动上门;也不行,那饭总是迟迟做不好。有一回我和小串吃完了,见老梁还一个人在村巷里游荡,问他:饭还没熟吗?老梁回答:老太婆说才死(柴湿),正生火呢!依然文质彬彬,不慌不忙。小串偷着笑,我也笑笑,到底不知道老梁那顿饭吃了没有,咋吃的。小串和吴金果住一起,了解的情报多。她听吴金果说,村里人都讨厌老梁,说那个“挨刀鬼”一顿饭不说一句话,活该饿死!我很想婉转地劝劝老梁,请他活泛些,可到底没想出什么合适的措辞来。
伙食最好的是谷子秋。他是水利办的头头,大队想打深井,几万元的资金,全指望他通融。凡是他吃到的人家,大队每天补助小麦二斤。老谷天天吃香喝辣,大家都想跟他吃饭,哪怕只吃一顿,也可略略滋润一下肠胃,他却把这个紧俏“指标”派给了老刘。大家只好看着二位领导油汪汪的嘴唇、红润的面容,无可奈何。
下乡的另一个苦处是无聊。班子建立之后,大队的一应事务自有大队小队的干部负责,宣传队则如聋子的耳朵,是摆设了。谷子秋还在机关里管点什么事情,老刘总是这儿那儿不舒服,他们常常回家或者回机关。吴金果不用说了。坚守岗位的,就我和老梁、小串三个人。老梁的老婆孩子在太原,我那时虽然已结婚,但爱人在外地,都无处躲藏。回机关躲清闲是不行的,每月领工资、粮票回去一下,呆两天就得走,不然,会遭白眼的。机关的人对待派下去的同事视同异类,希望他们永远也别回来,以免这苦差事轮到自己。这一点,我和老梁有同感。小串是借干,要好好表现。她家里也常常有事,有事时总是打发她表哥来叫她。她表哥四十多岁,瘸子,见了人怯怯的,据说是大队保健站的医生。小串回家不多停,少则一天,多则两天,就归队了。
宣传队住在一条巷子里,男一家,女一家,两家斜对门。小串和吴金果住的那家就一个老太婆,老太婆有三个儿子,都在西安工作,常年不回家。小串一个人寂寞,就到我们这边聊闲天。也幸亏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陪着,我们才不至于太寂寞。小串长得漂亮,青竹般的高挑身段,水汪汪一双大眼,永远也晒不黑的白嫩的脸,一举一动都带有农村姑娘特有的韵味。老梁在背后不只一次说:小串这姑娘,文化再高些,能做电影演员。我问:比你老婆怎样?老梁想了想说:模样强一些,气质不如。我老婆是音乐学院毕业,能歌善舞。说毕,无限相思的样子。我却在心中颇不礼貌地暗想:他老婆一定后悔,嫁了这么个窝囊丈夫。
小串也能歌善舞,尤其喜欢唱歌。流行的歌曲她几乎都会唱,还会唱许多样板戏的段子,蒲剧眉户都行,只不会京剧。广播上有什么新歌,她听两遍就能唱了,而且唱得声情并茂。有一次,老梁考试性地教她唱了几句外国歌,居然也唱得有滋有味,高的能高上去,低的能低下来,音色也很美。老梁惊异道:考音乐学院也差不多啊!好好训练几年,赛过郭兰英!小串说: 那你训练我吧!老梁说:我本来是学声乐的,嗓子练坏了,只好改器乐。我是半瓶醋,把你教坏了,还不如不教。再说,那得天天起大早拔嗓子,在这地方行吗?我闷的时候想拉拉琴,也不好意思啊!我看你呀,倒不如跟张老师学点文化最实用。张老师是中文系毕业,文学家。老梁说着,抖动着脚尖。
老梁虽然不善交际,但我早看出来了,这家伙的头脑是一流的,别看那一副窝囊样子,其实是在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呢。小串已订婚,对象是军人,按流行的说法,要算“军管单位”,不但冲击不得,套近乎也使不得。我看老梁十有八九也是怕自己把持不住,英雄难过美人关嘛,所以把球踢给了我。当然,这也可能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为我碰到小串的目光就心慌,从不敢和她单独相处,尽力回避她的目光。
小串是“七制校”毕业,实际就是小学毕业,据她说他们村里从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我们是她第一次见到的大学生,她对我们俩不但是尊敬,实在是敬仰。她很希望能跟我们学点什么,老梁先叫她吃了闭门羹,她有些失望,便转过脸看我,那目光可怜兮兮,又那样满怀渴望。我这个人心软,一时实在不忍心,便打趣道:老梁他不教你唱歌,是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架子,你别理他那套,他要真不教你,咱们就发动群众斗争他。至于学文化,不论是语文数学,还是物理化学,你学到哪里,我教到哪里。小串好高兴,跳起来拍手道:张老师你说话可要算数,明天就开始!
现成的教材是一套毛选。刚开始是她把书拿过来请教,因为我们在一起吃饭,回来时相跟着,她便邀请我到她的宿舍去。我谢绝过两次,她还是邀请,只好从命。她的宿舍收拾得一尘不染,贴着几张宣传画,简陋的房子显得很宜人。我第一次坐在她的板凳上,止不住心跳。小串说:你这贵客好难请啊!你大学生,比我还封建哩。不知为什么,有人在的时候我总不好意思提问题,听不懂也不好意思问。你再给我讲一讲好吗?她又拿出毛选,一连提了好几个问题,我一一做解释。我发现她悟性很好,讲过的东西,便再不用说第二遍,临走时情不自禁赞扬了她几句。小串满面流溢出光彩来。从此我常到小串住处,吴金果在时也去。和这样美丽的姑娘在一起真是如沐春风。小串很自重,我在时总是大开着屋门,一言一笑都很谨慎,轻易不看我一眼,反不及有人时随便。我心里不免笑话自己当初神经过敏。
小串对老梁拒绝教她唱歌,一直觉得遗憾,不止一次撺掇我做老梁的工作。我想何必郑重其事地拜师,直接叫他教不就得了。这天吃完晚饭,回到我的住处,等老梁回来。等了足有一小时,老梁才灰溜溜无精打采进门,看样子又有一顿饭落空了。果然,他一声不吭拿出几块饼干嚼起来。这使我们俩都挺尴尬,又有点幸灾乐祸。小串说:梁老师,明天你到五队吃饭,我到三队去。老梁不吭声。其实类似的建议我也提过,老梁说谢谢老弟,不必了。他吃罢饼干,喝一杯水,叹口气,打开他随身带的皮箱,取出一把小提琴,正正音,拉了起来。
老梁居然带着一把小提琴,这可是我们没料到的。后来我才知道,那把提琴不但是名牌,而且是祖传,他带着它,就如带着别的什么珍宝一样,是不轻易示人的,这次实在是因为情绪低落,才豁了出来。他拉的曲子是马思聪的《思乡曲》,我在高中时听过。马思聪逃到国外,这名曲早成了令人生畏的反革命歌曲。他竟然敢拉,我暗暗称奇,假装不懂。我得承认,那是我这么多年听到的最动人的乐曲。一把小提琴,能发出那么震人心魄的声音,实在是我料不到的。那么幽婉悲哀,叫人听着想哭。
也是老梁否极泰来,可巧大队书记老井来找谷子秋,听到了老梁演奏。老井是转业军人,在部队是文艺兵,复员后一直是村里“自乐班子”(俗称家戏)的台柱演员,在《红灯记》里扮演李玉和,板胡二胡也都拿得出去。公社布置要检查大寨田建设,他来看看谷子秋来了没有,走进院子,看见房东老两口雕塑般站在当院默默流泪,以为出了什么事,正要走上去问,听到了老梁的提琴演奏,才明白过来,于是也静静站着听,不久也流出泪来。待老梁拉完琴,老井走进屋子,握住老梁的手,半日无语,最后说:老梁,你这样的人材住在我们这里,真委屈你了!老梁依然无语,默默地把提琴收拾了,叹口气。
第二天中午,老梁正愁着没饭吃,老井来了,请他吃饭,连带着把我和小串也叫上了。到了老井家里,饭桌上已摆好了酒菜,看得我心花怒放。老梁那鸭嗓子先惊叫起来:啊哟,井苏 (书)记,你你你……老井拉老梁坐下,说道:老梁啊,这饭可不是白请的,是拜师宴,不成敬意。又指指我和小串说:他们二位是我拜师的证人。老梁灰暗的脸上顿时泛起光彩,谦虚几句,就狼吞虎咽起来。从那天起,老梁的境遇突然改变,顿顿吃饭有人叫了,而且饭菜质量大为改观。原来老井提高了老梁的待遇,按谷子秋的标准,所到之家补助麦子二斤,又特意吩咐,凡管饭人家必须提前恭请,按时按质管好,否则扣除口粮小麦二至五斤。这好伙食真是立竿见影,不几天老梁的面色便红润起来,人也眼见着胖了起来,越发像个提琴家了。只剩下我和小串依旧吃着玉米面发糕,心里叫苦,却又无话可讲。老梁从不请我们跟他吃饭,连句客气话也没说过。
老井拜老梁为师,是真干,不过不是学提琴,是学二胡。他说提琴他学不来,学会了也没用。老梁说二胡他外行。老井说会推磨就会推碾子,还不一样?果然老梁拉起二胡来也是不同凡响,一曲《草原轻骑兵》,把大家都震住了,都说和广播上放的一个样。老梁说老井的二胡用料不好,做工粗糙,他有一把,白放着,叫老婆邮过来;于是写信,不几天连琴带盒子都邮来了。那二胡果然出色,音质优美而且洪亮。于是二人交换了二胡,每天都要吱吱哑哑拉一阵子。老井是大队书记,从来不用上地干活,清闲得很,这下算有事干了。
老梁从此成了红人,每次大队开会,全村人都要欢呼着要他来段二胡曲子,谁家有红白喜事,也都要把他请去演奏一番。老梁一概不拒绝,每次演奏都一丝不苟,很投入地眯着眼,摇晃着身子,如醉如痴。小串学歌的意愿就此完结,只好一门心思跟我学文化。
小串学习进步很快,两个月下来,一部毛选能通读一半了。过了五一,地里的麦子一天一个样,眼看着染上了淡淡的柳黄色,小串家里的事情也多起来,她那瘸子表哥隔三差五地叫她,总有这样那样的事。小串回去两次,就再也不回去了,她说她妈讨厌,芝麻大事也叫她,一点不体谅她,说着竟哭起来。她有了什么心事,常常一个人发呆,学习时注意力不集中,答非所问。
夏收就要开始了,照惯例,县里要开宣判会,公社要开斗争会,大队要开批判会,沈庄自然不例外。这天晚上,大队召开夏收批判动员大会,先是老梁的二胡演奏,接着小串唱歌(宣传队真成了宣传队),大队和宣传队的头头们一人一段讲话;开完会,就十一点半了。群众散了,又开大小队全体干部会。谷子秋先讲话,刚讲了几分钟,就见大队的老贫协慌慌张张来报告,说不好了,出事了。老井忙问什么事?老贫协说,有人在工作队门口用石灰撒记号,很像是特务的暗号。大家一听,忙去看。果然如老贫协所说,小串住的院门口有一个石灰撒的圆圈。大家都惊呆了。谷子秋说:像特务!保护现场,快给县保卫组打电话!老井就一路小跑去了大队部。
不大一会,老井过来了,把谷子秋叫到一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便胸有成竹地开始部署。老井这人表面上像个马大哈,其实很缜密,他说是根据公社治安员的指示,我想是他在这几分钟里拿定的主意。他叫村干部们都回家,没有通知不许出门;又叫宣传队人员除老谷老刘外全部集中到大队部,也不要出来,很明显,他要限制的是小串;然后他和老谷带领七八个民兵埋伏在小串住的院子里,老刘带几个人埋伏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真是神机妙算,一切安排就绪,才过了半个小时,就有一个黑影翻墙跳进了小串的院子。众民兵一拥而上,把那跳墙的家伙制服,捆了起来,拉进屋子里。雪亮的电灯下,大家看那人时,不由大吃一惊,原来竟是小串的那位瘸子表哥!
坏人刚抓住,县保卫组的人和公社的治安员也都来了。锃亮的手铐一上,瘸子浑身打颤,该招的都招了。原来,这个比小串大二十多岁的瘸子,竟是小串的情夫!
这瘸子名叫殷天泉,霸占小串有三年了,因为是瘸子,四十多岁仍是光棍一条。他伯父是大队书记,安排他做了大队的赤脚医生,在村里就算是有头有脸了。他瞅准了小串,把她抽调到保健站做他的助手。对小串来说,这活儿轻松体面,工分也不少挣,求之不得,当然很感激。但感激归感激,要小串接受一个四十多岁的瘸子,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三年前一个夏日的上午,殷天泉偷偷反锁了大门,狼一样突然扑上去,强奸了小串。小串哭着回到家里,一连两天没去保健站,但也不好意思把事情告诉母亲。两天后殷天泉来到小串家唤小串上班。小串母亲诉说:这女子不知咋啦,不想上你那里去了。殷天泉说:好婶子,我教她配药,配得不对,我说了几句,她扭头就走了。小串母亲就骂:如今的孩子真没礼性,不知好歹!逼着小串马上跟着殷天泉走。小串只得从命。进了保健站,殷天泉就跪下给小串磕头,流着泪陪情道歉,又诉说对小串的思念。小串心一软,殷天泉就又扑了上去……就这样,小串一步步上了贼船,渐渐竟和瘸子情好日笃起来。小串能做借干,自然是殷天泉对她的报答,但殷天泉又对她不放心,过不了多久就要找小串一次,既笼络又监督,免不了要找地方发泄发泄,有时叫回去过夜,有时候就在野地里交合。最近殷天泉发现小串常跟宣传队一个大学生在一起,很亲密的样子,而且小串对她有点冷淡,怀疑小串和那大学生有了关系,就要小串离开宣传队回保健站;小串坚决不同意,他于是便接二连三地叫;这么一逼迫,小串和他闹翻了,殷天泉连叫几次都不走,甚至连沈庄也不出。殷天泉一时急昏了头,决定半夜里找小串,就在她宿舍过夜,逼迫小串就范。撒石灰圈的意思,是通知小串他要来了,叫小串晚上留门;结果门上了闩,他以为小串无情,越发怒火中烧,就跳墙而入,结果闯了大祸。
那个引起殷天泉发急的大学生当然就是我了。
那晚被软禁在大队部的,就小串、老梁和我三个人。我和老梁挤在一张单人床上睡觉,小串一个人坐在墙角,一句话也不说。大约凌晨两点多,老刘来叫小串,顺便叫我和老梁也过去。小串是被保卫组的人叫去审问去了,我当时并不知道,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天快亮的时候,老刘来叫我,说保卫组找我说话。我大惑不解,走进斜对门,看见小串那个表哥被铐在院里一棵榆树上,小串面向墙角低头站着,老谷站在当院抽烟,冷冷地看我一眼,我不由头皮发麻起来。走进屋子,见保卫组的三个人一排坐着,虽然都认识,却都黑丧着脸,和不认识一样。他们直截了当问我和小串的关系。我也直截了当回答:没有男女关系。也就在这一刹,我从心里佩服老梁:真是老奸巨滑呀!
俗话说: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幸亏有小串的证词,我才逃脱了干系。然而男女之事,从来是捕风捉影,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关于我和小串的流言,几年后才消弭于无形。
天亮后,保卫组的人带上殷天泉走了,后来听说被判了八年。小串躲在屋子里,整整一天没出来,我也没敢去看她,大家都不理她。第二天,老谷和老刘商量了一下,决定先打发小串回家,以免意外。他们相跟着到小串住处,竟已人去屋空。桌上留下一张字条,大意是说她走了,对不起领导,对不起同志们,请大家原谅。那张字条我也见了,是从笔记本上撕下的,很粗糙的纸,印着红线,是小串学习笔记本的一页,我很熟悉的。歪歪扭扭的字迹间,有一片水渍,不用猜测,一定是小串的泪水了。从此我再未见过小串,最后的一面,就是那个面墙哭泣的背影,想起来总不免深深地怜悯,莫名地惆怅。事发不久,那个现役军人和她退了婚,后来听说她嫁到了老远的山区,给一个三十岁的老光棍做了老婆。再美的姑娘,一旦坏了名誉,便是狗屎一堆,没人要了。我无法想像,一位那么娇嫩美丽的姑娘和一位枯树似的老光棍搭配在一起,日日夜夜厮守着过日子,会是什么样子。
几年前我到北京出差,去看已是大牌音乐家的老梁。我们不约而同说起小串。老梁仍坚持说,小串才貌双全,是大有培养前途的,可惜呀!我们默默相对,半日无语。我想,人们常说命运,这大概就是小串的命运吧。
老梁问小串的近况,我哪里答得上来,连是死是活也说不清。老梁又问老井,我同样答不上来。老梁叹口气说,真是往事如烟啊,只好任凭它消散吧。我请老梁为我来一段小提琴。老梁戏谑道:知道我一曲提琴的价格吗?一万!说罢,又拿出他那把祖传的小提琴,郑重其事拉了一曲《思乡曲》。我聚精会神地听,却怎么也品不出当年那种催人泪下的悲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