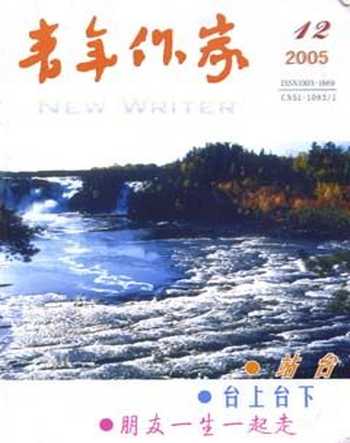谁敢看中午的阳光
眉山紫桐
一
林雨萱每天下班后无论多忙都要到匡若虚的画廊学书法和中国画。她那辆小小宝石蓝色甲壳虫还没停稳,匡若虚的脸上就情不自禁地露出微笑。若虚总是首先看到那个明丽的可人儿踩着高跟鞋的纤纤脚踝,脚脖子上系一条细细的银链子,上面缀了几只银的小飞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若虚把那条银链子的出现当成了每天惟一激动人心的节目,是不经意流过的日子里优雅而悲伤的美梦。那长了翅膀的小飞蛋银亮的光芒是暗寂的黑夜里迷乱而憧憬的色彩。
匡若虚家和林雨萱家父辈是至交。他们从小在一条巷子里长大,一起玩跳房子和藏猫猫,一起看书写字做作业。很小的时候,父母出差了,林雨萱就住在匡若虚家,房子小,两个孩子只好睡一张床上。他们在一起玩着剪刀石头布,兴奋地尖口叫,直到若虚的妈妈出来干涉,他们才用被子蒙了头,佯睡,片刻沉静后,在被窝里暴发出惊天动地的大笑。
林雨萱从有意识开始,就把自己当成匡若虚的女人,似乎是命运早已安排好的缘分。若虚的妈妈是一家儿童杂志的美术编辑,爸爸是中学美术教师。林雨萱小时候到匡家玩,印象里满屋都是书画作品。宣纸、画布、画笔、满墙的挂画、画架……巨大的画桌上铺了厚厚的毛毡,是匡伯伯画中国画的地方。匡家顺应了若虚的喜好,从小教他画中国画,他对中国画独有的敏感和热爱使他在上小学时就成了全城小学生中的书画领衔人物。
雨萱在若虚练宇和画画的时候,常拿支毛笔用个废纸头写上两笔毛笔字,匡伯伯看了就说,这小姑娘对书画有灵气。问她学不学,她却拼命摇头。在她的印象中,若虚已经是画中高手了,她和他是不分彼此的,有他会写会画,她的生活中就全是书画,够了。
林雨萱和匡若虚上同一所小学,两人放学上学一起走,肩并肩手拉手。可惜,那样纯净无波的快乐时光只持续到林雨萱十四岁;那一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那年春天,林雨萱的妈妈服毒身亡。
那一天有好得让人放心的阳光,明媚、温馨、艳若宝石般闪烁光芒,带着四面八方的花香草香铺天盖地扑面而来。
从那天起,林雨萱就不敢看中年的阳光。
二
因为包了“二奶”,林雨萱当局长的爸爸被县纪委调查,继而免去其局长职务。这是当年县城里最为轰动的事件之一。
林雨萱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小女生,坐在教室最边的一个座位上,老师提问时,她常常一脸茫然地站起来,讷讷地开不了口,连老师也不忍心看她那双明若星子般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无助。十四岁的少女最为敏感,她总觉得全校的同学甚至老师都在议论她父母的事。
那天快放学的时候,林雨萱直起身,突然有点眩晕。后排的女生惊叫起来,血!她循声回头,看到自己的椅子上有一摊鲜红的血迹,白的确良的连衣裙上也湿漉漉的,一摸,也是一手的血。全班同学的目光齐刷刷聚集到林雨萱脸上、身上,炮弹似的轰着她,令她觉得长了这个身体是最痛苦的事。她复又坐下,任同学们一个个走光了,还将头伏在桌上,抽噎。她哭到最后不知该如何收场。因为裙子还是湿的。
不知邻班的匡若虚如何得知了这件事。匡若虚脱下外套,系在她腰上;给她提来一大桶水,让她擦洗。他一言不发地做着这些事,脸上有深深的隐忍、严肃和慌乱。
若虚稚气的脸上成熟的表情吓住了雨萱。他的行动传递过来的温暖和关爱,让一个深陷孤独和不幸的少女从此成为爱的囚犯,失去了选择的自由。
三
终于,上大学了。林雨萱提着那个咖啡色的仿皮衣箱走进校园的时候,头也不回地把过早老迈的爸爸抛到身后,如同抛掉那些往事,那些噩梦,那些记忆。唯有匡若虚是不能抛掉也抛不掉的。匡若虚碰巧也被林雨萱就读的这所师范大学录取,读美术系。
大学的种种乐事让林雨萱慢慢开朗起来。她除了跑图书馆看书,写点小说散文什么的,也开始参加校园舞会;参加野营训练;开始交朋友;开始留长头发,买新衣服和淡紫色的口红。
最疯狂的是那次中文系和美术系联办的假面舞会。林雨萱不会弄假面,就让隔壁寝室美术系的女生帮忙画成和她们一个系列的京剧脸谱。记得那个叫胡蝶的美术系女生非常活泼,娇小可人,她到九寨沟写生的油画被老师挂到宣传栏,一贴三个月,直到有男生在上面贴上“胡蝶,我永远爱你”洋洋洒洒10页情书,那些画才被取下来。六个女生六张脸谱,生旦净末丑外加一个黑脸包公。林雨萱一张娃娃脸被胡蝶画成了孙悟空,红色黄色黑色白色的油彩腻糊糊涂到脸上,很不好受,可是大家都兴高采烈,相互看着对方的脸大声尖叫狂笑不止。
可是,当林雨萱在舞会上看到匡若虚,她才深深后悔起自己难看的化妆。
若虚已长得很帅了,他身着不知从何处弄来的佐罗式的黑披风,脸上戴了佐罗的面罩,只露出两只眼睛和挺直的鼻梁。林雨萱可怜巴巴地想要靠近若虚,可他正被一群女生包围着,无法靠近。
舞会一开始是文娱表演。等到一个叫云容舞的中文系女生上台演奏扬琴时,才把全场引向癫疯状态。只见云容舞一身湖绿轻罗绣裳,喇叭七分袖和曳地长裙令她飘飘欲仙,纤纤细腰不盈一握,白如凝脂的皮肤,却有“黑得像夜”一样的长发,齐腰垂着。高挑、袅娜,款款上台,薄而优雅的背微微弯了,开始演奏扬琴。云容舞精致的脸上清浅的笑容,映照着整个舞厅。
那一晚,林雨萱眼睁睁看着美术系第一才子拥着中文系绰号“小白菜”的系花云容舞翩翩起舞。一曲接一曲,他们挨得那么近,脸贴着脸,私语着,笑着。林雨萱那张滑稽的孙悟空脸隐没在舞会边的角落里,心如坠冰窟。
四
二十岁生日那天,林雨萱有点感冒,她逃了课,独自在宿舍蒙头大睡。
她突然很想妈妈。起床,吃了感冒药,从衣箱中取出妈妈惟一的纪念,那件妈妈亲手绣了墨绿牡丹的秋香色真丝绉纱旗袍。摩挲着那日渐淡去光泽、凹凸有致的牡丹,那些美和爱怜从指尖缓缓滑落。突然有要抓住什么的欲望。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旗袍,在一面圆镜子中,她看见梳了两条乌黑辫子的女子,脸若百合般竟和旗袍衬得那般完好。
暮色上来时,同学们打饭回来了。楼下传达室传来有人请林雨萱下楼的喊声。林雨萱止不住心中的狂跳,是若虚,一定是若虚。
天空下着一点小雨。若虚一脸阳光站在女生宿舍门口,一件黑色夹克已湿透,头发上也滴下水来。他笑吟吟地看着雨萱,真美,你穿旗袍让人感觉你突然长大了,不再是那个只会哭鼻子赌气的黄毛丫头,生日快乐,小宝贝!他说着伸出手,掌心一块碧莹莹的翡翠挂件——一个笑容可掬的弥勒佛。男戴观音女戴佛,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让这个弥勒佛保佑你,无忧无虑,快快乐乐。
林雨萱扑进若虚的怀里,在来往路人的众目睽睽下失声痛哭起来。在这二年中,除了妈妈,就只有若虚记得她的生日。
暮色四合,小雨一直在下……
大学毕业,匡若虚和云容舞都分配回原籍,分别
做了S城中学美术和语文教师。再过一年,相恋四年的匡若虚和云容舞理所当然地结婚生子。
匡若虚教学之余继续沉迷于翰墨丹青、封泥瓦当,他四处求师学艺。只要听说哪儿有好的书画展或有名师开课,揣两三件换洗的衣服就上路。对艺术的狂热和忠贞那是九匹马也拉不回来的。全国书法展在西安展出,匡若虚刚自费出了画册,当时经济很拮据,到朋友那儿借了500元钱就出发,刚刚够来回的火车票和最简单的食宿。在现实中,匡若虚一件5块钱的T恤、一双草鞋是闻名全城最经典的打扮。有一次到扬州看八怪画展,一下飞机,机场空姐实在控制不住笑意,说,先生,你穿草鞋好酷!一双草鞋和一身布衣也掩不住的潇洒奔放、落拓不羁,这是当初云容舞爱上他的惟一理由。但,一旦将爱落实到现实中,这位当年的系花免不了会抱怨。每天下课后还要骑自行车赶回家买菜做饭带孩子,在现实的折磨中,天长日久,美人成了黄脸婆,演奏扬琴的纤纤十指变得粗糙,扬琴也早已不复弹奏。
为了以画养画,匡若虚偶尔也帮朋友做一点美术设计之类,都是小型的。无心插柳,一不小心在圈子里渐渐有了名气。朋友推荐若虚主持一个大型演出的舞台设计。为了与相关人员接触,若虚被邀请至S城最有名的“雕刻风情”酒吧参加酒会。
酒吧二楼悬空有一道宽阔的回廊,被独具匠心布置成空中花园的味道,临窗有长长的落地玻璃墙,可以远眺长江水一碧千里,滚滚东去。这个回廊连接的一个露台正好可以用来举办各种小型party和沙龙的活动。匡若虚在朋友转身同三三两两进来的人打招呼的时候,找了一个临窗的位子静静坐下来。面前一杯桃乐丝,鲜艳夺目的血色液体,散发出顶级红酒淡雅的芬芳。匡若虚想,这里是不属于他的世界,他的世界里只有翰墨丹青、宣纸、草鞋、刻刀和永远临不完的书法帖,背上简陋的行囊就可以行走山水间。
在他心不在焉的时候,门外走进一个女孩,个头不高,肌肤如玉,妆容精致得让人不能逼视。一件绿色绉纱真丝绸的斜肩礼服裙,长可曳地,丰胸细腰,一边饱满圆润的肩头,系了宽宽的绿绸蝴蝶结,行走如弱柳扶风,袅娜而动。林雨萱!若虚寻找了三年的妹妹,竟然神话般以此种姿态出现在他的面前。匡若虚一时百感交集,说不出话来。
林雨萱手持一只晶莹剔透的杯子,款款前来,她微微笑着,说,若虚哥哥,我们终于见面了,你这几年过得好吗?镇静得令人停止呼吸,微微的冷漠。
站一旁的朋友忙介绍说,这位就是负责这次舞台设计策划的林雨萱小姐。匡若虚的手竟不自觉轻轻发抖。
匡若虚的舞台设计工作迅速展开,林雨萱每天都要到匡若虚的画廊看看工作进程。
匡若虚开了一间小小的画廊兼工作室,在教书之余做点美术设计,兼收些书画弟子,还代销朋友的书画作品,赚点零钱聊以补充学书画的费用。
林雨萱说,老头子既然把如此重任交给我,虽然我当不起,但也得尽最大努力把它做好。况且这几年,老头子待我不错。做完这一件我就不想做了,他让我做这个工作我本来是不太想做的,他想让我不要太无聊,但我试过之后发现自己不是做这一行的料。所以以后也不想做这行了,还是喜欢文字的东西,哪怕以后能做个记者编辑什么的也是学以致用吧。
林雨萱所说的老头子就是她所在文化公司的老总付之白。付之白五十多岁,除了这间公司,麾下还有别的实体。
三年过去了,林雨萱的说话语气、表达用词都有明显的变化。语气里有又软又糯又慵懒的调子,听来颇有点娇滴滴的味道,这一点反倒让她变得既神秘又平易,很有吸引人的韵味。但她的眼神里却又分明有落寞和无奈。这些变化匡若虚看在眼里,他很怜惜地不问她这几年的经历,却从她的神态、气质、打扮、谈吐和她开的车、花钱的作派中看出些端倪。
此后,林雨萱每天下班后都要到匡若虚的画廊。一开始是谈设计的事,后来看到有好些十来岁的小朋友在那儿学画,她干脆拿起毛笔,拜了若虚为师,开始练习书法和中国画。
林雨萱天天到来,却给匡若虚带来许多不解之谜。林雨萱不说,匡若虚也不好问,毕竟那关系到一个女孩的隐私。虽然匡若虚是林雨萱从小到大最亲密无间的人,但是,自从匡若虚在大学时代放弃了林雨萱,他就没有权利过问她更多的事情。
他仍为她每天的到来做精心的准备。她要系统学中国美术史大纲,她要看中国美术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书画作品的影碟,她要临一个新的帖《汉张迁碑》,她要一个刻闲章的石头,她要看徐青藤的画册……一切,匡若虚都心甘情愿为她细细准备,甚至在报纸上看到好的画评,他也剪下来给她读。
在匡若虚眼中,林雨萱永远是那个白纸一样的小女孩,是区别于外界传得极不堪的那个小狐狸精的。林雨萱的灵秀体现在艺术上是不点即通,像一个不通水性的女子只凭了一身轻功,踩了一枝彼岸的芦苇轻飘飘就抵达艺术的至境。虽笔下仍是粗浅,但那灵秀却超过了学艺多年的人。
从这一点看,她倒真有“狐气”。匡若虚开她玩笑,雨萱,你这个小狐狸精,要害人到何时啊?他看到她一直吊在脖子上的那个翡翠弥勒佛,无论穿什么衣服都不变地挂在她那两个迷人的颈涡下面。匡若虚有时看着就会出神,那两个浅浅的涡,是他突然想沉溺的碧蓝的湖,醉在里面,竟是老早以来潜在的愿望,不知为什么他自己原来竟没有发现。那弥勒佛,是他送给她二十岁的生日礼物,她戴到断了丝线,又重新穿上,再戴。那个弥勒佛,是当年匡若虚在雨中骑了半天自行车跑到城里,倾尽半年勤工俭学挣到的钱买的。只因为那时雨萱过早失去了母爱,过早失去了欢乐,匡若虚以一个临时监护人的身份在生日那天给了林雨萱一点小小的欢乐。
五
匡若虚的艺术创作进入了一个瓶颈阶段。虽然他依然痴爱书画艺术,但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追求技法和刻画到极致的误区。下笔小心翼翼,反而在意境上没有了新意。虽然技法已经很高超,但没有鲜活灵动,没有生命酌张力,哄外行可以,但却骗不了自己。他开始撕画,画一张撕一张,有时非常苦闷就会坐到画廊的角落里一个人抽烟。
林雨萱总是默默地将他来不及撕的画小心收起来。她有时在旁边随便给他说说。她说,你的创作走进一个为画而画的死胡同,没有注入感情的胸中丘壑,少了气势,缺乏饱胀的激情和有力量的热爱,对生活没有鲜活的感悟,画出来的画才总是令你失望。匡若虚突然被她点中了命脉,恍然顿悟。林雨萱说,若虚哥哥,出去走走吧,可以开阔视野,增加见识,保持生命的鲜活。
林雨萱默默为若虚上路准备好一应物品。从画画工具、书籍、手机、衣物到一些必备的药品,该想到的她都想到了,弄了一个精致的旅行包。这一次准备去敦煌采风,他的经费少,只能作一次苦旅。临行前一天,林雨萱特别沉默,看着在狂躁中渐渐枯萎的若虚开始兴奋,突然特别地心痛。身为艺术之人,把艺术当作了生活的全部,为主可以生亦可以死,世俗的价值观对他无一丝一毫的影响,他所有的收入都投
入到了书画学习中,至今仍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他是活在自己梦境中的男人。林雨萱于是说,若虚哥哥,你热爱的东西就要不顾一切去追求,我支持你。
若虚看着站在面前的女孩,他突然说,和我一起去?
林雨萱为这句话等了十多年,然而她却说:“你是云容舞的丈夫;而我,你应该有所耳闻,我是付之白的女人,他是付我钱的。我现在是个物质女人,是钱的奴隶。因为得不到想要的爱,能得到钱也是好的。你和我,在四年前就已错过。”
匡若虚出神地看着林雨萱,那眉目,那乌发,那颈下一双浅浅的迷人的涡,是为他盛装了二十四年的一坛好酒啊。他只愿沉醉在这坛本该属于他的酒里,世上什么都可以舍弃……
林雨萱软弱地与他对视。她眼神迷离,突然轻轻地说,好,我去。
他们上路,坐火车。再转汽车。几天时间转瞬即逝,颠簸中,就到了敦煌。
在莫高窟,那集壁画、雕塑、建筑艺术于一体的摄入心魄的艺术魅力深深地震撼了画家。匡若虚从壁画中看到了哺育了张大干的艺术营养,这营养不仅仅造就了张大千和美术,也丰富了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剥落、变色、褪色、风化让所有的壁画和雕塑都深深烙上时光匆匆走过的身影,飞天和千手观音颓败相望。林雨萱和匡若虚一时目瞪口呆,世俗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在此突然成了笑话。看到生命如此脆弱,时光如此无情,就会敬畏那种神秘的力量,敬畏来自内心深处的痴迷、爱和苦痛。
从敦煌回来,匡若虚的画艺精进,他说,他听到了内心的呼唤。
而林雨萱,是他可以为之放弃一切的女人。这,也是宿命。
六
林雨萱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是她生命中惟一爱过的男人给她的礼物,幸福的感觉悄然来袭,潮水一样把她淹没。这是他和她的孩子!她惊讶地发现自己原来如此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拿着化验单从化验室出来,化验室的女医生用见惯不惊的表情冷淡地说,阳性,怀上了。再低头看林雨萱的脚,你还穿这么高的高跟鞋呀?以后别穿了,小心别摔着。如果是头胎,最好生下来,头胎婴儿生命质量最好。要吃有营养的东西,不能久坐,不能抽烟喝酒,不能乱吃药,不能到人多的地方……
林雨萱模糊地听着医生絮叨,猛然感到,自己走在人生的路上,已经回不去了,那样纯粹的青春时光,随着这条小生命的到来,匆促地画上了句号。她的小腹突然成了最脆弱的部位,原来被她忽视的身体,现在成了另一条生命的源头。她疲惫地踩着高跟鞋,一路歪歪斜斜地走下去,那寂寞的余响,怅惘地回荡在医院的回廊里。回廊里那些来苏水、酒精的气味,成了那段特殊时光的标记,那么寂寥、无助和惊恐。
林雨萱不能把怀孕的事跟若虚说。她知道,若虚有家室,他是不会接受这个孩子的。她身体越来越不舒服,整天昏昏沉沉。她硬撑着给自己弄有营养的东西吃,在留与不留孩子的问题上,内心激烈交战,无所适从。生下来,他就是个私生子;不生,她又是那么强烈想要他。
做一个真正的女人,为自己心爱的男人生一个孩子,这是她现在惟一能做并想做的事情。其余的一切事情,她已经不能去想,去判断。她住进了医院。医院的时间总是漫长又漫长,她的病房里同时有另外两个住院的产妇。一大堆人来了,说笑,一会儿又风一样消失掉。静下来时,隔床的婴儿啼哭声就特别响亮,那稚嫩的声音犹如天使般可爱。一听到那样的声音,林雨萱的母性被唤醒,做母亲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
林雨萱现在只能住最便宜的病房,自从她和匡若虚的故事传出去后,她所有的财产包括车和别墅都被付之白在一夜之间收回去。她的银行卡上的钱也在一夜之间从7位数变成了4位数。这个男人还算有良心,给她留下了最后一点活命钱,林雨萱一想起过往的三年,浪费掉的青春和感情,就会冷透骨髓、直打寒颤。忽然有一场戏落幕后的寂然、怅惘。最怕是散戏之后,孤零零地面壁回味。
若虚为了彻底拥有她,竟下海办起了文化艺术公司,他要拼命赚钱,不让她重过那种一贫如洗的生活。她见若虚对艺术的热情大大减退,变得越来越世俗,就和他争和他吵,最后若虚竟至说出“不如无情”的话来……
自从和若虚吵架,直到逼他说出“不如无情”的话后,林雨萱惊觉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和匡若虚联系了。
林雨萱不甘心,她不甘心十年建筑起来的爱只是海市蜃楼,影影绰绰,虚无缥缈。若虚那温暖的脸、清澈的笑犹在,她记得他怜爱地说她是“可人儿”。雨萱不想放手。
明知他不会接自己的电话,林雨萱还是要拨过去——只有他的电话是惟一能和他相联的东西。电话那端传来空洞的铃声,他不接。再拨,仍不接。林雨萱像一只受伤的小狗,蜷缩在浆洗得发硬的白棉布被子下面,寒意一阵阵袭来。她茫然地重复拨铃的动作,把这个动作当成了目的。数响到一千次,手机也拨得发烫,终于停下来。
林雨萱在医院静养的一个月中,常常陷入迷茫。可是爱是确定的,孩子要生下来的愿望是确定的,她独自数着手机上的日历一日一日艰难度过。
出院之后,她想到了最好的去处,那就是乡下姨妈家。那儿有一幢两层的农家小楼。姨妈得知雨萱没有上班了,早就叫雨萱去那儿陪她。姨父死后,表弟读大学去了,剩下姨妈一个人住那样一大幢房子,挺寂寞的。林雨萱在那儿静养,直到把孩子生下来,那是惟一合适的地方。
雨萱收拾好行李,那些华而不实的衣服和首饰就装了几大纸箱。物质和身心最后败落到如此地步,雨萱嘴边有了淡淡的笑意,嘲讽是留给自己的最后的自尊和自爱。能够自嘲,还不算失落得找不到自己。还好,还有他,林雨萱轻轻拍拍已有点鼓起来的腹部,这是她最后的珍宝,是若虚留给她的礼物。林雨萱沉吟片刻,爱中的女人总是卑微的,她又拨出了若虚的手机号码。可他的手机竟然停机,从此他要从她的视野中消失吗?
七
匡若虚手机停机倒不是要躲避林雨萱,而是他出事了。
匡若虚得到内部消息是在警察到来的前一天,他匆匆从银行流通的卡上取出仅有的80万元现金。其余的钱,都作了投资,一时半会取不出来。第二天,他的银行帐户全部被警方冻结。
他用一个简陋的提包装了那80万元,换了手机卡,匆匆上路。
在火车上,他时时如惊弓之鸟,背对过道怯怯坐了,从玻璃窗里看后面的动静。一有穿制服的,他就紧张得心要跳出胸口。长长的旅途,他对自己的前半生想了又想,他想到了最坏的结果,死。假如死期真的临近,那最放不下的人还是林雨萱,那是为她可以放弃他的理想,放弃他的艺术的女人啊。他突然特别想她,她是无条件地爱着他的女人,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不设防地爱着他,为他吃尽了苦头。她的感情没有一丝一毫的杂质,那样纯粹的爱,得到了,是他匡若虚一生的幸运。
匡若虚拨通了林雨萱的电话。那边传来林雨萱孩子般快乐的声音。若虚,我知道你放不下我们娘儿俩的。若虚,我们的孩子已经四个月了,已经会动了
呢。我要把他生下来,到时候我们一家就可以团聚了。若虚,我在姨妈家,会种菜了呢……
孩子?匡若虚一时百感交集,不辨悲喜。要是人生能够重来,要是人生可以全部重新选择,那该多好啊。他要把这个天使般的女人当成珍宝,好好宠她,过完他们没有遗憾的一生。
匡若虚关掉手机,不可遏制地失声恸哭起来。
坐在旁边的那位中年妇女厌恶地盯着他,嘴里嘟囔,一个大男人,哭啥哭?
匡若虚在火车上度过了难捱的两天,火车上的食物他几乎没有动。只三天,他的白发就野萆般地长出来了;只三天,他就又瘦又老又憔悴;只三天,他就经历了炼狱般的磨难。
可是,一下火车,他就被便衣警察抓获。
那么明媚的阳光,金光四射的阳光,好得让人放心的阳光,好得和母亲死那天一样的阳光。林雨萱在田间摘菜的时候突然被越来越热的阳光晒得有点眩晕,她直起腰的一瞬,眼前黑了一下。这是怀孕初期的贫血症。但她还是感觉到有什么改变了,那种说不清的预感没来由地抓住了她。
忽然就急急往姨妈家走,模糊觉得那是揭开谜底的地方。
田边有一张别人包过东西的报纸,看看日期,还是昨天的。头条,一个男人跳楼自尽,全身血肉模糊。呀,又发生这样的事?林雨萱再一细看,那黑色的大标题:《XX文化公司总裁匡若虚涉嫌金融诈骗462万元畏罪跳楼自尽》。
天上明晃晃的阳光刀刃似的千刃万箭般掉下来,那天,只在一刹那就全部变成了黑夜。那样毒辣、闷热、多汗、窒息的黑色的阳光啊。
八
很久很久以后,林雨萱还如失忆者一样呆若木鸡地躲在房间里,坐在厚厚的窗帘下。那紫红色丝绒的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不能有一丝缝隙。姨妈稍稍拉开一点缝隙,让林雨萱透透风,只要不看到阳光还好,一旦看到一丝阳光,她就会浑身发抖,不可遏制地泪流满面。她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过一句话了,整天坐在窗帘下,苍白、多疑、出汗、失忆。
姨妈说,萱萱,过去的就过去了,你还年轻。这样的话林雨萱一听就会两眼放异光,好像立刻就会疯掉。实际上,她离疯已经不远了。她在平衡自己的感情,有意识地要往健康里发展,而不是寻找陷落到无底深渊的借口。可是,生命中她最爱和最爱她的人,妈妈、若虚都离开了她。她的胎儿也在那个中午因为惊吓过度流产。
很久很久以后,林雨萱慢慢能在清晨出门,抬一把竹椅,坐在一棵粉色樱花树下,这不是阳光强烈的季节。春天,阳光总是柔和温情的,那些樱花瓣一片片从枝头坠落,来自大自然的爱、怜惜就簌簌地扑面而来。林雨萱能忆起的前尘往事又上心头,那些遥远的故事,那些不能割舍的眷恋和爱着的人啊,那些骨肉相连的身影竟开始模糊,从她的生命中越走越远。
责任编辑阿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