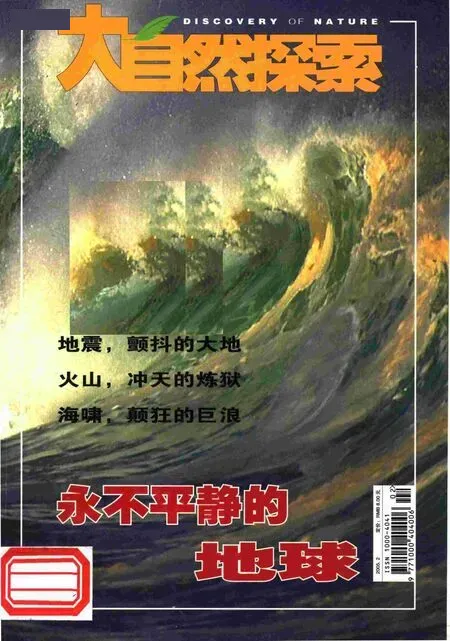“伤寒玛丽”的故事
编译叶曦
20世纪初,美国纽约,随着大量贫困移民的涌入,贫民窟不断增加,传染病肆虐,生存环境日益恶化,许多儿童被诸如腹泻之类的肠道疾病夺去生命。除此以外,肺结核、百日咳和白喉也在纽约大肆流行。
相比之下,位于长岛的牡蛎湾俨然是另外一个世界,这里是纽约富人们的度假胜地。但是突然间,这个权贵们的乐土也变得脆弱不堪。一个富豪家中出现了致命的疾病——伤寒。伤寒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然而,这种本应只属于贫民窟的传染病是怎样溜进富人区的呢?
病情突袭
1906年8月,在长岛牡蛎湾畔的一座豪华度假屋里,一个名叫玛格丽特·沃伦的小女孩感染了严重的伤寒。虽然她得到了最好的照料,但病情却丝毫没有减轻。人们惟一能做的事,就是采用各种办法降低她的体温。这家人带着佣人来到长岛度假,租住在这所位于海边的高级住宅里。不久以后,女孩的母亲、两个女佣、女孩的姐姐,最后是园丁——又有6个人相继病倒。说也奇怪,除了他们之外,这里没有人染上这种病。
在20世纪初,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方要数纽约的东下城,那里的人口密度甚至超过了印度的加尔各答。但是那里却仅仅拥有极其简陋的排水系统,同时也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每年,像天花、肺结核、白喉和伤寒这样的传染病要害死数以千计的人。
伤寒是纽约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流行病,特别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这段时间里,仅在纽约每年就会新增4000名伤寒病患者,其发病后的症状非常严重持续几周的高烧、头痛、腹泻和精神狂乱。死亡率超过10%。然而,直到20世纪初,仍没有出现能对付这种疾病的抗生素和大夫。
不过,这种疾病的起因已经不再是一个谜。早在30年前,科学家路易斯·帕斯特就发现导致这种疾病的元凶是一种肉眼看不到的细菌。这种细菌属于沙门氏菌的一种,寄生在肠道内,并随着粪便到处传播。1892年,纽约成立了美国第一个致力于保护公众健康的细菌学实验室。新兴的细菌学谱写了科学史上全新的一页,它让人们通过显微镜看到了前所未见的东西,知道一旦诊断出某人感染了传染病应该怎么做,以及怎样防止疾病感染更多的人。
在牡蛎湾这个连罗斯福总统都会光临度夏的胜地,伤寒的威胁让所有人都心惊胆战。每个人都在四下顾盼,试图发现可疑的分子。专家受命前往调查,他们深知伤寒病的起因在于不干净的食物和饮水。他们首先怀疑房间管道的涂料污染了饮用水,但化验的结果却是否定的。他们又检测了本地出产的贝类,试图找到海湾被污染的证据,结果同样令人失望。他们还检测了牛奶,但也没有发现细菌的踪影。这场伤寒爆发的源头成了一个谜。
端倪初见
尽管牡蛎湾的伤寒病人逐渐康复,但阴云仍然笼罩着沃伦一家租住的那所豪宅。豪宅的主人汤普森担心自己的房子将来再也租不出去,于是他决定找出事情的真相。1906年冬天,汤普森求助于37岁的医生乔治·索伯。索伯在治疗伤寒病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而且他也同样希望能找到这次爆发的原因。索伯欣然接受了汤普森的委托,开始重新审视原来的调查报告,试图从中找到蛛丝马迹。但让他失望的是,他没能从以往的调查中找到突破口。于是,他将注意力转向了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人。
他访问了沃伦家的每一个人。为了确保没有人被遗漏,他向其中一个佣人核实住在这所豪宅里的人数。这立刻提醒了这个佣人:那一年的夏天,沃伦家的厨师——一个名叫玛丽的女人在事发后不久就走人了。
索伯发现,在伤寒病爆发的前三周沃伦家更换了厨师,而所有的病人都是在新厨师玛丽到来后被感染上的,因为伤寒在发病前有三个星期的潜伏期!索伯找到了第一个线索。
一个身患伤寒的厨师传播疾病的方式可能是在上完厕所后,其他人接触到他(她)留在洗手间的病菌而被传染;或者是食物没煮熟,从而让病菌得以存活。有一个星期天,玛丽做了一份人见人爱的甜点:用鲜桃点缀的冰激凌。索伯医生认为,当时玛丽可能没有清洗双手,或清洗得不彻底,从而将疾病传给了众人。
37岁的玛丽是一个来自爱尔兰的移民,在纽约靠为富人家干活为生。索伯立即设法寻找她。介绍她到沃伦家打工的职业介绍所并不知道她的行踪,但他们告诉了索伯一些有关玛丽前几任雇主的情况,这令索伯大吃一惊!
10年中,玛丽为八个家庭工作过,其中六个家庭都出现了伤寒病人。也就是说,她在这些年里一直在传播伤寒,而自身却没有一丁点发病的迹象。这怎么可能呢?
索伯回忆起10年前读到过的德国科学家罗伯特·康驰写的一篇论文。康驰发现有一个面包师传播伤寒,但自己却没有发病。康驰称他为“健康带菌者”。如今,这种情况是否也出现在了玛丽身上?
索伯意识到,他正身处医学和医学史研究的尖端前沿。假如索伯的推测没错的话,这位玛丽厨师将是美国第一个被确诊的健康伤寒携带者。这无疑将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为了证实这一切,索伯需要获得玛丽身上的样本。1907年3月,他得到消息,玛丽正在为家住公园大道的一家人工作,而伤寒已经在这个家庭出现——一个女佣住进了医院;家里惟一的孩子在玛丽的照料下已经病得奄奄一息。
拒不合作
索伯原以为玛丽会乐意知道真相,并能够配合他进行调查,但是他们的面谈却充满了戏剧性。索伯试图说服玛丽面对她充当了伤寒传播者的事实。并且提供尿液和血液样本进行检测。但是没有料到,他的一席话激起了玛丽强烈的反应。玛丽认为,索伯没有提到那些她曾经工作过、却没有出现伤寒的家庭——比如在有一家,她曾和孩子们共居一室,却并不曾给他们带来任何的麻烦。
“假如某人身患某种疾病,他(她)就有可能传染给其他人”,这个概念在当时还相当前卫。当一群科学家告诉你原来闻所未闻、甚至肉眼都无法看见的细菌就是疾病的元凶时,你到底是信还是不信?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玛丽也无法理解这样的事实。
在19世纪,人们还以为疾病来自于神秘的下水道,来自于恶臭和沼气。随着移民涌入城市,垃圾和各种污秽堆满社区。每十年人口就增长一倍,然而公共服务却无法与之匹配。纽约城充斥了15万到20万辆马车,每天一匹马产生的25磅粪便成了公共卫生的头号问题。一年365天,20万匹马产生的肥料让这座城市变得肮脏不堪。没人收集的垃圾、动物的尸体、后院的杂物、堵塞的下水道和家庭废物使人无法忍受。清理城市成为了一项圣战。1895年,卫生部门宣称“清洁和基督一样神圣”,还招募人员组成了一个街道清扫队。索伯正是其中的一员。
索伯站在新科学的前沿,如果玛丽是伤寒带菌者这个猜想被证实的话,
将为细菌学的可信度带来新的注解。一个偶然的机会,索伯发现了玛丽和她同居男友布雷霍夫的行踪。布雷霍夫在一个酒吧上班,为人还算和善。他友好地接待了索伯,还让索伯到家里做客。他们住的房间无比肮脏,散发着恶臭,他们还养了一条凶猛、邋遢的狗,而布雷霍夫本人还是一个酒鬼。所有这一切,就这样真实地呈现在索伯的面前。
索伯对布雷霍夫采取了一些手段,从某种程度上激起了他接受检测的欲望。索伯再一次尝试说服玛丽跟他到医院做检测,但他的人际沟通能力比不上他在流行病学方面的成就。玛丽是一个强悍的爱尔兰移民,她原在爱尔兰过着自由的生活,却来到了一个轻视她,对她这样的人抱有偏见的社会。愚蠢、醉酒、肮脏、无法融入主流社会,在美国这些贫困移民不得不变得强悍。
玛丽家乡的生存条件非常恶劣,每年都会爆发瘟疫。她吃着粗略加工的土豆长大,没有盘子和刀叉。1883年她和叔叔婶婶移居纽约,不久以后,她的亲人离开了人世。事后,她总是形容她自己是“美国的孤人”。
她洗过衣服,做过裁缝,当过清洁女工,拉过煤,几乎所有低层的工作她都做过。后来她学会了做菜,以及怎样管理好厨房。很明显她很擅长做这样的工作。以后的时间,她一次又一次地被富裕人家雇用。
厨师在佣人中的地位最高。玛丽常常不仅仅是一个厨师,实际上还扮演着管家的角色,并且深受信任。但玛丽的顾主根本没有料到他们的厨师会给他们带来伤寒。索伯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一旦条件成熟,玛丽将造成疾病的大流行。但问题是索伯没有权力强迫玛丽合作。
强制隔离
纽约城市卫生委员会的委员比格斯负责领导对付伤寒、麻疹、流感、白喉和肺结核这些传染病。委员会保证用科学和公共卫生手段清除疾病。在这场战斗中,工作人员有权进入贫民区对居民进行接种预防,让感染人群呆在家中,不得外出,甚至可以用武力手段强行隔离那些不愿合作的病人。
索伯在比格斯面前列举了玛丽的事实,并建议立即将她拘押做采样调查。因为雇佣玛丽的那家人的女儿已经死于伤寒,比格斯答应了索伯的要求,下令玛丽必须接受检查。但是,当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警察的协助下准备带走玛丽的时候,却遭到她的强烈反抗,并且还让她一度逃脱。让工作人员头疼的还有那些和玛丽一起干活的佣人们,他们拒绝透露有关她的任何事、任何消息。工作人员几乎搜遍了每一个角落,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就在他们准备放弃的时候,有人在后廊一个堆满垃圾箱的门后发现了玛丽。经过一番劝说,工作人员最终强行将她带到威拉德·帕克医院(一个专门给穷人呆的传染病院),并将她关在病房里和那些传染病人呆在一起。玛丽是一个清白的人,却被当成无赖、罪犯,遭受粗暴的对待,这对她而言的确是一种侮辱。
在纽约刚建成的细菌实验室里,科学家用最先进的仪器和技术对从玛丽身上取得的样本进行了化验。最终得出的结论正如索伯医生所怀疑的那样,玛丽果然是个伤寒病菌携带者。但是为什么连玛丽都不知道自己患上了伤寒呢?那只是因为她自身没有具备足够的条件来诱使其发病,以至于她还一直以为自己不过是患了感冒。
在大部分伤寒病例中,人的身体作为微生物战斗的战场,胜负总是一目了然。如果病菌赢了,病人就只有一死;反之,如果人体免疫系统赢了,病菌则会消失。但是,在健康的病毒携带者身上却不然:病毒携带者的免疫系统保护着人体不让病菌肆虐,但同时病菌又能在人体内继续存活。比如玛丽,她虽没有伤寒病的病症,但是她的传染性却和其他伤寒病人是一样的。
玛丽的故事在当时轰动一时,“伤寒玛丽”这个名字常常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头条。应玛丽的要求,卫生部们隐瞒了她的完整姓名,但同时也隐瞒了她是被逼无奈的事实。玛丽出于对自身遭受粗暴待遇的愤怒,一直拒绝与索伯合作,这其实是不难理解的。但是,除了将玛丽隔离起来,他们还能怎么办?总不能再让她回去重操旧业吧?!公民个人的自由有时不得不服从于公共利益。因此,为了大部分人的健康而剥夺某个公民的自由,应该是能够得到公众的理解的。
暂获自由
北兄弟岛距布朗克斯南海岸约几百米,滨河医院——纽约最大的隔离区就坐落于此。这里的病人大多是肺结核患者,他们会一直呆在这儿,直到他们痊愈或者死去。这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充斥着虚弱的传染病患者。而玛丽,这个无论谁都不会怀疑她的健康的人,却被送到了这里,被幽禁在岛上的一个小屋内,从此与世隔绝。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对玛丽的监禁是合理的。一些有声望的科学家对此就持反对态度,他们知道玛丽是一个病毒携带者,也清楚她所能带来的危险,但他们认为只要让玛丽换个不需要她烧饭的工作,她就不会再威胁到任何人。可是卫生部已铁了心不放玛丽走,所以医生们只能尽力开发各种新药及新的治疗方法,希望能治好她,可惜的是玛丽并不配合。玛丽并未就此罢休,她不断地给索伯医生写信,乞求得到自由。可是两年过去了,一切还是没变,玛丽仍旧被囚禁在这个岛上,她感到越来越绝望。直到1909年6月,玛丽和她的爱尔兰律师向纽约高等法院提起上诉,要求得到释放。她的理由很简单:她从来没有得过伤寒,所以不可能传染给任何人,而且她从未出过庭,对她的囚禁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
后来,《纽约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玛丽的故事。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坦言他们至少发现了50个病毒携带者,但是惟独玛丽被囚禁了。为什么卫生部会让另外49个带菌者“逍遥法外”呢?其实当他们混迹于纽约的人群中时不会造成危险,只是玛丽碰巧是一个厨子,所以她就很容易传染给其他人。1909年7月,玛丽来到纽约高等法院进行抗辩,这是她两年来头一次离开北兄弟岛。在法庭上,卫生部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并极力申辩:有实验结果表明玛丽确实是病毒携带者,因此她对公众健康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而玛丽为这场官司也做了充分准备。数月前,她让她的男朋友布雷霍夫亲自将她的样本送往曼哈顿的费格逊实验室做了化验,化验结果与卫生部的完全不同,样本里没有发现任何伤寒病菌。偶尔在健康病毒携带者的样本中可能发现不了病菌,这也许可以解释这个化验结果,因此最高法院还是和以往一样站在公共卫生部的一边,驳回了玛丽的上诉。
事实上,当局对玛丽进行隔离的决定应该是无可非议的。公众拥有同威胁自己健康甚至生命的人隔离开的权力。正如今天我们面对某些疾病(譬如多重抗药性结核病、艾滋病和非典型性肺炎)的时候,为了保护公众健康,仍然只有牺牲某些患者的人身自由,将其隔离起来以防疾病的再度扩散。但是“伤寒玛丽”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因为她没有发病,她是健康的。她甚至认为自己只是当局为了讨好那
些有钱人,向他们证明他们的健康利益得到了政府的“有力保护”的牺牲品。
卫生部门中还是有少数人为囚禁玛丽而感到愤愤不平。屈于种种压力,纽约卫生部提出只要玛丽隐姓埋名并从此离开该州,就不再囚禁她。但玛丽却坚决不愿接受以这种方式换来的自由。到了1910年,玛丽终于转运。纽约市聘用了一个新的卫生专员——恩斯特·雷德勒。雷德勒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人,他同意释放玛丽,但前提是玛丽必须定期向有关部门报告,并且不能再做厨师的工作。他甚至还为玛丽安排了一份洗衣女工的工作,这虽然是女性工种中收入最低且异常辛苦的工作之一,但是这份工作可以使玛丽避免将伤寒传染给他人。
玛丽获释后不久,她的男友布雷霍夫就死了,光靠她自己一个人,生活几乎难以为继。卫生部从1910到191 3年都清楚掌握着玛丽的行踪,但是到了1914年玛丽却“人间蒸发”了。这时,卫生部的官员们面临着另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他们渐渐意识到至少有3%的伤寒症痊愈者都成了病毒携带者,这个数目是庞大的,卫生部不可能等每个伤寒病人痊愈后挨个进行化验,因此他们就把焦点集中在食物处理人员的身上。卫生部随后通过了一项决议,即纽约市内的任何食物处理人员必须定期接受体检。对合格者卫生部将制发健康卡,以便规范管理。然而通过这种途径,他们仅发现了少量病毒携带者,大部分携带者都躲过了检查。
一个象征
1915年3月,伤寒症侵袭了著名的斯诺尼妇科医院,共有25名医生、护士和医院的工人被感染,并造成两人死亡。院方当即找来了乔治·索伯,他通过辨认笔迹才知道这位散播伤寒病毒的医院厨师布朗夫人其实就是当年失踪的“伤寒玛丽”。玛丽明知自己是伤寒病菌携带者,为什么还要做厨师呢?究竟是为了报复,还是生活所迫?卫生部的探员跟踪玛丽来到她在皇后街的住处。玛丽面对他们显得十分平静,似乎早就知道他们会来,探员们带她走的时候她竟没有一点反抗与挣扎。但是,面对这么一个名字等同于可怕疾病的女人,人们已经很难再对她抱有同情心了。
玛丽被再度幽禁到北兄弟岛上。和第一次不同的是,她开始渐渐适应这里的生活,还和这里的一些医生、护士成了朋友。就这样过了三年,卫生部开始允许玛丽偶尔乘船回纽约探望朋友什么的,但是必须准时返回岛上。就在玛丽被隔离的这段期间,卫生部对待病毒携带者的政策也变得更为灵活。原来作为食物处理人员的携带者,有机会接受再就业培训或者由政府发给停业补助;即便是不合作的携带者,也不会再受到像玛丽那样的待遇。
玛丽仍旧是一个伤寒病毒携带者,隔离中的她还在滨河医院得到了一份实验室技术员的工作。在北兄弟岛上度过了26个春秋之后,玛丽于1938年逝世,享年69岁。她曾经传染伤寒给47个人,其中有三个人死了。但是玛丽一直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从那时起,随着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伤寒症也日益消失。十年之后,能够治疗玛丽这样的病毒携带者的抗生素诞生了。但是,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的致命疾病不断出现,以至于一个世纪以前最初由玛丽引起的问题又再度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怎样才能在不践踏患病公民的个人合法权利的前提下行使公共卫生权力?
尽管玛丽早已被人们遗忘,但“伤寒玛丽”却没有,她依然是一个有力的象征,象征着我们对疾病的恐惧,象征着我们对为了保护自身,究竟能把措施采取到何种地步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