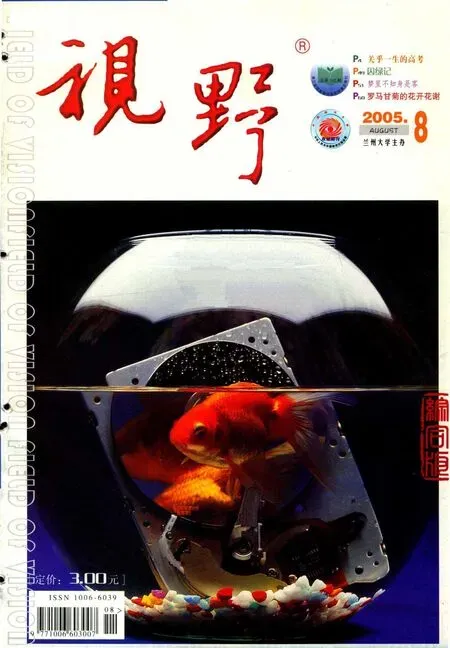大朋友,小朋友
郭韶明
Mentor源于荷马史诗
“大朋友”,这个熟悉而亲切的词听起来或许并不陌生,但询问身边的人,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你定义的大朋友就是年龄比你大的朋友吗?与好朋友、忘年交有什么区别?我们有父母、有老师,为什么还需要大朋友呢?
在我们还对“大朋友”存在模糊与质疑时,在国外,“大朋友”早已作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成长互助模式推广开来。
是叶祖禹先生将“大朋友”(Mentor)项目引进到中国的。作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美新路公益基金理事会主席,他一直很关注青少年的成长。在谈了引进初衷后,叶祖禹讲述了“大朋友”的历史由来: Mentor一词源于著名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俄底修斯在出发前把他儿子忒勒马科斯托付给他的挚友Mentor。此后多年Mentor一直关怀和辅导着忒勒马科斯,直到他成人。今天,Mentor仍然在人们心里代表着一个始终关怀我们、陪伴我们成长的“大朋友”。
1904年,“大朋友”作为一个公益项目在美国被推广开来。当时考特先生在纽约市的商政各界找出40位成熟稳健、有爱心的成功人士作为大朋友,一对一地带领40名需要辅导的青少年,与这些孩子共同面对成长中的困惑与烦恼,使这些孩子的心灵得到真诚的关怀。
一百多年来,此项目已遍布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使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受益。有关“大朋友”项目所做的调研显示,在参加“大朋友”项目的青少年中,76%减少了旷课次数,84%学习成绩有进步,60%减少了学校处罚,79%减少了帮派行为。据调查,大朋友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对青少年产生正面的影响:一、和别人相处的能力;二、学习的能力与成绩;三、师生、亲子、朋友关系。
耐心的倾听者和领路人
美新路公益基金“大朋友”项目负责人王王月介绍说,如今大部分孩子都是独生子女,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家庭已经不能成为孩子倾吐烦恼的出口。在学校,学生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沉重的学习压力和心理压力让孩子喘不过气来。从社会角度来讲,一些社会现象也正对孩子产生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如离婚问题、成年人的就业问题、家庭及社会的暴力问题等等。此外,随着城市化的推移,大量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者的子女,不得不面对不稳定的生活环境和城乡文化的差异。
“以上种种客观因素,都可能使这些正处在成长期的孩子们感到极度困惑与孤独,不知如何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他们的内心渴望着一个可倾诉的对象、一个可信任的朋友、一个领路人。”
其实中国的青少年在成长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大朋友,在人生的某一阶段或某件具体事情上给他们以启迪,只是这种大朋友处于一种随意的状态,并没有被人认识到。
去年,“大朋友”项目被正式移植到中国。通过招募志愿者,和中学生结成一对一朋友的形式,志愿者作为引路人和青少年共同面对成长的烦恼。
作为孩子最亲密的家长,是怎么看待“大朋友”的呢?对这一问题家长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极端:一种是质疑型,怀疑大朋友是否有足够的资格去帮助他们的孩子,会不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现在社会上是否还有这样无私奉献的人。另一种是接纳型,认为有家长、老师之外的大朋友给自己孩子一些启迪,更好地促进孩子成长,是一件难得的好事。
在叶祖禹看来,中国的家长通常有一种比较功利的心理,就是更注重孩子学习方面的提高,认为考大学才是最好的惟一出路。而美国则不同,他们更尊重孩子个人的意愿,让孩子自己选择要走的路。“我们最初没有认清这一点,所以遇到了很多挫折。”
家长们刚开始听过宣传,觉得这个项目不错,就参与了。后来有的发现对孩子的学习并没有十分显著的成效,就开始动摇。志愿者刘沐这样描述他所接触的家长:“他们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不愿意放弃对孩子有益的事情,另一方面又害怕新鲜事物对孩子造成的影响。”
14岁的陈晨和32岁的李
得知一位和大朋友结对子的小朋友也走上了敬老志愿者的道路时,我忍不住拨通了小朋友陈晨家的电话。电话中,14岁的陈晨表达清晰、思维缜密,一点儿都没有与陌生人通话的局促感。
“我觉得李就像邻家大哥似的,不像老师,很像朋友。从前我有点儿害羞,有什么话老憋在心里。李哥哥教导我要多跟人交流,现在我与陌生人交往自然多了。”
“说到去敬老院做志愿者啊,我就是觉得李哥哥把爱心都给了我,我也要把自己的爱心奉献给别人,尽我所能。”
陈晨口中的李,就是她的大朋友。一年半以前,两人结成对子。最初的交往,主要是辅导功课。陈晨的数学很差,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挺难熬,都提不起兴趣了”。李的介入,使陈晨开始有了转机。这种转机不仅体现在学习上,更体现在她的人生态度与处事能力上。
陈晨的妈妈徐俊仙是残疾人,家里开了间杂货店维持生计。陈晨哪儿都想去,可哪儿也去不了。妈妈理解她,“别的家长都有钱有地位,孩子见的世面多,而我们家孩子特自卑,哪儿都没去过。”自从李走进了这个家庭,陈晨终于也走进了外面的世界。她去过科技馆,还去过法国大使馆的阅览室。在学校组织去敬老院帮助老年人时,陈晨骄傲地告诉别人:“我已经在敬老院做了好久志愿工作了。”
从一个孤僻自卑的小姑娘到敬老院里充满爱心的小志愿者,陈晨的变化令人吃惊。
当然,这只是众多“大朋友”项目在中国的一个小故事。更多的故事或许已经发生,或许正在孕育。这种新的模式正在中国成长,虽然步履蹒跚,但却一直在坚定地向前走。
专家视点:
弥补成长
陆小娅
现在城里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对这些独生子女来说,父母是最主要的支持系统。但是,到了青春期,他们很多苦恼并不愿意向父母说。两代人成长背景的不同,使得父母很难理解孩子,何况有时父母本身就是压力和烦恼的来源。
老师本该是孩子的另一个支持系统,但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老师很少有时间去倾听学生,帮助学生解决困扰,甚至很多老师对学生的内心世界完全不了解,也没有兴趣去了解。
而在多子女时代,当孩子碰到麻烦时,会有哥哥、姐姐,甚至表哥、表姐帮助出主意、想办法。这些哥哥姐姐因为是同辈,没有距离感,有时比父母更容易理解自己。同时,他们又年长几岁,生活阅历和经验相对丰富,因此能帮助遇到麻烦的孩子从更多角度想问题、想办法,而不是意气用事。
今天的独生子女一代失去了这种天然的资源,他们只有上一辈的父母和同龄的同学,因此在遇到压力和麻烦时,支持系统变得相当脆弱。能不能在父母和同学间再加上一根支柱呢,比如说,帮助和鼓励孩子结识一些健康进取的“大朋友”?
“大朋友”具有多功能性,他们兼具榜样、老师和朋友三种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独生子女成长中的一些缺失。
国外成功案例:
“精神姐姐”改变人生
瑞秋·怀特是非洲裔美国人,而珍姆·考珀出生在非洲的利比亚。两个女人有着相同的种族背景,但由于来自不同的国家,很容易看出她们之间明显的不同。
9岁时到美国对于珍姆来说是个噩梦。学校里的孩子们嘲笑她传统的利比亚装束,取笑她的非洲口音。珍姆开始努力克制她的口音,并尽量穿戴得和她的那些同学们一样。很自然,她的家人对她放弃自己“非洲特色”的做法十分不理解。
珍姆的妈妈和瑞秋是朋友,认识到女儿面临的问题,可能需要另外一个成人关心,就把珍姆介绍给瑞秋认识。
瑞秋在1993年就开始参加一个名为“精神姐姐”的“大朋友”
项目。瑞秋接受的培训提供给她一个工具叫做“响应倾听”,就是非常包容和近距离地倾听他人,仅仅问少数关键性的问题。通过“响应倾听”,瑞秋充分理解和接受了珍姆独特的种族和文化背景,以及她所面临的问题。
得到一个成人朋友充分的关切和支持,珍姆开始放松和接受自己,并且为自己是谁而感到骄傲。她开始释放和表达真正的自我,并重新操起非洲口音,还重新燃起对舞蹈的热爱,报名参加了费城颇具声望的自由剧院暑期舞蹈课程。
(鱼丝丝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