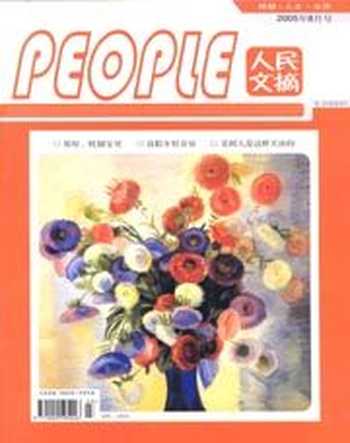在温哥华等待樱花
凯 吉

当我第一次来到温哥华时正是春天,满街的樱花长长地排去,如一群侍女,落红纷纷,飘啊飘地铺起了天盖起了地。对一个外乡人来说,或许会睹物伤神,暗自垂泪。然而对于我,对这个世界充满抱负的我用力提提行李,在心里喊了一声:温哥华真好,樱花真好,我要永远生活在这里。
我从大陆来到温哥华,由于语言问题很难找到好工作。多亏三叔的照顾,三叔是一个在温哥华做了十几年卖花生意的老移民。他的店很小,住的街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很破。但卖花的却很多,整条街几乎都是,中国人占多数。平时,我帮三叔打理一下生意,闲暇时便一个人去市区,像一条游进大海的小鱼,我不和谐地穿行在温哥华的大道上。但我很高兴,因为我有生以来见到了这么多的外国人。我想有一天有了钱,我要向他们一样活得这般悠闲,就在温哥华,永永远远,直到老去。
一天,店里来了个老外,是个女的,名叫MARY。就是这个名字让我刻骨铭心,不懂英文的我像小学生记拼音一样把这几个字母记在了心里。她影响了我,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爱。
“中国人,有郁金香吗?”她操着流利的中文。
“有有有……”看着她白皙的脸我一时不知怎么说。
最终她挑了一盆,看着她这朵嗅嗅那朵嗅嗅,我出神了。
“可以帮我搬到车上吗?”她直视着我问。
“行啊。”我立即动手帮她搬出去。
要走了,她发动车,伸出头向我挥挥手:“谢谢你,中国人。”风一吹,她的头发美极了,金黄的颜色。车子走了,留下傻傻的我。
故事也许该到此为止,可并没有止。后来,MARY又来了几次,我们渐渐地熟了。有时她并不买花,只是来跟我聊一会儿,聊中国。她说她喜欢中国。我也不再拘谨了,跟她说一些地道的中国话。
好几次MARY用车带我去STANLEY PARK。MARY说那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大公园之一。
“要是以后每天都来这里就好了”我惬意地说。
“你永远在温哥华就行了”MARY很轻松地说。
“不可能。”不知为什么,此时我一下子将心中的梦想否定了,那么干脆。
MARY也无语了,她只是看看我,又看看前面。那种眼神我记住了,不好描绘,只是记住了,当时形容不出来。
就这样我跟MARY什么都谈,包括许多不能对三叔说的事,也许当时都是年轻人吧。MARY很少谈她自己,除了她的名字,我对她一无所知,也从没故意问过。她家住哪里?她父母做什么?……这似乎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我只知道我们在一起很快乐。樱花又开又落。
我在温哥华的两年过去了,MARY是这两年里我惟一的朋友。
一天晚上,三叔喊我到他房间。
“小胜呀,你跟那个老外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呀。”
“没什么?”
……
“我不说你了,如果你有那种想法,趁早死了心。”
我没有说话,没有反驳。
那夜我失眠了。忽然在心里意识到:MARY好几天没来了。我寻思着三叔的话,觉得三叔捅破了自己心中的秘密。我确实是喜欢上MARY了。什么时候开始的?第一次她来买花的时候?坐在她车上的时候?在STANLEYPARK跟她一起坐在草坪上的时候?……可我只是一个卖花的,我没有权利去喜欢她,可……我明白三叔说的话,我该怎么办?结束两年的交往?坦诚地告诉她?那夜我真正体会到了为喜欢一个人的无眠。
第二天,我无精打采地打理着生意。看着外面,这已是第三个春天了。这些美丽的樱花一如我初来般绚烂。只是我已不是当初那个我了。一开始我只有往前冲的冲动,现在却因为一个人而怀疑我能否冲得动,有没有能力冲得动。温哥华并不因我而伤心,樱花也并不因为我而美丽。
浑浑噩噩的日子过了好几天,突然MARY来了。还是那样灿烂的笑,随意的装束。她说这次要带我去一个更好的地方。我没有吭声。MARY奇怪地看着我。许久,我说:“MARY,我带你去看樱花吧。”“樱花?满街都是呀。”MARY不解地问。“走吧。”我不由分说地拉起她的手。
是呀,那天满街都是樱花,全世界都是樱花。走着走着,我突然随意地说:“MARY,I LOVE YOU”MARY一下子站住了,或许这惟一一句我说得最好的英语让她措手不及了。我继续若无其事地走,心里是无所知的状态,后面传来一句:“我也喜欢你。”
汉语,我虽在异乡,却从未生疏。但这句却宛如天籁之声,让我刹住了脚步,让我花了几乎一生的时间去理解它。三叔是错的,只要真心地爱,可以找到另一颗爱你的心。MARY从后面跑上来抱住了我。我陶醉了。
那天是我30多年的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难以忘记,永藏心底。
晚上回去我坦诚地告诉了三叔,我固执地认为他对外国人有偏见。
“你懂什么?”三叔生气了。
“你懂什么?爱,你懂吗?”我顶了三叔一句。
三叔没有在乎我猛地转过身。
我想冲出去。
“站住!”三叔喝了一声,“你没有钱,你什么也没有。你凭什么给她幸福。爱,爱能当一件大衣,在她寒冷的时候给她披上吗?你们的爱只能像外面的樱花,花开的绚烂,可没有一朵有结果的时候,有吗?这种爱只能是来的快去的也快……”
我几乎快被击到了,踉踉跄跄地冲了出去,往前跑,沿着整条街。樱花在脚下,竟是那么多,落得真快,真多呀……跑着跑着,我再也跑不动了。倚着一棵樱花树,嚎啕大哭起来。温哥华呀,那是我第一次将眼泪洒在这里,你还记得吗?一个卖花的,一个外乡人,一个穷小子,我凭什么娶她?如樱花漂亮般的姑娘。
后来我和MARY说了,她没哭,只是静静地走了。一点表情也没有,再也没有来找过我。
我又成了以前的我,只是心中多了一份心事。过了几年,三叔也走了,三叔没有家室,生意留给了我。樱花依旧又开又落,我忙碌着店里的生意,在心里,等待着下年的樱花。慢慢地店面扩展成卖日用品为主了,生活也好起来了。我娶了妻,有了女儿。
陈年往事似乎已不再。女儿很讨人喜欢,她特别喜欢樱花。每年做爸爸的我总会在樱花初开的时候喊她:“去看樱花吧,MARY。”
(侯东生摘自《多伦多信息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