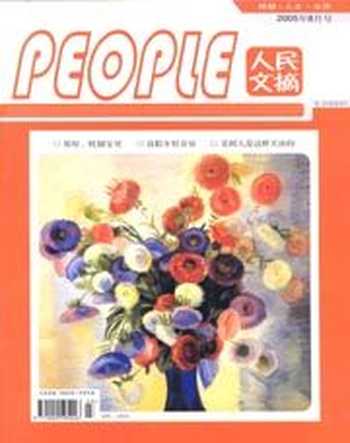天空中弥漫的独特气息
黄正平

如今的萨特也如一盘炒鸡蛋,人们在里面添了不少料,很难再找到其原味了。
2005年的巴黎,处处烙着萨特的标记。
塞纳河边的树绿了,春风中幽幽地带着萨特的独特气息,时淡时浓,似远犹近。
2005年是萨特100周年诞辰和25周年的祭日。
从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之丰富来看,人们并没有忘记萨特,包括他的对手。虽然,这种场面或许是萨特所不喜欢的。
自幼失去父亲,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萨特,从小就自视甚高,自律甚严。他在年轻时给自己立下的人生目标也许是绝无仅有的:“我要同时成为斯宾诺莎和司汤达。”也就是说,既要当一个一流的哲学家,也要当一个一流的文学家,而这成为了现实。
他的作品在20世纪哲学和文学领域中都是少有的经典。法国哲学教授让·吕克·南希近日在《世界报》上著文说,萨特是个古往今来从未出现过的两面神:没有一个哲学家像他那样在文学海洋中游弋,也没有一个文学家像他那样大举进行哲学操练。
对此,萨特的反对者并不以为然,说萨特所做的一切,就是处心积虑地要向人们表明,他是一个怎样的天才。
有意也好,无心也罢,有一点谁都不会否定:萨特是个勤奋的人。除了去世前几年间因半失明而辍笔外,他一生中从没有停止过写作。萨特把笔耕当作是一种乐趣、一种需要、一种人生的基本支撑点。他这样说:“我没办法让自己看到一张白纸时,不产生在上面写点什么的欲望。”
萨特喜欢去一家咖啡馆写作。他每天早上9点到咖啡馆,开始工作,奋笔疾书,直至中午。出去吃饭和休息后,下午2点又回咖啡馆,继续工作到晚上8点。晚饭后则在那里接待朋友。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实际上是咖啡馆定型的。
咖啡馆叫“花神咖啡馆”,坐落在圣·米歇尔大街的一个路口。作为存在主义的发源地,咖啡馆现在已成为巴黎的景点之一,是怀旧的知识分子爱去的地方。
不大的店堂内飘散着特别浓郁的黑咖啡香,只见一桌一桌的有好几圈人,分别在小声地讨论各自的文稿,也有人在埋头写作。
这分明是一个文化俱乐部,人们感慨地说:“萨特气息犹在啊!”
萨特的魅力大约还在于他的近于狂热的入世精神。
他这样看待人的社会参与:人的出生是由于他的先人撒了几滴精液造成的结果,他的出生或不出生本来是完全偶然的;人的存在因此并不是按照某种事先设计好的路线而规划的,人应当“自由地”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应当完全介入到自己生存的社会中去,以自己的行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这种精神使他很自然地对当时的社会持批判态度,而对社会革命大表支持。
整个60年代,萨特在法国知识界如日中天,是无可争议的无冕之王。德里达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时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跟着他(萨特)走。”
萨特在他晚年以及死后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认为他搞错了很多事情。例如盲目支持造反,把年轻人引入暴力歧途、极端主义等等。批评愈演愈烈,到了将萨特全盘否定的地步:他除了在政治上一无是处外,学术上也毫无可取之处。同时,萨特的私人生活,萨特与加谬、梅洛·庞蒂这些同时代大文豪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成为评论的热点。
到了这一步,已经不再是学术上的争论了。人们把这种全面诋毁现象叫做“萨特恐惧症”。
萨特曾在美国一家杂志写过一篇哲学杂文,其中说:“我想创造一种炒鸡蛋,期望它能表达存在的虚无。但到烧成,它却并非如此,只飘散出一股奶酪味。我眼睁睁地看着盘子里的它,而它却不回答我。我试着把它端到黑暗里去吃,但这一点儿也没用。马尔罗(萨特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建议我在里面加辣椒粉。”
如今的萨特也如一盘炒鸡蛋,人们在里面添了不少料,很难再找到其原味了。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萨特对当代社会发出的哲学疑问,他在文学领域所作的探索,以及他作为一个文人所表现出的罕见的政治热情,将继续启发人们的思路,引起人们的心动。
(黄 林摘自《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