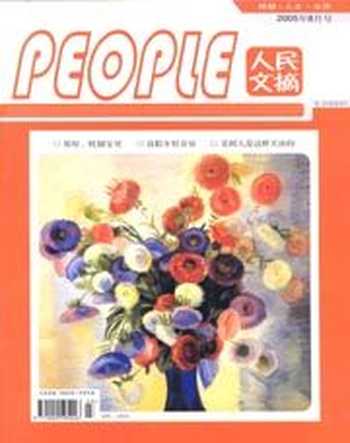为自己画一个姑娘
王宏甲

这是我插队时挂在土屋里的一幅画像。
“她是谁呀?”村庄里没人知道她是谁。
我也不知世上是否有一个长得跟她一样的女子。
“她”是我在插队的岁月中画的。
我12岁上中学,刚读完初一,“文革”开始,我的读书岁月结束了。突然出现的变故,不仅仅是读书的日子中断。我的父亲是个小镇医院的院长,作为医生他一生谨慎,一辈子做过的一桩最勇敢的事,就是把自己杀死。15岁半,我去上山下乡。大卡车把我们拉到福建北部山区的一个渡口,那个日子,阳光铺满河面,对岸的山路向我们迎来,我们还听到了鸟声……不久,我躺在没有窗户的茅屋里怀想山路,感到从前的黄金时光已经隔得像放牧那样遥远。
15岁半,在陌生的山村开始劳动生活,那里无疑有我无法回避的艰难。我插队的那个村子叫火爬山,总共13户,我是第13户,村子里就我一个插队知青。我的住房是生产队放肥料的茅屋,把肥料搬走了,安上一个竹床,就安置了我。我做饭的土灶也是农民们像筑土墙那样用泥巴筑起来的。南方多雨,下暴雨的日子,茅屋漏了,我就要在锅台上支一把伞,用来阻挡雨水落进锅里。但这似乎不是最难的,最大压力是精神上的压力。
由于我有“家庭出身问题”,一度,中学时代与我要好的男女同学都与我疏远了。这似乎不能怪他们,他们的父母要求他们不要跟我走得太近。随后,同在一个大队插队的知青陆续招工或者重新上中专、上大学走了,每次他们走向新的岗位,按当时的说法都说是应国家的需要走了,而我却像个国家不需要的人。我不知我那时精神上的压力同今天学生们读书的压力是否也有点相通。
在缺少朋友的日子里,我忽然想,我要为自己画一个女友。
人类的这种情感,神秘而神圣。那时,我在一本杂志上见到一个形象,是一幅油画。我从未学过油画,村庄里也没有油画颜料,但我决心到县城去买。
我得步行30里到公社,才能搭上去县城的班车。那是个脚下有阳光的日子,我出发了。你可以想见,那是我插队岁月中一件隆重的事情!隆重得不亚于农民娶亲要到城里去“剪布”来做嫁衣。
我回来了。画在何处好呢?那时我所能找到的最理想的纸是一张奖状,我就把她画在奖状的背面。
不管生活出现了怎样的感伤和孤独,那是一个幸福的日子,我要来画一位姑娘了。
光明是这样创造的,孤独是这样遁去的。这就是那个时代我心中最美的形象,让她刘海透着金色的阳光,一条小辫也朝气蓬勃,望着她,我能听见《让我们荡起双桨》……就在这个形象中,在她遥望远方的目光中,有我不肯舍弃的追求和期盼。
我插队整整8年。在我意志力就要崩溃,人就要堕落的日子里,总是她以微笑一次次把我召唤。在她目光的注视下,我读了我那时所能找来读的许多书,许多是没封面没封底的书。没书看的日子,我还一页一页地读过汉语字典。后来还津津有味地自学完了初中阶段的数学和几何。然而要同自己的悲观、失望作战,并不简单,8年中那似乎是一场持久战。在我心空黯然的日夜,她就是我那没有窗户的小屋里的太阳。
告别8年的插队生活,我把“她”带回故乡之城,再后又带来北京,珍藏至今,像一件文物。现在想来,在我走向社会,由少年而青年的岁月,画一个形象鼓励自己,看来不算虚无。那里,同样有我的黄金时光。
或许,还可以这样表述:人生何谓美好,只有追求美好才有美好。何时以为世无美好,放弃追求,美好就结束。人若失去自己内心的有力支持,自信就会瓦解。望着我自己描绘的美丽形象,我不肯丢弃,就这样一程程走过来。
也可以说,我曾经每天都望着她,在内心深刻地爱她。这故事够天方夜谭的吧,但天方夜谭确然是阿拉伯民族的骄傲,是真正的沙漠中的神灯。
(蒋 鹏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