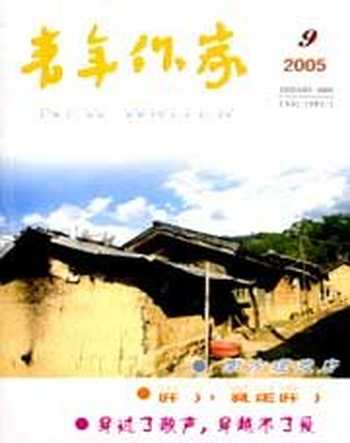白塔
流 马
沉睡者的身体猛然往后仰去,被一个类似布袋的东西挡了一下,反弹回来。在他身后,一个女子发出刺耳的“哎呀”声。他被这“哎呀”惊醒,回头去看,发现女子屁股翘起,一颗大头正抵在汽车车头的玻璃上。车子停了。驾驶座的门开着,司机不见了。
沉睡者抬起头来,面对一车的乘客。他们都一种表情:茫然又迷惑。车里的人真多,狭窄的过道也站满了。沉睡者还是幸运的,没有站着,屁股坐在发动机的大铁盖上。但坐在铁盖上的,不只有他一个。左边,是个老头,右边,也是个老头,两个老头的屁股都很硬,将他的屁股挤到铁盖的边缘。在他背后,与他背对背,屁股顶屁股坐着的,就是那个大头女子。她原本叉开双腿,骑在铁盖上,坐在驾驶席和副驾驶席中间,后背毫不客气地倚在沉睡者的背上。沉睡者一上车就沉睡了,将头埋在两腿之间,身体弯曲着,正好是大头女子的靠背。
坐在副驾驶上的那个乘客慢悠悠地点了一支烟,回头看了看车里的人,“哈——”他发出一声很尖的笑声。他坐在最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自然最清楚了;好像是他导演的一场恶作剧。大头女子不顾头的疼痛,爬到驾驶席上去,脑袋伸出驾驶座的门,向外看。乘客门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开了,但是车里的乘客一动也不动。
一个多小时以后,一个警察骑着摩托不紧不慢地过来,后面跟着一辆面包警车,车上下来几个人。那几个人拿着皮尺在车外量来量去,一个叼着烟卷的人在一个本子上写字,还有一个人在拍照,前后左右将车拍了个遍。最后,警察将车里的乘客全部撵下来。乘客只好都站到马路牙子上,站成一支不太整齐的队伍。大家都在打量这辆车,好像他们不是从这辆车上下来的。
这是一辆白色中巴,很破旧。车身上沾满厚厚的尘土,尤其车的尾部,简直像个刚刚在泥水里打过滚的猪屁股。这辆车还真的像一头受到惊吓的猪,歪歪地站在马路中间,一动不敢动。它的眼睛瞪得很大,无辜地看着围着它的人。它那突出的鼻子往前伸着,似乎要拱起那个躺在嘴巴下面的家伙。
他,那个坐在发动机铁盖上睡觉的人,站在马路边,看见几个人把躺在车底下的人抬走。只剩下那辆空车横亘在马路中央,孤零零地。两边不断有各种汽车呼啸而过。那辆汽车就像一个幻影,在车流中忽隐忽现。
不一会儿,警察让司机将空车开走了。只剩下这一堆乘客,站在马路牙子上。
他点着一支烟,朝四下看看。身边恰好有一个站牌,上面写着:白塔。
他盯着这个站牌看了很久,这个名字让他想起什么,或者他只是想记下这个站名。
一辆马车从身前得得走过去。马车上有一男一女。男的拉着缰绳,女的靠在男人肩上,有说有笑。他跟那个男的打了一个照面,觉得那男的长得和自己有点像。他这样想的时候,马车上的女孩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旋即转过头,脑袋歪靠在男的肩上,拍打着男人的胸脯,发出一阵笑声。那个男的没有回头,扬起鞭子,在空中打出一声爆响,马儿拉着马车跑远。
这是什么季节,有这么大的风。大风扬起马路上的沙尘,吹迷他的眼睛。他的烟也被吹灭了。他将烟卷滤嘴咬烂,扔在地上,让风吹走。他跑到路边一个小店的门口躲避大风。太阳亮白亮白的,照得整个马路明晃晃,但是一点热度也没有。这还是上午,太阳一点一点、不慌不忙地向天正顶爬。他眯着眼看了一会儿,没有云彩,无法确定太阳是否移动。但太阳毫无疑问是移动的。他很不耐烦,又想抽烟。风还是很大,无法打火。
店里有一个女人,在用一根很粗的擀面杖擀饼。饼擀得并不大,但是很厚。他观察女人从揉面到擀饼的一连串动作,推测她一定很有力气。女人左边有一个蜂窝煤炉子,炉子上有一个平底的铸铁锅。平底锅的直径只比饼的直径大那么一点点。饼就是在这种锅里面烙出来的。女人右边是一个箩筐,箩筐被一块棉布遮盖着。他走过去,掀开棉布,几个烙好的饼子整整齐齐地摞在里面。
“多少钱?”他问她。
“一块钱。”她抬起头,咧开嘴笑笑。
“吃不了一个。”他说。
“可以切开,你要多少?”
“一半吧。”他说。
女人放下擀面杖,搓了搓手上的面,从箩筐里拿出一个饼子,放在案板上,操起一把菜刀,在那个饼子上切了一个“十”字。饼子被分成平均的四块。她拿起其中的两块递给他。他给她要了一个方便袋,把饼放在袋子里,手隔着袋子捏住饼子,吃了起来。原来还是发面油饼,有半个拇指那么厚;饼的两面都烤得很焦,里面很软,还分了好几层,一些葱花、花椒颗粒,椒盐点缀在各个夹层里,饼做得很劲道,很好吃。他很快吃完一块,将剩下的一块放回方便袋,提在手里。
他将手里的烟晃了晃,问那女人:“有火吗?”女人将一个铁钩子伸到炉子下面,示意他稍等。
“风太大了。”他说着,将手里的打火机在女人眼前摇了摇。
女人示意他不要站在店外,他便走进去。他现在可以用打火机点烟了,但他没有。他看着那个伸在炉子下面的铁钩子,出了一会神。女人将铁钩子从炉子下面拿出来,举在他面前。铁钩子尖尖的顶端烧红了,活像宠物狗勃起的阴茎,从皮毛里吐出来。他将烟卷凑上去,伴随着“咝咝”的声音,冒出一阵烟气。女人帮他点完烟,照旧在擀自己的饼子。他站在店门口,注意看马路牙子上的人。
说快也真快,太阳这就爬到天正顶了。他觉得自己离开集体太久,重新走到马路上去。至少两个小时过去,马路牙子上的乘客都有些不耐烦。大头女子在人群中走来走去,问这问那;那边几个农民打扮的老头子正不着边际地闲扯,他们倒一点也不着急;几个年轻人也都很沉得住气,有的托着腮蹲在地上,有的站着,翘首望着车来的方向。大家都在互相询问,互相假设,互相求证,用这种方式互相安慰。太阳又一点一点开始往下滑了。它往下滑要比往上爬显得快,像是有了加速度一样。这些人还在等。
他再次离开人群,跑回店里。
女人换成了男人。
男人很清瘦,脸上胡子拉碴,好像有好几个月没洗脸了,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男人以为他要买饼,他便举了举手里剩下的半块饼。男人皱起眉头。他注意到男人额头上有不易察觉的一块淤伤,被凌乱不堪的头发有意遮盖住了。
“这里是白塔?”他问。
“就是。”那男人的回答显得有气无力,也许他是懒得回答。
“不对啊,白塔应该还在前面。”
“这就是了。”
“地图上不是这样的。”
“这就是了。”那男人机械地回答他。
“是不是有两个白塔?”
“那不知道,反正这里就是了。”
“我说的白塔那里有座佛塔。”
“这里也有佛塔。”
“我说的佛塔有好几百年了。”
“这个塔是明朝的。”
“是吗?”这人有些兴奋,“是白塔吗?”
“白的,可白了;晚上都白得放光。”
“那你听说过塔里闹鬼的事情吗?”
男人一下子警惕起来,上下打量他好久,冷冷地问道:“你怎么会问这个?”
“我说的那个白塔里面经常闹鬼,我是去捉鬼的。”
“嗤——”
“你们这里若有鬼,我也可以捉。”那人半笑不笑,让人猜不透他是真的,还是开玩笑。不过不管是玩笑,还是认真,男人对他的话没有表示一点兴趣,但也没有厌恶或者不耐烦。他的头老是低着,似乎怎么也抬不起来,但是眼睛却使劲往人身上看。这种看人的方法很隐蔽,不注意还以为他并没有看你,实际上已经将你琢磨个七八分。他问这个磨蹭着不走的人:“你是那车上的?”那人点点头。
“你们怎么还不走?”
“没人让走。”他说。
“谁管你们?”
“随便谁,公安局啊,还是交通局啊,汽车站啊,至少得有人来打个招呼啊,总得有个说法嘛。”
男人发出冷冷的笑声。“不会有人管你们啦!”他弯腰抬起平底锅,看看炉子的火是否还旺,抄起地上的铁钩子,钩了钩炉膛,钩出一些灰白色的炉灰。
“他们不能不管我们。我们买了票。”
“真稀罕,买了票就了不起啊!”男人很鄙夷这人的天真,突然把火钩子扔到墙角里,抄起擀面杖,在案板上狠狠敲打起来。客人觉察到他的不太正常,就准备离开,刚抬脚出门,又被男人叫住了。
“你真的要等?”
“不然,车票岂不白买了?”
他起身搬了一个小马扎。客人以为是请他坐的,但是男人还是将小马扎垫在屁股下面。“那你不住旅馆吗?”他双臂抱胸,边问边吹蜂窝煤炉子上堆积的煤灰。“今天不可能等到了,你看这天。”
“看来我要住下了。这里有住处吗?”客人看看天,面无表情。没跟他打个招呼,天就无声息地黑了个严实。
“我倒是能介绍你一个,价格好商量呢。”
“能凑合一晚上就行。”
“那还有错。”他还是那副不肯正面看人的猥琐样儿。这让客人偶感不快。
“你怎么称呼?”客人问男人。
“我姓张。”
“老张,那女人是你老婆?”客人提起手里没吃完的饼,晃了晃。
“我老婆。”
“老张,你老婆挺好看。”
男人不知道该对这句话做怎样的反应。似乎夸自己老婆好,是危险的。可是危险在哪里呢?他又拾起火钳子,敲打起地面。客人见这人听了这话竟然不像刚才那么凶巴,心里有些猜疑便有些落实了。
“老张,今晚我能住你家么?”他继续问。
“最好还是找个旅馆住。”男人的声音很虚弱了。
“你老婆烙的饼很好吃。”
“嗯啊。”
“你平时在店里吗?”
“我有我的事。”
“你做什么的。”
男人没有回答,只是继续用尖尖的火钳敲打地面。
“有热水吗?我有点渴。”
“要收钱的。”
“收什么钱?不就喝一口水吗?”
“那不行,水也有水钱。”
“要是你老婆在,保准不要钱。”
“你想怎样?”男人丢下火钩子,站了起来。他很瘦小,站起来也没有客人高大,而且骨架也窄,倒显得客人比他还有压迫感。他的眼睛无力地在客人的脸上盯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弯下麻秆一样细的腰,封上蜂窝煤炉子,提着擀面杖出来,锁上门,带着客人进村了。这个时候天竟完全黑了下来。客人看了看马路上,那些人还在等。他们也会住旅馆吧。他想。
“哎,我们明天见——”他朝那群人大声喊道,但是没人理他。
“干嘛拿着棍子?”客人不解地问男人。
“这是擀面杖。”
“防身吗?”
男人走在前面,不理客人。在村里七扭八拐,到一个院子门口。开门的果然是男人的老婆。
“来了。”女人说,仿佛已经知道他要来似的。
“来了。”客人说。
“我把他带来了。”男人将擀面杖交给老婆,转身回去。
“好好看店。”老婆扳着门框嘱咐男人。男人转过身来,悄声对女人说:“他刚才问起白塔……”
院子很大。五间大房,都涂着白浆。两间西屋,大门和西屋相连为一体,都是红砖墙。靠东院墙有一排鸡舍,用塑料网圈起来。南边没有墙,能够看到街上;只有一个猪圈隔着。院子里栽了许多树,椿树、杨树、槐树,都是乡下常见的树木。主妇正在院子里忙活。从压水井里汲满水,倒进正屋屋檐下的水缸里;那边炉子上的热水烧开了,她放下水桶,从鸡舍旁拾起一个木盆,走进一间屋子,不一会儿又端着木盆出来,里面盛满打碎的草料细末,走到炉子边,提起那壶开水,倒进木盆里。她用一根木棒搅拌好木盆里的草料,重新放到鸡舍边上。鸡舍里的鸡一拥而上,从塑料网里探出脑袋,啄食草料。她又从水缸里舀了一瓢冷水倒在木盆旁的瓦罐里。最先啄食草料的鸡烫坏了嘴,只好将尖尖的嘴伸到瓦罐里去降温。主妇并没有急着招呼客人,只是在院子里来来回回,企图将一切收拾停当。有时她会停下来,直起腰,擦擦额头,或者在围裙上擦擦手。等她将猪食也弄好,又去洗衣服了。
客人打算先洗洗脸。他走到压水井旁边,双手伸向出水口。主妇压了一下,清冽的水就流到客人的手中。他很快将那一捧凉水捂到自己脸上,那些水顺着他的手臂流淌,滴在裤子上和鞋子上。他不管这些,只是一遍一遍地洗着,抬头看一看压水的主妇,说一声:“真舒服。”自己就笑了。主妇给他找来毛巾,他擦完脸,站在旁边看主妇洗衣服。
“你要看白塔?”
“有吗?”
“有的,但是不让看。”
“为什么?”
“里面有鬼。”
“怎么会有鬼?”
“都这么说。”
“你去过吗?”客人问。
“去过呀。”
“见到鬼了吗?”
“哪里有鬼。”
“这不就对了吗,带我去。”
“你真会捉鬼?”
“那还有假。”
“那你见过鬼吗?”
“鬼都怕我,哪敢露面啊。”
“那好,你先去睡一觉,一会叫醒你去看。”
“现在不能看么?”
“现在去碰不上鬼啊。”主妇嫣然一笑,让人心神一荡。客人感到奇怪,起先在烧饼店的时候怎么没发现这一点呢?
客人被主妇领到西厢房。里面除了有一张床之外,主要放了许多粮食。进门的时候,突然停电了,主妇从抽屉里拿出一截小蜡头,点着,将一只茶碗反扣在桌子上,滴一些蜡烛油在茶碗的碗底,将蜡烛头粘在上面。客人躺在床上,眯缝起眼睛,看着蜡烛头跳跃的烛火,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他觉得自己眼皮很沉重,无论如何睁不开;而这时候恰恰有人在叫他,还用手来回推他的身体。他很烦恼,抬起一只手去驱赶那只推他的手。他感觉那只手像一只讨厌的蚊子,总是在耳边嗡嗡嗡,就是赶不走。他太疲劳了,懒得理那只不让他睡觉的手。他开始做梦,全是梦见手。墙壁上长出手,地上钻出手,空气中飘着手,就连这张床也伸出两条胳膊来抱住他,将他越抱越紧。有的手在摸他的脖子,有的手在掀他的两瓣嘴皮。他还听到那些手在唧唧喳喳地说话。它们说一定要掀开他的嘴,才能将东西放进去,不然,他就看不见白塔。它们又说眼皮睁不开放进去再多那玩意也没用。它们又想办法将他的眼皮掰开。可是他的眼皮太沉了。不但那些手这么说,连他自己也觉得眼皮就像两道死锁的门,怎么撬也撬不开。他又想自己是这道门的主人,应该是有钥匙的。他于是伸手去摸自己的裤带,钥匙应该别在裤带上。他摸了半天,裤带上光光的,什么也没有。他很灰心,觉得这眼皮是无论如何也睁不开了。那些手们对这双眼皮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它们只好去干别的。他觉得自己的裤带开了,有一只手隔着内裤摸他的下身。下身“嗖”的一下就站起来。他猛然睁开眼睛。他听见那些手发出笑声,说原来钥匙在这里。他坐起来,驱赶走那些在他两腿间忙活的手,重新将裤带系上。这时,桌子上的蜡烛头突然倾斜,大滴大滴的蜡烛油都滴在桌子上。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是一些手将那反扣着的茶碗掀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小人儿。那些手捧起那个小人,放在客人的大腿上。小人突然变大了,竟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女孩对他笑个不停。他有些喜欢,但又觉得这个女孩面熟,不知道在哪里见过。
“你怎么来了?”他问女孩。“我偷偷跑出来的。”女孩只是扳住他的脖子格格地笑。“你爹娘不知道吗?”“我给他们下了安眠药。”“你家的狗儿猫儿的也没看见吗?”“我给它们蒙上了眼睛。”“马儿驴儿呢?”“我给它们添了夜草。”“猪儿羊儿呢?”“我把它们放到山坡上去了。”“鸡儿鹅儿呢?”“我把它们的脖子拧断了。”“那,你家的门神也看见了。”“我把它们的眼珠子都用墨汁涂掉了。”“你真有办法。咱们什么时候走?”“别急嘛。”女孩笑嘻嘻地去解他的衣扣。女孩格格笑着,他也不阻拦。他把女孩平放在床上。那些在空中飘着的手一起帮忙,将女孩和自己脱了个干净。两人在床上翻滚了几下。女孩说:“走吧,再晚就看不成了。”那些手儿帮他们穿好衣裳,从后窗里爬了出去。
“我们去看什么?”
“白塔啊。”
“为什么要去看白塔?”
“不是你要去看的么?”
“可我现在不想看了。”
“那你想看什么?”
“想看你。”他又将手伸到女孩的胸上。那些手没有跟来。
“我也是鬼呢。”女孩挡住他的手,突然面孔放出光彩,高兴地跳了起来,“快看,快看。”
“什么?”他的眼前一片白茫茫,什么也看不清。
“白塔,白塔。”女孩兴奋极了。可是他却什么也看不到,四周都是白茫茫,根本没有什么白塔。他很着急,摇着女孩的手,一遍遍地问:“在哪里,在哪里?”女孩生气了,扔掉他的手:“你连眼睛都没睁开,还问在哪里在哪里;这怎么能看得着啊。”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闭着眼睛,于是拼命睁眼,可是那双眼皮就是死沉死沉,怎么也睁不开了。他禁不住用手抠自己的眼。
“啊——”他大叫一声,从床上坐起来。他看了看那只小蜡烛头还在不紧不慢地烧着,这才回过神来,原来只是一个梦。这时门开了,主妇从外面进来。“啪”的一声,按亮了电灯。“来电了。”她说,“我听见你喊,就进来了。你的眼睛怎么了?”主妇很关切地问他。主妇不慌不忙地吹灭了蜡烛头,从桌子上拿起一块镜子,给他照。他的眼皮被他抠出血来。主妇出去,带回来一瓶紫色的药水,给他涂上。
“几点了。”
“刚到12点。”
“你丈夫回来了吗?”
“他不回来;在公路上看店。你怎么了?”
“只是做个梦。”
“是不是太累了。你饿吗?要不要弄点吃的。”主妇一直站在床边,屋子里没有坐处。
“我不饿,你坐吧,有水喝吗?”
“等等。”女人走出去,不一会儿,提着一个暖水瓶进来,另一只手里提了茶壶和一只茶碗。她给客人沏了一杯茶,在桌子靠近客人的那边推了推。客人端起茶,一口喝下去。他见女人一直站着,就在床上移动了一下,示意女人坐下。女人坐在了床尾。
“是噩梦吧?”主妇问客人。
“也不算噩梦。”
“没事,听别人说梦都是反的。”主妇安慰客人,将那蜡烛头从反扣的茶杯上弄下来,从茶壶里倒一些水在茶碗里,晃了晃,将茶碗里的水泼在地上,然后倒满。
“还去看白塔吗?”
“去看,去看。”客人很急切。
“刚做了噩梦,你就不怕……”
“没事没事,我不说了嘛,我是捉鬼出身。”他想再摆出一副半嬉皮笑脸半一本正经的样子,脸皮却不够听话。笑的时候有些惨,不笑呢又过于严肃,倒显得紧张了几分。
“那走吧。”主妇从床尾站起来。“外边冷,多穿些衣服。”
“远吗?”客人问道。
主妇没有回答,和客人一起走到院子里。主妇让客人等一会儿,她走进自己的屋子。客人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感到一阵黑暗的冷气。他看见主妇的屋子里灯亮了,一个巨大的人影在窗子后面的窗帘上晃动。他一下子感到这一切都很陌生。他不愿意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移动了一下脚步,走到一棵椿树下面,用手去抚摩。椿树的树皮虽然有一些斑点,但算是比较滑的,唯一不好的地方在于有时会从树皮里面流出脓液一样的东西,发出一种酸气,而且很粘,像胶水。他的手上果真触碰到那种脓液,又凉又腻,他慌忙往自己的裤子上抹,觉得不妥,伸出手掌在树皮上蹭起来。他又走到鸡圈旁边,鸡都睡觉了;它们挤在一起,在鸡圈的一个角落里,不仔细看,什么也看不清。他用树枝穿过塑料网去抽打它们,它们也仅仅是咕咕叫两声,一动不动。他又走到猪圈旁边,跳到猪圈里,去踢那头老母猪,老母猪连哼哼都懒得哼哼,对他不屑一顾。他从猪圈里出来,发现主妇还没从屋里出来,窗子上的影子还在晃。他又走到压水井边,压了一下,压水井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这让他始料不及,吓了一大跳,可以说是一下子就蹦开了。他又走到大水缸旁边,揭开水缸的木盖,里面的水是满的。在夜光中,那一汪水异常清澈明亮,仿佛镜子一般,照出他黑乎乎的身影。他把刚才不小心弄脏的手伸进水缸,镜子立刻破碎了,一股钻心的冰凉从指尖直达心肺,他急忙将手抽了出来。水缸的旁边,正是主妇屋子的木门。他向木门靠近了一步。这时,里面的灯灭了。主妇打开木门,从里面走出来。主妇显得异常臃肿,好像穿上棉袄一般。“外面冷,所以多穿了些衣服。”主妇说着,带上门。走出院子,来到大街上的时候,客人才注意到主妇的手里正提着一根木棍。“擀面杖。”主妇说。
“远吗?”客人问。
“走走看吧。”
“这话有意思。”客人大声说,好像跟自己提气。
“小声点,有狗。”主妇的话刚说完,村里的狗果然都叫起来。刚走出胡同,突然有个东西窜将上来,迎面爬上客人的肩膀。主妇抡起擀面杖,打过去,那个黑东西呜一声跑了。“我说吧,有狗。”主妇说。客人小心翼翼走在主妇后面,警惕地看着四周。然而四周安静下来,再也没有狗叫了。
“就当是去河边挖野菜。我们隔着河看看就算了。”主妇小声说。
“深更半夜挖野菜,也很新鲜。”客人的调门很高,稍稍有些颤音。
“咋啦?”
“没事,绊了一交。”
“看路。”
“好。”
“又咋了?”
“脚脖子好像崴了。”
“快走吧。”主妇有些不耐烦。
“很疼。”
“棍子敲两下就不疼了吧。”主妇低头看蹲在地上的客人。客人也抬头,看见她居然真的举起那根擀面杖;而在她背后,突然闪出一轮明月。客人被这一幕惊呆了,不知道他是害怕主妇真的会给他一棍子,还是被那突然出现的月光迷住,他腾地站起来,和主妇继续前进。然而月光又突然消失了。
主妇和客人回来的时候,客人看上去累坏了,哈欠连连。主妇劝他早早休息。客人一边答应,一边往西厢房走,突然回头看看主妇。她站在院子里,并没有进正屋,似乎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客人有些担心。刚才走了那么多路,他确实累坏了,真想倒头就睡。但主妇好像又要出去,这不关他的事,他也实在不想在半夜里陪她瞎跑了。可现在都已经后半夜,主妇的样子还是隐隐让他感到不安。他倒不担心主妇怎样怎样,他开始担心自己。前所未有的恐惧感突然从心底跳出来。不过到底有什么恐惧的呢?他暂时弄不清楚。
半躺在床上,一时不敢关灯。看了看桌子上那半截烧剩下的蜡烛头,不禁又想起刚才做的梦来。他以为是旅途劳累,才会做这种艳梦。但是那个女孩的面容却清晰地在脑海里晃,下面又悄悄直立起来。没想到意淫这么可怕,他摸了下面一把,很有些感觉,于是连续摸了一阵,终于泄出火来,然后就开始迷糊了。
门又开了。客人很警觉,但只是眯着眼,佯装睡着,看见主妇进来。她和刚才出去时一样装束,穿得厚厚的,手里还是提着那根擀面杖。客人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但不敢稍动。主妇并没有走到床前,只是在门后将屋子的灯拉灭,重新将门带好。客人听见院门开启和关闭的声音。
客人立刻起来,没有开灯,黑暗中穿好衣服,走出院门。黑漆漆的大街上什么都没有,主妇的身影早已不知道消失在哪里。客人疑惑着,不敢返回自己的房间。他凭着直觉,朝公路的方向走。估计很快就天亮了,即使天气很冷,随便找个背风的地方躲一躲,估计也冻不死人。他这样想定,就不顾一切地朝公路的方向奔来。虽然摔了几个跟头,好在方向不错,公路找到了。他正要在墙角里找个背风的地方,却愕然发现烧饼铺子里的灯还亮着。
好奇心鼓励他去看个究竟。铝合金的卷帘门拉到一半,昏黄的电灯光从那一小块敞开的地方泄露出来。不过因为店门有着高高的台阶,所以通过那一块敞开的空间还是能看到里面。客人快要走近时,哐当一声,卷帘门突然从里面拉死了。客人靠近卷帘门,不用刻意趴在上面听,里面就已经传出来很大的动静。男人鬼哭狼嚎似的叫声。棍子抽打在骨头上的声音。还有女人的哭叫。女人一边奋力打,一边哭,嘴里发出不清晰的几个词:“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叫你……死去……算了……”这种混杂的声音持续很久。客人听得肝胆欲裂,不敢停留,跑到马路对面一个背风的墙角蹲下了。又过一会儿,卷帘门打开,一个人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提着一根长长的东西,大踏步往村子里跑去。
客人不敢再尾随那个人,他缩在背风的屋角,感觉骨头都快要冻裂。他想无论如何不能睡着,一定要睁眼等到天亮。天也许很快就亮了,汽车站会派一辆最早发的车来接他。他不过是个旅行者,应该没有人会无故阻止他的旅行;而已经发生的所有事情,也都和他无关。他舔舔嘴唇,嘴唇像抹了一层冰淇淋,有点甜,但更冰冷一些。
那些和他一块等车的人都去哪里了呢?他现在感到脱离集体的孤单和无助。不过,等到太阳再次升起时,在这条明晃晃的大马路上,他们一定还会出现的。他们不也都买了车票吗?他们决不会因为隔一天就不再等。可是现在,他们都在哪里呢?
公路上突然有车灯闪烁,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汽车的动静在后半夜竟是这么巨大吗?他从背风的屋角冲向公路,还没来得及摆手,那辆汽车在他身边戛然而止。
“请问你是汽车站派来的吗?”他大声问司机,声音颤抖得几乎说不成话。
“你他娘的说什么?”
“我说你是来接我的吗?”
“老子正是来接你的。”
“太棒了。怎么才来,我都要冻死了。”
“在路边店被他娘的小娘们缠住了,好歹住他娘的一夜,起个大早往这里赶。听说这里昨天发生一场他娘的车祸?”
“是啊。”
“听说车子翻了个底朝天?”
“没有的事。我们都在等救援呢。”
“你是那车上的?”
“是啊。”
那个司机在车里盯着他,龇着牙,摸了一会儿下巴。
旅行者站在车门口,不住地往双手上哈气,然后搓脸。
“还不赶紧上来。”司机说。
“怎么,你他娘的在路边站了一夜?”司机又说。
“他娘的,什么破地方?”司机见他不回答,狠捶着方向盘,自言自语。
“白塔。”他说。
“什么?”
“白塔,老兄。”
“再说一遍。”
“白塔。”
“娘的,什么破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