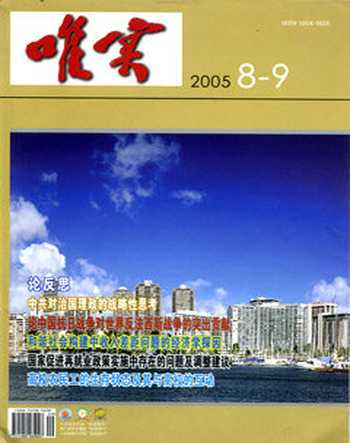发现费穆
张永祎
有一位导演在他所处的时代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反而在沉寂了若干年之后,适逢新世纪春风初拂之时,却愈益“放射出让人目眩心惊的光芒”。他儒雅清秀、风范大气,他用笔淡雅,如诗如画,时过境迁没有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任何尘封的痕迹,在恍若隔世之中他给我们创造了一段美丽而忧伤的爱情故事。他就是活跃于我国三四十年代的早期著名导演——费穆。
费穆,1906年生于上海,1924年后利用在天津华北影片公司干杂活的机会刻苦钻研电影艺术。1932年到上海加入联华公司,导演了《城市之夜》、《狼山喋血记》等影片。上海沦陷时期,编导演了《孔夫子》、《四季儿女》,后拒绝与敌伪合作,愤然退出了电影界,战后拍摄了故事片《锦绣河山》、《小城之春》和我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生死恨》。1948年赴香港参加龙系影片公司,导演了《江湖女儿》,影片尚未拍完于1951年病逝。
他对江南文化非常熟悉,特别是对苏南文化更是情有独钟,他的创作时时受到苏南文化的激发,也常常成为苏南文化的载体,许多影片都取材于苏南的水乡小镇。他对苏南文化的由衷热爱,使他在创作的过程中时常会出现一种不由自主的驾轻就熟,那就是深入骨髓的江南情结在为其自觉地引领航向啊!是的,当一位导演生于斯长于斯,在耳濡目染中形成了某种深厚的人格积淀以后,那么他所孕育而生的作品也就无法跃出这种心灵的半径。滋生于苏南风光之上的爱情绝唱就很可能变成他透视社会的艺术之旅,这种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固然不会受地域所限,但插入其中背景的不同给人们带来的感觉也会产生变化。荒漠大滩上,边塞戈壁里,固然会有铁骨铮铮的侠客柔情,但那毕竟是代表着一种旷达悠远的情调,而苏南的那种细雨霏霏、烟岚朦朦、流水潺潺、黛山隐隐,可能更符合费穆的审美心境,更能代表他对人生的一种温情脉脉的注视。于是,在这种和风细雨的情调中催生了许多作品,脱颖而出的当首推《小城之春》。
影片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战后,南方,那一座僻静的小城里。礼言、玉纹夫妇过着相敬如宾的平淡生活,不料随着医生志忱的到来,却突然打破了他们生活的平静。他不仅是礼言老同学,还是玉纹的旧相识,偏偏礼言还不知道志忱和玉纹已有前缘。断情再续有着天性的青春冲动,又有着不敢越雷池半步的胆战心惊。“一种相思两样愁”的小城故事在费穆有声有色的叙述中便娓娓道来了……
从一般意义讲,故事片的美学是以情节为中心的,如何在情节之中注入情绪,或者说在客观的叙述中平添几分主观的感觉,这种艺术的叠加是许多导演孜孜以求的,也是容易取得成功的。问题是费穆竟能够将情节和情绪颠倒过来,即把情节奠基于人物情绪的基调之上,让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变成了心理聚焦的情绪特写。志忱和玉纹的相遇、相爱、相难、相分过程,几乎共冶人物情绪于一炉,玉纹的心理变化成了这些情节的发射点,许多情绪的抛物线都是从这出来的。为了进一步强调影片的这种主观色彩,他还别具匠心地在第一人称上下起了功夫,用玉纹的旁白来结构全篇,使一气贯注的情绪流淌在人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上,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跟着她的感觉走,有了一种近似回忆般的朦朦胧胧的主观感受。
影片反映的背景正是国共战争如火如荼的年代,《小城之春》居然能够置战火纷飞、风雨飘摇的局势于不顾,甚至对巨变前夕的若干中国人的现实状况充耳不闻,反而能够静下心来聚焦于小城一隅,尽情地饱餐着桃源仙境里的道道美景,专心致志地对几个心绪不宁的人物进行实验室里的洞幽烛微和手术台上的条剖缕析,给人以一种浮游于世、超然物外的感觉。就连在小城里生活的人们都被他给虚化掉了,我们看到的只有他们几个人,除此之外仿佛都不见了踪影。这真实吗?肯定不真实。但费穆这样处理自有道理,似乎是在有意鼓励人们与现实拉开距离,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他所创造的审美境界之中。
于是,《小城之春》在诞生之后便屡遭厄运。人们群起而攻之,矛头直指影片弥漫着那种小资情调,还有人愤怒地控诉费穆脱离政治、忘却时代,严重缺乏现实意义。其实恰恰相反,影片并没有超越那个特定的时代,只是没有像其他影片那样直白地将镜头对准现实的人生,而是在深层次上与时代进行联通,极其巧妙地以一种封闭空间中的人性化故事来展示中国旧道德伦理对人性的束缚和爱欲的挣扎,而这种欲说还休、发乎情止乎礼仪的情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跨越时空的自我感觉和情绪认同,以至今天看来这种情感的揭示,仍具有一针见血的穿透力和未见褪尽的深刻性。
对于《小城之春》中表现的这种想爱不能爱、想走走不了的人生困境,并不是费穆的异想天开而是他的别有所求。据说他曾让编导李天济按照苏轼《蝶恋花》“笑声不闻声见悄,多情却被无情扰”的意境来构思影片,从《小城故事》看基本已实现了这样的思路,为了弥漫这种唯美情调,他很善于吸收中国古典诗词的传统,注意借物喻人、以景抒情,烂熟于中的诗情画意很容易化景入境。这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地就是《小城之春》颇具经典的开头。影片通过玉纹的独自配合一组平行蒙太奇,只用简约的几笔就勾勒出了小城的概貌:一道城墙隔绝了城外模糊的春意,只见城内疏桃浅巷,残垣断壁,老仆,药渣,病人等艺术符号的出现,让人们一下子就扑入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的境界,这种疮痍满目的轻描重写也为“春风吹又生”的生命活力预留了伏笔。这种情绪不可阻挡地向影片的纵深溢漫,直到志忱的到来才出现了些许亮色,特别是在他们同游踏青的时候,许多美丽的画面才渐次映入了他们眼帘。他们的小船摇曳在山水之间,徜徉于风光之中,就像一幅简约的中国水墨画舒卷开来,充满着纯美的散文或电影的一种浓重的诗意,这种随意点染之笔恰是志忱与玉纹旧情重燃时那种载欣载悦的真实写照,荡漾在心中的一抹恋情被飞扬于盎然的春意之中。按照这种情绪发展下去,如此美丽动人的故事最终应该是花好月圆的,但却被链接上镜花水月一般的悲剧结尾,看似恢复了往日的生活,却完成编导在美学上崇静尚宁的编码过程。
看来费穆是在苦苦追求那种“不是风动而是心在动”的宁静氛围,黑白片恰恰能够以色调的凝重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费穆说:“我为了传达古老中国的灰色情绪,用‘长镜头和‘慢动作构造我的戏。”也就是说借助于黑白片天然形成的灰色基调来表情达意,而且他还善于运用“长镜头”和“慢动作”,许多镜头美仑美奂、不即不离,如旁观者一般的冷漠淡定,散发着一种超然物外的平和安详,游刃有余中显示出一种大师的风范,让人不由心生敬意并叹为观止。戴秀用唱歌向志忱表达爱慕之意的那一场戏,费穆用了长达1分40秒的长镜头,小心谨慎地将玉纹、礼言、志忱的微妙关系溢于言表,在这个长镜头中,他们三人几乎都没有在一个画面中同时出现,编导用镜头语言向人们交代了应该交代的内容,也向人们述说了他想向人们叙述的事情。费穆娴熟的电影语言表达方式还表现在对于自然光影的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玉纹多次去志忱的房间,这是反复出现的核心情节,在光影的处理上却每次都有所不同,或明或暗,或隐或现,或利用月光的婆娑树影,或表现为烛光摇曳,丝丝入扣,一气呵成,都能够恰到好处地与当时人物的心理状态形成一种对应关系。可以说,影片的叙述是在不露声色中体现出一种宁静致远的风格,情节的发展全凭本:身的内在张力,费穆并没有刻意去在放大这种张力,甚至还被他内敛了许多,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镜头语言的思维上,通过镜头语言的运动和变化来反衬人物关系的冷冷清清,通过这种相反相成地组接传达出了“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境界。
岁月流转,经典永恒;人去楼空,小城依旧。50多年前缔造的《小城之春》在电影史上竖起了丰碑,那无与伦比的魅力甚至淹没了50多年后跃跃欲试的创作热情,尽管有人试图铤而走险,其同名影片尚未充分绽放,就已成了明日黄花。应该说,翻拍可以为经典提供一种新的版本,也可以提供一种新的选择,更可以带来一种新的阐述,但对于像《小城之春》这样历久弥新的极品之作,任何细微的改变都会让人觉得不可容忍,事实也证明它是无法超越的。世界电影100年10部经典作品中有它,中国电影90年10部经典作品中也有它。它被誉为“中国电影一致公认的经典作品”。香港电影界认为它是当之无愧的“有史以来中国最佳电影”,著名导演张艺谋称自己最喜欢的电影就是《小城之春》。
《小城之春》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出现在21世纪观众的眼前,从它“大器晚成”的爆发中人们终于发现了费穆天才的导演艺术。他在黑白世界里给我们酿造了一缕缕淡淡的哀愁,一片片相见恨晚的情思,尽管岁月冲刷画面已日渐褪色,斯人作古故事已愈益遥远,但《小城之春》依然能够让人屏息凝神,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是因为费穆于历史的缺憾中生发出爱的永恒和江南的美丽,使人心驰神往,弥久恒馨。
(作者单位:江苏省人事厅政策法规处)
责任编辑:张功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