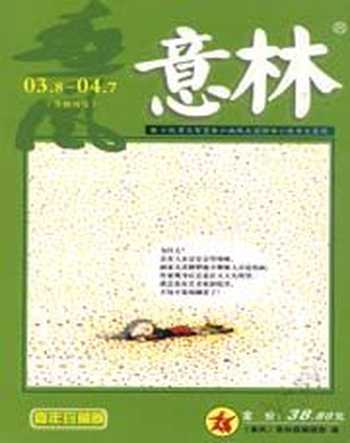山 民
佚 名
做生意的二哥从陇上归来,我去看他,见他郁郁寡欢,便提出请他吃一顿。我们在一家中档餐馆落座后,服务员小姐将菜单递到我手中,却听见二哥冷冷地说:“点两个素菜,够吃就行。”我笑着对二哥说:“兄弟没你钱多,一顿饭还是请得起的。”二哥瞪我一眼,“有钱也不能糟践。”语气中带着一点愠怒之色。
我大惑不解,却只好由他。
“老三,我给你讲个真事,你看你能不能写个啥,在报上发发,也算了却我一桩心事。”二哥说。
我点头说,没问题。
二哥长长嘘了口气,缓慢讲了起来———这次到兰州讨债,事情还算顺利。当我准备返回时,忽然想起你嫂子的那个弟弟了。他叫毛三,你该知道吧?三十年前,从老家逃出来,流落到甘肃西南的一个穷山沟里,被当地人收留,成了倒插门的女婿。我想去看看他,接济接济他,那里还是贫困区嘛。主意定了,我就到汽车站买了票,走了。汽车在山路上颠颠晃晃走了七八个钟头,下午四点左右,到了终点站。到这儿,公路就断了,四面全是山。和我一块下车的也只有五六个人,等到大伙一散,就剩下我一个人在那里发怔了。
我真有点发毛,在这穷山旮旯里,我该怎么走?
忽然,我看见一个山里人正朝山上走,便急忙喊了一声“老乡……”那人扭过身来,我忙问,“到刺儿沟咋走?”
那山民四十来岁,身体也还算结实,只是穿得太破太脏。
“刺儿沟远着哩,二十来里,路不熟,到天黑你也赶不到。天一黑山里就让人怕哩,狼、熊直吼叫哩!”山民的话让我更怕了。真后悔怎么想起到这鬼地方来。
那山民却咧着大嘴一笑:“莫怕,我给你带路,天黑前准到。”
我看那山民也不像歹人,便说:“那就谢谢了。我会给你付劳务费的!”
山民肯定搞不懂啥叫劳务费,眯着眼望着。我忙说:“噢,就是钱,我给你钱!”
一听说钱,山民那浑浊的目光中闪出一丝光来。
就这样,那山民在前面带路,我在后面跟着,遇到沟沟坎坎,山民便先上去,然后伸手拉我,遇到有刺的草丛,山民便先用脚将草踏平,再让我过。途中有两条小河,山民不由分说,便将我背起来,踩着水里的乱石,小心翼翼地过去。兄弟啊,那情形简直比对他亲爹还尽心!
果然,天刚黄昏,我们就到了刺儿沟。那山民说:“到了,我回去了。”
我一面连声称谢,一面问:“老弟,我给多少钱合适呢?”我原想掏个三四十块钱给他,又怕人家嫌少不高兴。我看见那山民脚上都渗出血来了,要是城里人,给一百元都没人干。
那山民又用怯生生的目光望着我:“真给钱?”
“当然,咋能让你白辛苦呢,这一路也够难为你了。”
那山民,双手在裤子上搓了半天,喃喃地说:“那……你就……给我……五……”
噢,他准是想要50元,行,不多。我正准备打开提包取钱,却听见一个胆怯的声音:“给五毛钱,行不?”我怀疑自己的耳朵有毛病,瞪眼问了一句:“什么,多少?”那山民一惊,后退一步,结结巴巴地说:“五毛不行……三毛……三……毛……”
我听懂了,可就这一串结结巴巴的话,却如一声炸雷,我的心猛地震惊了,发颤了!天啊,咱在大城市,一块钱掉在地上都懒得弯腰去拾,麻将桌上一扔就是三千五千,一顿饭就是千把块,山里人拉你,背你,扶你走二十多里路,想挣你五毛钱,还如此战战兢兢。
兄弟,那一刻,我真的落下泪来了。你知道,哥哥再难的事也不会落泪的,可为这山民讨要的五毛钱,哥落下泪来了。我掏出张五十元的大票子,塞到那山民手里,转身就朝村里走去。
转身的那一刻,我听见身后有响声,“嗵”,像什么重物落地。可我心里乱,没顾上回头看。等到了村口,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你猜我看到了什么?“大山?”“不,兄弟,我看到的是,那山民跪在山路上,正朝刺儿沟方向磕头啊,兄弟!”
二哥的故事讲完了。
二哥问我:“你信吗?”
心里很闷,我长长地,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说:“我信……”
文/彭结梅摘自《散文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