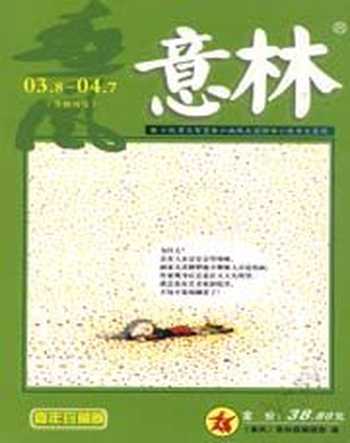孤 雁
草 籽
二十年前的一个十月底,正是秋风萧瑟,玉米金黄的季节。我所住的知青宿舍外面是个宽阔的大苇塘。不知什么时候,一群南迁的大雁落在大苇塘里歇脚。它们白天飞出苇塘觅食、嬉戏,晚上回到苇塘里过夜。
一天中午,知青们正在午睡,忽然被一阵叫嚷声吵醒。只见知青“麻秆儿”左手握着他那个从不离身的弹弓,右手拎着一只滴着血,还在扑腾的大雁闯进屋里来。
“嘿嘿!哥儿几个醒醒,都开开眼吧!”
“哎哟!这么大的家伙!怎么逮着的?”
“一个大滚珠儿正打在它脖子上。”
“给‘麻秆儿记一大功!”
“好!今晚上开斋!拔毛炖肉买酒去!”
身材瘦高,平素寡言少语的“麻秆儿”一个中午竟成了知青们公认的英雄。晚上,四瓶白酒加上一锅香喷喷的炖雁肉,让这伙一个月没见着荤腥的知青高兴得发了狂。三天后还在咂摸那大雁肉的香味儿!
然而,自从“麻秆儿”打死那只大雁后,苇塘里的雁群就不见踪影。据车把式们说,雁群挪到村外北头的河套里去了。可奇怪的是,从吃完雁肉的第三夜里,就隐约听到苇塘里有雁叫的声音。开始知青们没在意,后来,所有的知青都清楚了,那是一种凄厉、悲痛欲绝的雁叫声,吵得知青们几乎无法入睡。连着好几个晚上,知青们一齐往苇塘里扔石头,却发现只有一只大雁哀叫着腾空飞走。白天看不见它的踪影,一到晚上,它又幽灵似的在苇塘里哀叫。有时竟飞落在我们宿舍外的窗台上。打开灯,我们甚至能看清它的模样:灰褐色的身躯,脖子上有黑色的斑点……这是一只被我们夺去配偶的孤雁。
“麻秆儿”的脸色挺难看,老是坐立不安,蔫头耷脑的。知青们无奈之余也就渐渐适应了那只孤雁的哀鸣,照睡不误了。
十一月初,就在降了第一场小雪后,住在村北头河套里的雁群终于浩浩荡荡排着整齐的队形启程南飞了。老乡们望着远去的雁阵纳闷:“哎?真怪呀,今年的大雁比往年晚走了半个月……”知青们心里明白,可谁也没吭声。只有默默祈求大雁家族能保护那只孤雁了。一转眼,随着北风呼号,天寒地冻,就要到年底了。知青们兴致勃勃地采购年货,准备回京城过元旦了。只有“麻秆儿”似乎郁郁寡欢,有时站在宿舍院外的栅栏边,望着已经结冰的苇塘发愣,他手里的弹弓早已不见了踪影。
回京城的头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早晨,阳光灿烂,四野白雪皑皑。知青们吃过早饭提着大包小包走出宿舍,准备搭进城的拖拉机回家。就在等拖拉机的空儿,眼尖的“黑子”突然像发现什么似的往苇塘里跑去。大伙瞧着他撩开稀疏的枯苇秆儿跑到苇塘深处的一个地方,弯腰拾起了什么东西。知青们放下提包,跑进苇塘,只见“黑子”手里拎着的竟是一只冻僵的大雁!“麻秆儿,你快看!这……是那只孤雁!”
知青们围拢上前,看清楚了,正是那只被我们夺去配偶的孤雁。它的身体枯瘦,羽毛还较鲜艳,眼睛亮闪闪的,可见冻死的时间并不太长。
“麻秆儿,真有这么痴情的活物……拎回北京吃肉吧!”“黑子”见大伙都阴沉着脸没吭声,终于忍不住了。“放屁!我掐死你!”“麻秆儿”突然暴跳起来,一把掐住“黑子”的脖子,就势将死雁夺过来搂在怀里……大伙儿这才发现“麻秆儿”的眼睛已变得血红,大滴大滴的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涌出。
文/刘震声摘
——崔涂《孤雁二首·其二》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