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
杨全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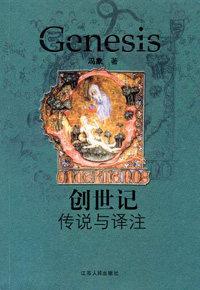
美国著名作家赫伯特·芬格莱特是中国哲人孔子的思想所深深吸引并加以研究的西方人,他说研究孔子的“主要目标就是去发现孔子思想的卓异之处,学习并体会他所能够给予我的教诲与启迪,而不是为了寻求那种有点学究式的快乐,也就是说,不是为了在一个古代的异域思想者身上,期待某些已经为我们所十分熟悉的看法”。
这是一个西方人对待中国经典的态度。其实对待所有的人类经典,真正的思想家或者学问家所采取的态度都是一样的。政治哲学大师施特劳斯的弟子和另一个大师阿兰·布鲁姆对待经典也是如此,他的为学基本上就是对经典的现代阐释。在这些真正的学问家、真正的思想大师眼中,经典并不是像对一般人而言的一种家庭装饰,一种社交用的闲资,而是真正的对现代的个人生活或社会生活有教益、有启迪的原料。
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圣经》同样需要被这样对待,不仅是西方人,东方人也一样。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圣经》可能只是一只提供了若干著名故事的篮子,它的功能跟挂在好多中国家庭里的西方油画名作复制品一样;赴宝山探险的人少之又少。冯象却绝对算得上一个。
《圣经》汉语通行译本为合和本,文字为白话文学运动兴起之后带点古拙味道的笔法,读来虽不琅琅上口,倒也跟经文的内容相得益彰,在阅读时自然地生出一种敬畏感来。冯象的译文用的是当代的规范中文文体,明白如话,只要识字的人都看得懂。从这个角度说,冯象的译文是给众人把《圣经》当成一种文学、历史文本所看的,译经的出发点当在于作者的学术兴趣。这是冯象的译文跟合和本译文的第一大区别。也是冯象译文的第一大特点。
冯象译文的第二个特点大家都看得出来,那就是译名的不同。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人物神祇山川城镇等的译名,是汉译《圣经》诸多问题中较为彰显的一个。原因很有趣,如传教士的口音、方言‘官话和宗派教义的影响……我的原则,一是约定俗成,尽量保留众所周知的名号,例如亚伯拉罕;二是名从主人,依照原文的发音含义和文体风格,以及解放后建立的现代汉语译名用字习惯,适当再现《圣经》里常见的词根谐音互明反讽等修辞效果。”《圣经》的翻译,大都会对某一语言的发展产生一种革命性的影响,英文如此,德文如此,汉语也是如此,合和本的译文是在中国白话运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译本,至少也是对白话运动的一种推进。冯象的译文因为用的就是当今比较成熟的现代汉语,所以对于汉语发展的促进作用能有多少,我无法评价;但是对于中国当代翻译外国的人名、地名、城镇名等,我以为,还是很有启发的。其实他的原则也并非什么传世之秘,在白话运动中涌现的那一批知识分子手中,这种译法是被普遍采用的,只是到了后来,被一部对中国影响深巨的著作的翻译所打断并误导,才显得“失传”了。
再说《创世记》一书的上编,即二十则《圣经》故事。在作者看来,“写故事,也是治西洋文学的一法。很多西洋古典作品从原文阅读,在原文的学术传统里辨析讨论,并不感觉深奥曲折。可是译成中文,就常常变得艰涩难解,让读者兴味索然。”这是因为中国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母语的思维习惯不同,而原著的某些思想和表达是没法准确简明地移译的。要解决这个难题,“除了注释评介,还可以‘故事新编;即把原著拆了重新敷演,融入中文的语境与文学传统”。这一点,我们在读“尘土亚当”的故事的时候,分明能感到作为文学与历史文本的《圣经》对作者的生活是有影响的,并不是挂在墙上的一些油画复制品,而是进入了作者厨房的菜肴。
经典,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
难怪作者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我希望每三年,将《神曲》重读一遍。”
《圣经》冯象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10定价:2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