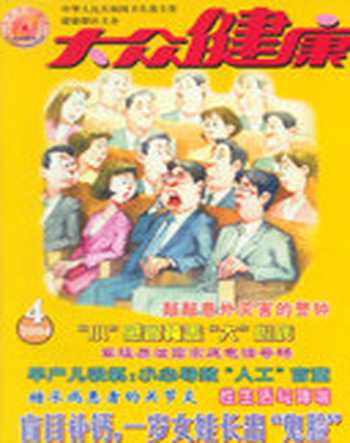男儿当自强
袁 苑
1981年10月……
王明晓正式行医于1981年秋季。他是中国恢复高考后毕业的第二批医学生。他的第一个职业驿站是郑州矿务局总医院。
王明晓最初给人的印象大概有二:一是消瘦,1米72的个头,不过90来斤的体重;一是热情、精力过旺。身在内科,却也关心其他科室危重病人,哪怕半夜,也要起身去看个究竟。
大约1年的光景,一种莫明的疾病像一团暗火在当地矿区隐隐地蔓延。求医者接二连三。从临床表现看,既似伤寒,又不似伤寒。尤其是临床上并不见持续高烧、玫瑰疹、肝脾肿大等典型病征。更何况此类传染病在国内的暴发流行已基本根绝。难怪大夫们没往伤寒上想。起初时,多以感冒、肠炎对症下药。然而,病势疯长,患者剧增。
“明晓”,不知是巧合,还是爹妈当初起名字的时候,有某种暗示或授意,反正,关键时刻他似乎格外聪明晓理。一个尚未摆脱“乳臭”的孩子,居然在“大兵压境“之时,悄悄地否决了众人的治疗思路,考虑会不会是病菌的变异反应?他知道,坚持新观点,必须有病理和机理的支撑,必须对临床反常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他需要从大量的中外资料中找到明确的说法,而时间又不允许拖延和迟缓。很快,他的预感和判断得到了证实——肠伤寒。随着疾病的确诊,一整套针对性很强的治疗方案确立。终于,结论折服了所有的人。于是,一场患病人数很多的烈性传染病得到遏制,而且因为神速,竟没有一例不幸者。
事后,王明晓撰写论文《肠伤寒临床变异情况的初步分析》。此文发表在《煤矿医学》杂志,当年获得郑州市优秀论文奖、郑州矿务局科技成果一等奖。
不久,一位骨折病人因为心律失常请内科会诊。经王明晓诊断,典型的房性早搏,随即进行了对症处理。奇怪的是,药物下去,早搏现象丝毫不见收敛。再行其他药物,病症依然是无动于衷。相持之下,更奇怪的事发生了。随着病人骨折的好转,心律失常竟也悄然不见了踪影。这种闻所未闻的怪现象让王明晓碰上,自然是不会轻易放过的。苦于一时找不到现成的资料来说服自己,于是居然跟随病人,甚至跟到病人家里,坚持观察记录病情,时间长达半年之久,直到接下来陆续出现了几例类似情况。王明晓终于找到结论:骨折与心律失常有关。于是,又一篇论文出世。《创伤导致心律失常的临床分析》发表在《煤矿医学》和《临床心血管》杂志。此时,王明晓在郑州,在河南,在煤矿系统,初露锋芒。
论文,在80年代初是稀罕之物,更何况在基层的企业医院里。因为持续十几年,学术领域几经颠倒、几番折腾,猛然拨乱反正后,人们普遍还没回过味来。专业理论、临床技术是否需要表达?用什么方式表达?大家还隔膜得很。却不料,这等惊天动地之事竟让一个刚出校门、几乎没有太多临床经历的大学生一次次地抓住。瞩目之中,长者们对于“初生牛犊”不免倍加赞赏。
其实,王明晓自幼喜欢写。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就曾给《解放日报》投稿。“要让别人知道你”,这是他最早的不甘被人忽略的童心反应。因为他的家乡确实没有引起别人注意的理由,离洛阳城很远,在一个山坳里,七沟八梁,十年九旱,漫山遍野散落的都是羊粪,而羊粪就是钱。只要手脚勤快,一会儿就能拾一筐。按照大人们的折算,一斤羊粪合一个工分,一个工分就是2分钱。然后这样一分一厘地攒起来,开学了,就是一笔学费。他觉得这是一个有能力的孩子最大的乐趣。于是,他把这种值得骄傲的经厉仔细地纪录下来,命题《秋假》。
相比之下,把临床上的独到体会表述出来,这是王明晓做了医生之后,在患者面前做的第一件“有能力的事”。同样是自信和成就感,却与童稚的生存能力味道截然不同了———“通过自己的努力,解除了那么多矿工的痛苦”。那种感觉是强大的,具有冲击力的。这时,王明晓觉得自己好像一粒已经快发芽的种子,他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回报大地的强烈愿望。
1986年3月……
1986年3月,29岁的王明晓被任命为医院医务部主任。那时,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才刚刚拉开。大锅饭喂得人人懒洋洋的,几乎没有人去理会生存问题、竞争问题。自然也就没有人去刻意追求质量理念、服务理念。
从专业转向管理,王明晓必须另起炉灶。而他的“炉灶”要“炮炼”的是苦口良药,是人们一时不情愿接纳的“管理”、“标准”之类的东西。改革者无论大小,注定是与风险伴行。他们要触犯的往往是人们头脑中最顽固的习惯势力。
王明晓首先从基础业务入手,规范处方和病历的书写标准。在他看来,如果连走都走不好,还谈什么跑?更何来腾飞?
那时国有企业正在探索分配制度的改革,什么奖勤罚懒,多劳多得,拉开档次等等。这些时髦的字眼原本对医院可以网开一面。而王明晓却是与众不同的“明晓”。他山之石,又为何不能为我所用?他不甘落于人后,于是,在医护人员中拨弄起奖惩的杠杆。
自然,他首先瞄准的是处方和病历。一张不合格处方扣罚0.1元,一张不合格病历扣罚0.5元。那时职工工资不过四五十元。几张“不合格”就很可以“伤筋动骨”。
人没有先知先觉,王明晓同样不谙管理学的技巧。那时他未必懂得“游戏规则”的不可松动性。但是,从人们崇尚权利的心理,他清楚,如果医院领导不做特殊公民,那就是按规则办事。
事出不巧,“游戏”刚刚开始,亲手栽培、提拔他的老院长,竟有几张处方写得不合要求。是要人情还是要规则?王明晓傻乎乎地找到老院长。“我看您这5张处方不规范”。因为心存“不仁不义”之嫌,他说话的语调有些战战兢兢。老院长看着年轻人这般敦厚,差点没笑出声来。当即表示,“该扣”,并提议,把被扣罚的名单当众公布,老人自愿放在第一个。王明晓感动:原来,只要你做的事情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你的背后就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在支持着你。
这一来,医院的处方、病历,开天辟地地出色起来。处方的合格率达到99%,甲级病历竟达到100%。第二年,郑州市上百家医院进行质量评比,自然是郑州矿务局总医院名列第一。
王明晓出师顺利。
1988年2月……
王明晓自称“出道早”。这一年,31岁的他出任郑州矿务局总医院副院长。职位的快速转换在外人看来是春风得意,而在他则要马不停蹄,甚至没有喘息的工夫。
好在他善于在万变之中找出头绪。这种功夫推想是得益于“苦”。在他童年的记忆中,地里的收成总是填不饱肚子。其中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过错,他决不怨天尤人。大千世界原本苦乐无常,他认准,改变命运惟一的途径———读书。而且这种决心让他在羊粪堆,在麦地里,在火车站搬运石头的跳板上,日复一日,百炼成钢。可以想见,羸弱的身子,扛起百斤重的石头,一步一颤。因为支撑骨骼和神志的是丝毫不能产生能量的空腹饥肠。那是人能承受的灵与肉双重磨难的最低底线。但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继续坐在高中的课堂里。于是,他挺过来了。孩提应该是懵懂的,所以一旦在孩子的目光中有了神往,那是外力难以摧折的。
当有这等吃苦经历的人要制定一个发展目标的时候,他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作为煤炭职工医院,自然最忌讳的是“伤残”、“死亡”这样的字眼。于是,“提高救治水平,降低伤残率”,被王明晓称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煤炭系统的急救建设不是孤立的。从井口到矿区,再从矿区到总医院,应该是一个健全的网络体系。其中各自为政或是某一个环节的薄弱坍塌,都会累及到生命。王明晓亲历过这样的惨状:矿井发生意外,伤员被不分轻重地送到矿区医院。结果一例极普通的气胸病人,因为受限于矿医院的技术水平和设备条件,居然眼睁睁地失去抢救的机会。如果当时直接送到总医院呢?这是绝对不该发生的悲剧。
于是,王明晓把急救单位划分成三个级别,然后,把伤情按照轻重缓急制定出三个标准。“三三”对应:轻者送井口卫生所;中者送矿区医院;重者直接送总医院。这样一来,一旦发生意外,整个网络牵制互动,分级疏导,一路畅通无阻。
这无形中给自己增加了压力。危重的病人,繁重的抢救任务势必集中到他这里。随即,总医院打出了毫无退路的标语———“把好最后一关”。好在“不怕吃苦”已在王明晓的生命里生根,再难的事他也挺得住。每一次的抢救现场,可以没有别人,却从来不能没有他。协调,组织;会诊,手术;血源,药品……情况紧急的时候,他可以一连几天没白没黑的守在病房里。
这是很难说清的一种情愫。
一天晚上,正赶上他值班,接诊了一位腹泻相当严重的病人,抗生素上去,症状暂时减轻了些。第二天,待王明晓查房时,却发现平展的床上已经不见了人影。病床上留着字条:“大夫,我先回去了,矿上有很多工作等着我呢。手续后面另办。”他的眼睛不由地落到病历页面患者名字一栏———燕青平。这个名字他恐怕一生也不会忘记,尽管几十年了,他过目的病人当以万计。在情绪冲撞的瞬间,他想起燕青平残疾的左手。那一定是在哪一次的事故中被活活地吞噬了指头,之后,留下的是一块残缺的手掌……后来,他得知,那是一位省劳模。
“这就是我们的矿工!”那时,正是4月的天气,春风吹开了满院的槐花。他想到了小时候,槐花放进嘴里,那种暖乎乎、甜滋滋的味道。这花朴实得几乎让人漠视。王明晓由此想到了那些默默无闻的矿工兄弟,他按捺不住涌动的心绪,提笔写下《槐花赋》。之后,郑州的一家报纸发表了这篇散文。燕青平呀,不知您是否看到了这篇文章?但是,有一点是一定要提及的———就在王明晓主管急救业务的那段时间里,整个总医院最响亮的口号是:工人兄弟用血汗养活我们;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
从1988年到1991年,王明晓他们接诊的危重病人,每年当以百计,然而竟没发生一例死亡。
1991年1月……
就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34岁的王明晓被任命为郑州矿务局总医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截至1995年初,他在位4年之后,有人为他拿出了一组数据:医院床位从200张增加到550张;日门诊量从百人增加到700多人次;医院的业务收入增长了3.7倍;职工的个人收入翻了一番;科技人员的学术论文每年在百篇以上……其间的1993年,郑州矿务局总医院在河南省煤炭系统第一家通过了医院等级审评,为此他当年荣获卫生部“全国优秀院长”称号。
孔圣人有劝学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后学者们竭尽追求“学与思”的融会贯通。无独有偶,王明晓回首往事,千言万语浓缩出6个字———多读书,多思考。
曾经的一场文化灾难,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成了毒草。于是,这个买不起书的孩子,在家门口的废品站垃圾堆里,有幸翻阅到各种各样的经典著作。这是天意。尽管很多书是残破的,甚至缺章断码,但这并不影响他饥饿的“胃口”。或许是命中注定,在那么多倒背如流的漂亮词句里,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儿子,居然彻头彻尾地被一首民歌降伏了———“朝为读书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主,男儿当自强。”不怕笑话,“将相本无主,男儿当自强”,就像过年时才能吃到的大白馒头,搅扰得他日思夜想。
不可否认,日后王明晓的敢想敢为,超前创新,很大程度正是取决于绝少门阀等级的心理。
他做院长恰是授命于动荡之年。首先是医院的名分起了变化。说是国有的,是福利性的,却断了财政的供给。院长不仅要是“巧妇”,而且还要自己找米下锅。好在他的市场嗅觉相当灵敏。早在3年前,他已经“蓄意”导演了一部“股份制”的喜剧。
那时“CT”在郑州的医疗区域内,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大家对它的价格望而生畏。但是,在王明晓的眼睛里,这台可以给患者提供可靠诊断资料的庞然大物,因为它不可估量的市场潜能,极有可能演化成一架钞票印刷机。这让他先人一步发现了“金矿”。接下来,挖掘“金矿”的巨额资金便成了他必须面对的难题。
王明晓搬出了《资本论》。他要向马克思要答案。于是,终于在字里行间,让他找到了大约是这样的话———当你决定修一条铁路的时候,如果要等到资金足够的那一天,恐怕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你用股份制的办法,可能一个晚上就可以解决。他合卷而起:资源为什么不能改换成资本的形式?
商机在等待中必然死亡。这时,他想到了职工口袋里沉淀的钞票。这些升值缓慢的资源如果流动起来,那将是倍增效益。300多万,可谓集腋成裘,竟是一夜之间。接着,一台最新的无可替代的CT设备,成为他所在的区域中患者追逐的宠儿。那时,一次的检查费用相当昂贵,要二三百元。但是,因为检查报告相当准确,抵挡不住人们物有所值的心甘情愿。接下来,便是钞票飞速的跳跃。大约一年的工夫,数百万的资金连本带息尽数回笼。王明晓,淘到了第一桶黄金。畅快。其实,严格地说,那是医院的福气,是职工们的眼力不俗。
待到1991年,他正式执掌医院命运的时候,郑州矿务局总医院的财务状况已经从容镇定。
据说,在他买CT的那会儿,理论界关于姓“社”、姓“资”的讨论还没有开始。王明晓着实胆子大了点,一挥而就———《股份制医院的理论探讨》。此文很快发表在《中华医院管理》杂志。这是可以查证的在医疗卫生系统提出股份制设想比较早的文章。王明晓再次从中受益:理性化,必然逼你思考;思考,必然逼你读书。这当是人生步入上升通道最好的方法。
1995年5月……
这一年4月,赴京上任之前,王明晓郑重与母亲话别。此前10年,老人尽管癌症缠身,却因为有个孝顺儿子,终日并不见愁容。王明晓知道,这一走最苦了她老人家。据说,送儿子的那天,母亲强颜欢笑,没有抹一滴眼泪。只是儿子走后不到一个月,老人便含笑撒手人寰。
正是在这个时候,王明晓正式接手中国煤炭总医院副院长职务。
煤炭总医院1993年10月刚刚建成,崭新得近乎空落。医院只有大内科、大外科,统共200张床位。从各路抽调的人员尚处于自然、随意的状态。这对于一位已经担任过等级医院院长的他来说,是重新回到原始状态。失落逼着他重新“起灶”。而这个“重新”是连基础资料都没有的零起点。王明晓必须从一个一个科室的调查分析开始,之后,他拿出的是五六万字的《经济核算管理方案》。这个方案涉及医院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工种,搞得这么一位不怕吃苦,或者说吃了苦而不知苦的人竟然也不否认“熬尽了心血”。
方案出台后,突出的成效有三:一是量化理论,激发了医护人员收治病人的热情,调动了员工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二是质量考评,规范了专业标准,净化了医德医风;三是成本核算,杜绝了浪费,投入产出比更加精良。之后,医院的收入每年以大于50%的速度增长,从1994年的1200万到1997年的4000多万,数字征服了一切。此方案1997年获得煤炭工业部现代化管理成果一等奖。随后,1998年,医院一举通过北京市三级医院的审评。
2003年底,《环球时报》编辑邀请王明晓发表署名文章,回答一个社会关注的问题:当今中国医院院长应该是什么样?
事实上,王明晓的所历所为,是最好不过的解答。
一次,饭桌上,北京某大学教授说到一个新的纳米现象。当金属锌的离子被分割成微单位的时候,离子的表面奇迹般地出现了正电荷。纯粹是一场闲聊,纳米和临床,那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领域。而对于“明晓”之人则是天赐良机。几乎是同时,王明晓的第一反应是革兰氏阴性杆菌。这种对人体有害的病菌它的表面恰恰是负电荷。思维的快速切换就像电流忽然合闸,须臾之间,人的眼前可以是一片通明的世界。如果细菌在正负电荷的中和作用下……他兴奋得简直不敢往下想。就在这顿饭之后,金属锌的纳米试验被请到了煤炭总医院的细菌室。结论是意料之中的———锌的离子表面与病菌接触的地方,形成了明显的抑菌圈,因而进入这个危险地带的细菌居然是无一幸免。机缘,能说是偶然和巧合吗?不,是必然和注定。这项获得国家教委科技成果二等奖的基础研究,迅即开始了跨学科的合作。
近年,管理学在国内成为时尚。无论是西方的MBA,还是中国儒商学派理论。事实上,管理学最终是解决人的问题。王明晓属于引领潮流的先驱者。1996年到1998年期间,他完成了首都经贸大学MBA课程。
和所有的管理者相同,他的眼睛像老鹰一样搜寻着能够快速带来奇迹的人才。德国的王冀博士;日本的王成纲、周正博士;美国的晋志高等,陆续成为他求贤若渴的“猎物”。他并不例外地重复着筑巢引凤的传统故事,诸如人还没到,上百平方米的房子已经事先摆在那儿。
但是,与所有表面现象不同的是,王明晓不是把人才仅仅放在获取直接利益的层面。他用了一个怪异的字眼———“天敌”。他是把人才视为能够给原组织中的人带来巨大威胁力的“天敌”引进的。这种创意来自挪威的一个古老传说。当渔夫把一条鲶鱼放到离开海水便奄奄一息的沙丁鱼群里时,由于仇敌相见,原本准备等死的沙丁鱼居然左冲右突,调动起了所有生命潜能。结果,“天敌”激活了对手。动物尚且如此,更何况有思想、有廉耻之心的人呢。
显然,他要的是这种效应。他要让绝对能干的人才一落地,便在众人心中产生相形见绌的震动和压力。那种不进则退、不进则亡的冲击力,是他期望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当员工的生命潜能、生存要求被激发起来之后,王明晓自然要“添柴加火”。他搬出马斯诺的需要学说,及时地为渴望生存的人提供必要的帮助。按照马斯诺理论,人的需要是分成不同层次的。其中员工的“职业安全的需要”、“受尊重的需要”等,被他视为是管理者必须的责任。一个管理者有义务通过再教育的方式,帮助你的员工消除职业的不安全因素。由此可见,王明晓的管理是相当考究的,他要创造的是整个医院人力资源逐步向人力资本的转化。
他采取的最明显动作是,医院对原有人员的培养力度加大了。从技能到学术上的呵护,使每一个有心进取的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备受重视的感觉。尤其是当护士们也被一批批地送到香港玛丽医院进修的时候,整个医院的气氛完全变了。
同样,为了保证引进的“鲶鱼效应”能够持续下去,孤单的鲶鱼不至于被强大的沙丁鱼种群吃掉,王明晓要对引进人才提供能够保持其持续活力的满足。这种满足被马斯诺称之为“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如果管理者把王冀博士从柏林心脏中心请到北京煤炭总医院,至此,便万事大吉,那将是极大的错误。漠视两地的落差是很荒唐的事。为了王冀个人发展的需要,为了技术更新的需要,他专门在两地之间搭建起双边合作的通道。信息的对接和频繁的沟通,像王冀这样的人才还会“心存余悸”么?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合作为医院构筑起国际交流的平台,使医院有机会进入与世界一流医疗机构进行对话的层面。
2003年4月……
2002年6月,王明晓主持煤炭总医院全面工作,当年,医院收入及病人就诊人数创历史最高水平,然而正当他带领全院职工实施“内抓管理、外树形象、谋取快速全面协调发展”的宏伟规划时,2003年4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不期而遇。作为北京市首批定点医院,王明晓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事后总结,煤炭总医院收治病人180名,治愈率高,死亡率低。其中,特别是医护人员零感染、病人相互零感染的突出业绩,一时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话题。也因此,煤炭总医院理所当然地拿到“特殊时期”的最高荣誉,王明晓本人也被评为“抗击非典最可爱的人”。
当中央电视台记者把摄像机镜头对准他的时候,这个真正的“男儿”竟是潸然泪下。记者们私下说“这是一位感性院长”。其实,这就是王明晓。从医20多年,他记忆中不曾掉过眼泪。为困难,为自己,那不值得。但是,在特殊的日子里,面对同事、孩子或者普通群众,他却常常是泪流满面。
记者们怎么会知道,就在他们到来之前,北京曙光电机厂的工会主席刚刚从医院的大门出去。此时,王明晓的心里,是那个蹬着破旧自行车的背影。就是这样一位穿戴非常马虎的工会主席,找到王明晓,掏出一个纸包,打开来,厚厚的一摞钱,多是五元、十元的票子,码得整整齐齐,一共一万九千零四元。
“一万九千零四元”,对于一个亏损企业,那是多大的一笔数目。这个厂的工人们连工资都开不出来,生活费有时都不能兑现,而工人们是自发地捐款。工会主席话不多,但是王明晓能感觉到,他身后,站着那么多和他一样朴素的工人兄弟,每个人的眼里是担心和真诚的惦记。“四元钱”,很可能就是已经非常节俭的一家人从早点或者买菜的钱里抠出来的……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的心里放不下遥远的浙江一个素不相识的小镇子,从那里寄来了2000多元钱,是当地小学生们的一片心意,钱的尾数还有毛票,孩子们真是使出了最大的力气;他不知道一对老夫妇的姓名,他们给医院送来了一万元。而他们每月仅有几百元的生活费,那可能是他们一辈子的积蓄……
他心里放不下自己的同事们。在非常时期,他们用生命挡住死亡的威胁,在病魔和群众之间筑起一道血肉之躯的屏障。平日里也曾是你多我少、儿女情长的医护们,仿佛一下子都变成了钢铁战士。生死攸关的紧要时刻,他们无怨无悔地把危险留给自己;无私无畏地把安全奉献给别人……
事后,王明晓把自己的心绪一气落在纸上,写成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之后,全文发表在《华夏时报》醒目的位置上。王明晓说,这篇文章是用心血一气呵成的。